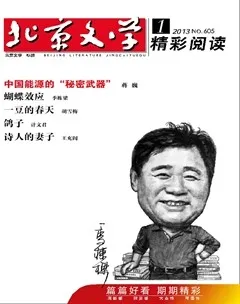創作是心靈的解放
過了不惑之年我才拿起這支筆,開始文學創作。此時,我在人生的路上已經奔忙了三十年,將物質方面基本鎖定在無須計算,即可安穩度日。
那么,到達了人們常用于贊譽的一個詞,“富足”時節了,且又是這般年紀,為什么還要拿起這支相當沉重的筆,進行寫作呢?
《尚書》中說的“詩言志,歌永言,律和聲”,是自上古以來中國的藝術信條。關于“志”,也許有很多解釋,我想,是指思想和情感。文學藝術完全可以認為是精神層面上的東西。至于文學寫作,更可以認為是與金錢無關系的行為。如果發生一不留神走紅了,得到的錢財也是意外之財,與作者和他作品的本意關系甚微。
我是知青。16歲即被安排去了遠離北京的大興安嶺山里插隊。最近,對“知青”又有些提及和關注,讓人們重新想起了這個似乎略帶寒冷的詞。馬未都先生前些日子寫了關于知青的話,他說,“很多知青就是在毛主席的號召下義無反顧地注銷了城市戶口,變成了地地道道的農民……苦難是一種磨礪,當今天我們看到許許多多社會精英成為國家的棟梁之時,才知道苦難遠比學歷重要。當年上千萬知青改變了自己的人生軌跡,這段歷史沒法清晰地講給今天的年輕人,能告訴他們的是,歷史永遠都在錯誤中前行,試圖找到正確的方向。”
凡致力于寫作的人,兒時就做文學夢的人很多,這不外乎源自對文學執著的喜愛。
我在小學四五年級就開始讀外祖父的藏書。最先讀了古文,之后發現了更引人入勝的科幻小說《神秘島》《海底兩萬里》等,再后,就著迷柯南道爾的《福爾摩斯》了。這些啟蒙書,對一個十歲左右孩子說,真是開了眼界,訝于自己所置身的環境以外,竟還有如此遼闊的世界。恩格斯說他在巴爾扎克的《人間喜劇》中學到的比“當時所有職業的歷史學家,經濟學家和統計學家那里學到的全部還要多”。足見文學是啟心智的。于是閱讀便成了我一生的習慣。
在升初中的暑假里,我讀了整套線裝本的《紅樓夢》。這部中國歷史上最杰出的著作,給我的一生所起到怎樣的深刻意義,我現在都無法估量。《紅樓夢》是一部名副其實的百科全書。文學巨匠曹雪芹呢,寫了這部流芳百世的作品,相信他沒有得一個獎,拿一分錢。一生貧寒至終。
我到了初中時,涉及大量外國文學,尤其是俄羅斯文學。沒有多久,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開始了,轟轟烈烈中,我被安排去了遙遠的大興安嶺山里。
當徹底進入了社會的最底層,融入為農民以后,我萬分慶幸在“文革”前讀了許多書。無疑,這些書給予人的啟迪,其精神力量是無窮的。中國在那特殊的年代,文學作品完完全全地被付之一炬了。那時,中國成為沒有文學可言的國度。這是一段“無字”的歷史,長達十年,可悲得令每個過來人回想起來悲痛不已。我在深山八年的日子里,除了《毛主席語錄》,再無其他文字可看,《人民日報》是黨報,我們看到它時已經是半個月以前的了。那個時候,心干涸到極致。
寫作在我來說,或許還有些自我使命感。這樣說并不是”天降大任于斯”的意思。馬丁·海德格爾說:“詩不只是此在的一種附帶裝飾,不只是一種短時的熱情或者一種激情和消遣,詩是歷史的孕育基礎”。
這是迄今為止我認為“文學是什么”較為完滿的解釋。創作伊始,誠如我的文集《暗香如故》后記中,我所說的,“我的人生是匆忙的。匆忙得無法停下腳步,總是有許多許多事情在等著我做。心底里,始終掛牽的,卻只是寫小說的事。小說還沒有寫。從十六歲赴大興安嶺插隊,三十多年間,變遷,動蕩,坎坷,艱辛,我經歷的故事和人太多太多,他們的命運,他們的悲歡離合,喜怒哀樂,我還沒有向世人敘說。倘若再拖延,也許為時太晚,每每這樣的念頭掠過,便急出一身汗來。”
終于,等到了我的生活漸入佳境。自由創作是心靈的解放,令我身心無限地愉悅。
我的短篇小說《我們曾經年輕》,描述了我的一位同學知青生涯的悲慘遭遇;她是將軍的女兒,17歲的年齡,受不了饑餓的折磨,被當地一位農民誘惑而懷孕,當生下的孩子死后,心灰意冷的她拒絕返城,決心終老在那山林中。這篇小說完成后,我并沒有在意有人會說這是知青的一種訴苦,一種喊冤的矯情。因為我講述了一個真實歷史中的一個真實命運。
中篇小說《女人秋月》,是再現插隊知青完全融入農民生活的寫實。女主人公秋月是當地農婦,夫家為了延續香火,強迫她與他人偷情,最后由寄宿在她家的知青點化而悔悟,又因無力反抗而自殺。面對秋月的死,知青盯著墻上“知識青年到農村去,大有作為”的標語,陷入深深的迷茫。這篇小說是我對我的女房東,一個質樸的農村婦女的深切懷念。
中篇小說《四平調》中顧家老與小兩代媳婦,因1949年中國大分裂時,顧老太太的兒子身在臺灣,就此母子們,夫妻們遭遇了生死離別的命運。在殘酷的政治環境下,顧老太太用盡心機,設計要兒媳婦活下來,自己卻是整夜思念兒子低聲悲啼,直至傷心死去。臺灣作家龍應臺在她的一本紀實文學中,訪問一位當年國民黨撤往臺灣時抓來當腳夫的老兵,那時才十幾歲的人,一走就是四十二年。待他回來尋找父母時,人們告訴他,母親臨終前說,“我是想我兒子想死的,等我兒子回來你告訴他,我是想他想死的。”民族大分裂,這是廣泛的痛苦。這痛苦是人民的,是母親的,是撕心裂肺,肝腸寸斷的。
寫作者以冷靜的目光,以獨立而自由的心境,將一個個鮮活的人性與生存的困境寫出來,是我提筆寫作的原本意義。這種意義的寫作,如果生活負擔沉重,在當今堅持下去可能會非常非常之艱難。
關于寫作,墨白先生概括得十分精辟。“一個作家寫什么或不寫什么,那是由他的命運來決定的。那些傷痛的,不可回避的經歷和對生命深刻的感受,也是不可代替的。”
把人類命運的感悟和對歷史的見證寫下來,是我將繼續進行下去的。
責任編輯 張頤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