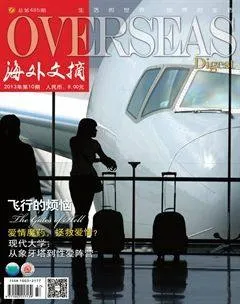普京的最后一站
12年來,弗拉基米爾·普京一直在允諾建設一個偉大的俄羅斯。很長時間,俄羅斯人相信他的承諾。然而現在,這個越來越強勢的領袖卻發現自己不得不應對一個騷動不安的國度。加拿大《麥考林周刊》的記者邁克·佩特羅走遍整個俄羅斯,對這個國家各階層的人們——從高級官員、反對派人士,到沉默的普通工人進行了采訪,發現在普京的鐵腕統治下,動蕩已若隱若現。
小城一幕
2013年4月底,小城皮卡洛沃依然覆蓋在緩緩融化的積雪之下。這是一座工業城市,位于圣彼得堡以東250公里處。一片大型工業區是這座有著2.5萬人口城鎮的主要就業來源。其中,一座巨大的水泥和磚塊工廠屬于奧列格·德里帕斯卡。他是一個身家億萬的寡頭,也是全俄羅斯最富有的人之一。和其他俄羅斯巨頭一樣,德里帕斯卡也發跡于混亂的20世紀90年代。那時,隨著蘇聯解體,政府對商業的控制全線崩潰,一些野心勃勃、有政治靠山的人乘虛而入,賺得缽滿盆滿。
功成名就的德里帕斯卡曾多次表示,自己會回報國家,立志改善俄羅斯國家的整體狀況。但和另外一些鋒芒畢露的寡頭不同,德里帕斯卡深知絕不能挑戰普京的權威。一直以來,他遠離政治,埋頭積累自己的財富。
但在2009年,他還是不可避免地和普京對上了。那一年在皮卡洛沃,很多工人失業,有工作的人也拿不到薪水。由于當地居民付不起賬單,市燃氣公司便停止給居民供暖和提供熱水。德里帕斯卡正是這家公司的老板。工廠工人和當地居民集會示威,最后阻斷了通往圣彼得堡的高速公路,造成400公里的交通阻塞。
這件事引起了普京的重視,他親自前來處理問題。當時,普京是俄羅斯總理。他把皮卡洛沃市政廳官員以及包括德里帕斯卡在內的所有工廠老板都叫到跟前,就像訓斥頑皮的學童一樣,把他們狠狠訓斥了一頓——電視臺的攝像機記錄下了這一切(好一場政治秀,表演者普京比他的所有前任都更深諳媒體的力量)。“你們的野心、無能、貪婪綁架了數千民眾!”普京嚴肅地說。然后,他命令這些老板當場保證重新雇用那些被解雇的工人,立刻補發拖欠的工資。
“每個人都在這份同意書上簽名了嗎?”普京問,“德里帕斯卡,你呢,簽名沒有?我還沒看到你的簽名,過來!”
德里帕斯卡乖乖走上前,努力想迅速讀完那些條款,奈何普京就在一旁死盯著他,德里帕斯卡知道自己無法細看了,看了也改變不了什么,便簽了字。對他的表現普京顯然不滿意,厲聲說:“好了,現在把筆還給我。”
那一刻很能說明為什么普京依然是俄羅斯不容置疑的領袖。雖然當時俄羅斯名義上的總統是梅德韋杰夫,早在一個月前他就命令當地官員處理好這一事件,但沒有任何結果。然而,普京一來,當天工人們就收到了短信通知,拖欠的工資已經全部支付。
于是,在這座曾為反法西斯戰爭出過力的小城里,普京再次顯示他才是這個國家社會穩定與經濟繁榮的保障。在民眾遭受苦難的時候,是他只身面對那些一夜暴富的寡頭。只需一個下午,他就為人們帶來了薪水、工作以及社會穩定。
不過,也正是這一事件,暴露了普京的困境。正是因為普京獨攬大權,造成國家杜馬形同木偶,各級政府部門都依賴和奉行克里姆林宮的決策,從而執政力、行動力都相當低下,才讓皮卡洛沃的局勢一再惡化,最終演變成普京不得不親自處理的局面。
54歲的工人車庫諾夫頭戴一頂皮帽,身穿尼龍夾克,一身酒氣,“普京來之前,我已經三個月沒拿到工資,很可能馬上就要失業。”他說。雖然普京讓他保住了飯碗,但當被問及對普京的印象時,車庫諾夫只是聳了聳肩。在去年的總統大選中,他投了一位共產黨參選人的票,“蘇聯時期雖然經濟停滯,但人們的基本生活至少還能保障。”他說。
車庫諾夫還告訴筆者,在去年的總統大選前夕,一位主管曾召集工人們開會,“他敦促我們投普京的票,說現在政局穩定,如果沒有普京,情況將發生變化,人們就又要過苦日子了。”
這種說法普京已經兜售多年:“俄羅斯曾經是世界強國,但在我領導之前卻已岌岌可危。至今,它依然面對著內憂外患。只有我有足夠的力量和決心來遏制這些敵人,重建俄羅斯的榮耀。我們已經取得了很多的成績,但是沒有我,一切都將如往日的輝煌一樣再次灰飛煙滅。”
很長時間里,俄羅斯民眾相信這套說辭。于是從2000年到2012年,普京接連出任了兩任俄羅斯總統和一任總理。去年,他卷土重來,再次成為俄羅斯總統。按目前的情形看,他有可能執政俄羅斯直到2024年。屆時,他已經71歲,數百萬新出生的俄羅斯人除他之外再沒見過別的總統。
可與他首次入主克里姆林宮時不同,俄羅斯的形勢已經發生了變化。人們對于上世紀90年代的回憶漸漸淡去,新一代俄羅斯人有了自己的要求與期望。越來越多的人寧愿冒著被捕和坐牢的危險,也要上街游行,反對普京的統治。即便是那些對抗議游行漠不關心的人,也在內心質疑,為什么自己的政府如此貪腐無能?這就是下一個十年里,普京將要領導的國家。
為了理解普京如何改變了俄羅斯、能否繼續維持大權,筆者橫跨俄羅斯西部一千公里,和工人、士兵、退休人員、政治家、知情人士以及那些希望把普京趕出克里姆林宮的人進行了溝通交流。由于俄羅斯國土遼闊,這段旅程也僅僅走了它的一小部分領土。我們由此得出的畫面是:一位越來越強勢的鐵腕領袖、一群曾經擁護他的民眾,和一個與他漸行漸遠的國度。

克格勃年代與普京的崛起
普京曾言,他對克格勃的迷戀源于他幼時無處不在的間諜小說,他還喜歡觀看冷戰時期拍攝的反映前蘇聯諜報人員英勇行為的電影,“我就是蘇聯愛國主義教育最純粹、成功的產物。”他說。長大后的普京雖然如愿以償成為克格勃的一員,但他的上司卻認為他潛力有限、個性孤僻,即使派到國外,也不能去倫敦、華盛頓這類重要的大城市。所以,普京被安排到東德的德累斯頓工作。
1989年,柏林墻轟然倒塌,東西德實現統一。可隨之而來的蘇聯解體卻讓普京的世界分崩離析。普京并不懷念斯大林,他之所以堅持認為蘇聯的解體是20世紀最大的災難,是痛心俄羅斯在世界舞臺上大國地位的喪失。蘇聯的解體深深影響了普京以及數百萬像他這樣的俄羅斯人。雖然當時在東德的角色微乎其微,但普京和其他數不清的間諜、警察、士兵以及軍工廠工人一樣,自詡為蘇聯的守護者和建設者。然而,37歲的普京回國后,卻發現民眾公然鄙夷他曾為之努力的一切。這段經歷讓他痛苦萬分,對其影響迄今可見,他的桀驁不馴、他對自由主義反對派的深刻敵意都來自于此。
普京曾說,任何不為蘇聯的解體感到遺憾的俄羅斯人都沒有良心,但任何為蘇聯解體感到遺憾的人都沒有大腦。
普京絕對是有大腦的人。由于蘇聯解體之后俄羅斯的社會災難,人們無比懷念蘇聯時期的井然秩序和明確目標,普京立刻抓住了人們的這一懷舊心理。整個九十年代,俄羅斯經濟一落千丈,政局動蕩不安。別的國家不再懼怕俄羅斯,它的公民失去了畢生積蓄,整個國家經濟體系崩潰,寡頭們大發國難財。與此同時,犯罪率高漲,毒品泛濫。一支由車臣分裂分子組成的烏合之眾就能把堂堂的俄羅斯軍隊打得一敗涂地,灰溜溜地回家。掌管這一切的是俄羅斯的第一任總統、酗酒成性的葉利欽。情況委實令人尷尬。
此時,普京回到了列寧格勒,在大學里謀了一份外事助理的職業。不過,不到三個月,他就告別了這份職業,在1990年春天成為了著名民主派政治家、市政廳議員阿納托利·索布查克的幕僚。索布查克在1991年六月當選圣彼得堡議員,普京也正式進入政壇。
1996年,普京來到莫斯科,開始任俄總統事務管理局副局長。葉利欽的班底有許多曾追隨索布查克的人,他們都認識并信任普京,這種關系為普京打開了通往克里姆林宮的大門。1997年,他加入了葉利欽總統的幕僚;次年,葉利欽任命他為俄羅斯聯邦國家安全局副局長。這個機構的前身就是克格勃,這次任命對于普京來說可謂是重操舊業。
普京的崛起勢不可擋。1999年8月,葉利欽又任命他為俄羅斯總理,由于車臣武裝分子襲擊達吉斯坦,俄羅斯重新出兵車臣。這位新總理尚武好戰,允諾不惜一切代價也要將恐怖分子繩之以法。2000年新年前夕,葉利欽突然宣布辭職,任命普京為代理總統。此時的普京,在公眾中的地位早已超過其他總統寶座的競爭者。三個月后,普京在第一輪競選中就贏得了總統大選。
普京的演變

在就任總統后的第一次公開演說中,普京允諾:“言論自由、信仰自由、新聞自由、財產權利,這些文明社會的根本要旨將在國家的保護下不受侵犯。”很難想象今天的普京還會發出這樣的言論。不過,在其執政早期,有很多人將他的言語奉為圭臬。
就連普京的反對者也承認他早期強烈的民主傾向。古德科夫是如今普京最猛烈的抨擊者之一。他身材高大,長著海象似的八字須,最近被趕出了國家杜馬。他被驅逐的官方理由是被指控違反議會經濟規定,而很多人則認為他是因為批評普京而受到懲罰。盡管古德科夫現在對普京頗有微詞,但卻承認普京“一開始是位非常民主的領導”。這種觀點在俄羅斯并不鮮見。曾深信普京是個真正的民主改革者、今天卻反對他并上街游行的人,如今在莫斯科大有人在。
巴甫洛夫斯基恐怕比任何人都要了解普京的政治演變過程。從葉利欽選擇普京作為自己的繼任者時,巴甫洛夫斯基就是克里姆林宮的局內人士,并且直到2011年都是普京的幕后軍師。巴甫洛夫斯基一頭灰白的短發,戴著方框眼鏡,表情木然,一看就是一個高超的暗箱操作者,而普京就是他的作品。“普京智力超群,善于抓住問題本質,處理問題極其靈活,并且實事求是。在他身上我能看到一位幾近完美的總統,當初葉利欽選擇普京而不是他人,我非常高興。”
巴甫洛夫斯基將自己曾全身心參與建設的普京的治理系統稱作“管理下的民主”。當然,所謂“管理下的”不過是受限制或受管制的委婉說法。巴甫洛夫斯基對民主的理解已經這般靈活,但最終還是與普京分道揚鑣,因為這位他曾為之傾心的領導者表現出反民主的傾向,越來越留戀權力。在他看來,一個十年前是完美總統的人,今日已然不是。
2011年,巴甫洛夫斯基與普京決裂。但在那之前,不論是對于民主,還是對于俄羅斯融入西方,普京的態度一直三心二意,這在他第一任總統期間就顯現出來。早在其擔任總統不久,西方國家的一系列舉動就令普京心灰意冷:俄羅斯協助美國打擊阿富汗的好心并沒有得到西方的感激和好意,與此同時,北約不斷東擴,進入歐洲和波羅的海。這在俄羅斯看來,無異于耀武揚威地侵入了自家的后院。
在對國際事務失望之際,普京以增強國內團結為由加強了對俄羅斯的政治管控。他廢除了由地方選取行政長官的做法。在過去,俄羅斯的225個選區可以直接選出一半數目的國家杜馬代表,余下的由黨內產生。現在,450個代表名額都由黨內指定,而一個政黨想要加入杜馬所需的投票通過率,提升到7%。這些措施實實在在地將權力集中到普京手中。取消地區選舉當地行政長官的做法可以阻撓潛在政治對手的壯大;而對杜馬選舉的改變,則將克里姆林宮不喜歡的政黨拒之門外。
克里姆林宮專門組建了一個支持普京的青年隊伍。這個組織稱作“我們的人”,聽起來隱約有些法西斯的影子。其成員都參加愛國青年野營、開展支持普京的集會、抗議那些他們認為對俄羅斯懷有敵意的國家使館。但是,這個組織的主要目的是防范在莫斯科發生大規模的抗議活動。它的發起人之一曾透露,該組織的成員必須生活在離莫斯科不超過十小時車程的地方,以便在夜間搭上公交車,早晨就能占領紅場。
充滿爭議的“梅普組合”
2008年第二任總統任期結束前,普京完全可以直接修改憲法,第三次競選連任,但他卻遵照法律下臺,全力支持他當時的副總理梅德韋杰夫競選總統。后者也是他在圣彼得堡時的同事。梅德韋杰夫很容易就贏得大選,并提名普京為自己的總理。
梅德韋杰夫把自己包裝成一個推崇現代精神的人。普京喜歡騎馬射虎,梅德韋杰夫卻喜歡到美國硅谷一游,并試圖在俄羅斯也建設一樣的高科技樞紐。然而,俄羅斯的最終操盤者還是普京,其依然控制著俄羅斯的權力支柱和經濟命脈。俄羅斯政府機構的性質在梅德韋杰夫統治期間并沒有發生變化,仍然貪腐無能。
謝爾蓋·馬格尼茨基律師的命運最能反映這一切。他因曝光一些官員涉嫌上百萬美元的稅務詐騙行為,被以逃稅的名義逮捕。在獄中,他遭受虐待,并因無法得到救治而最終在監獄里死去。在他死后,俄羅斯政府居然還對他進行了審判。就在2013年7月,也就是他遇害三年后,謝爾蓋·馬格尼茨基被最終裁定為犯有逃稅罪。
雖然還不是完全民主,但俄羅斯的民眾卻并不是沒有任何力量。普京深知這一點,他的權力最初就是來自于民眾對他的愛戴,為了繼續爭取他們的愛戴,普京費盡心思塑造自己的形象。
2011年,普京現場觀摩了一場武術比賽,這是克里姆林宮公共宣傳的常用手段之一。這件賽事充滿了活力與力量,就連觀眾都大多是普京那樣的人——強壯有力、自尊高傲、熱愛國家。錦上添花的是,這場比賽中,俄羅斯運動員干脆利落地打敗了美國選手。
可當普京拿起麥克風想要祝賀俄羅斯選手贏得勝利的時候,不可思議的事情發生了。嘲諷聲和起哄聲響徹這家位于莫斯科的體育館。普京面容僵硬,人群中有人叫道:“滾開!”
這場比賽被俄羅斯電視臺全程直播。盡管在之后的新聞中,這一片段被剪輯掉,但在互聯網上,這段視頻卻迅速流傳開來。體育館內民眾的反應只是表面的漣漪,下面有著更洶涌的波瀾。就在體育館事件幾周前,梅德韋杰夫宣布,普京將在馬上到來的大選中競選總統,如果獲勝,梅德韋杰夫將擔任總理一職。
很難具體確定究竟何時俄羅斯人的不滿和憤世嫉俗聚焦成了反抗普京的力量,但梅德韋杰夫的這一通告無疑是火上澆油。俄羅斯人都對此義憤填膺,他們將“梅普”二人互換身份的做法稱作是“王車易位”(國際象棋中保護國王的策略)。巴甫洛夫斯基認為,如果普京在2008年時退出,那么他的執政時期將被認為是俄羅斯歷史上的一個閃光點,“可當他決定第三次擔任總統的時候,他親手毀了這一切。”
2011年12月的國會大選,普京的“聯合俄羅斯黨”得票率低于50%,與2007年相比,下降了15%。就在當月,莫斯科發生了反普京示威游行,這是自蘇聯解體以來莫斯科發生的最大規模的示威游行,其他一些城市也有波及。
總統選舉在示威游行中如期進行,普京又贏得了大選。當晚,他登上紅場外的一座高臺,熱淚盈眶,向支持者宣告勝利,他說:“這不僅僅是一次總統選舉,對于我們所有人,對于全俄羅斯,這都是一場考驗。我們已經證明,沒有人可以強加給我們任何東西——絕對不行!”就這樣,普京把他的勝利等同于這個國家的勝利,那么那些反對他的人自然就是叛徒、奸細以及西方的走卒。
不過,俄羅斯也有獨立的聲音。“莫斯科回聲”廣播電臺的副總編彭特曼就是這么一個人。他擔心普京對示威活動的鎮壓會將一些人推向極端。“普京不明白的是,當他逮捕年輕人的時候,也摧毀了那些由聰慧的青年男女發起的正當抗議。”
這也是前杜馬議員古德羅夫所擔心的。和普京一樣,他也是克格勃出身,在蘇聯解體時經歷了巨大的心理創傷。他擔心,克里姆林宮對權力制約和平衡的蔑視會使俄羅斯人極端化,將他們推向暴力甚至內戰。他害怕俄羅斯會因此四分五裂。

不明朗的未來
如果在如今的俄羅斯尋找一處和當初沙皇冬宮類似的地方,首選不是克里姆林宮,而是莫斯科西郊的拉布勒斯卡地區,連普京都在此處有自己的住所。俄羅斯的很多政治、商界精英以及寡頭都居住在此處。為了方便官員出行,從這里通往城內的公路經常被管制。居住在這里的富人們大都對城里的游行不屑一顧。他們認為,大規模的示威活動主要集中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而這些由數千人發起的運動對于擁有一億多人口的俄羅斯而言,影響微乎其微。
但是,僅從數字觀察問題,未免太過膚淺。去年,一家研究所在俄羅斯16個地區進行調研后發現,民眾普遍認為政府貪腐無能,普京的支持率每月都在下降。沒上街游行并不代表那些地方的人們就對政府滿意。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游行示威的焦點多集中在新聞自由、選舉公平等方面,可對于沉默的大多數俄羅斯人來說,他們的憤怒更體現在對國家公共服務的沮喪之上,他們更關心醫療、住宅和公正的司法系統。可惜,那些喊著要爭取民主自由的反對派領袖卻沒能拉近和底層民眾的距離。
剛剛加入克格勃時,普京的上司曾評價他“缺乏對危險的感知”。這不是在贊賞普京勇武,而是認為他常常意識不到威脅的臨近。可眼下局勢的危險,普京絕不可能沒有察覺。俄羅斯人已不再相信他的統治。
曾幾何時,他是葉利欽時期社會動蕩的克星,強悍有力、頭腦清醒,致力于將俄羅斯打造成世界強國。但九十年代離現在似乎已經非常遙遠,在普京治下的13年,俄羅斯政府依然深陷貪腐,很多地區的人們平均壽命不到60歲。
對于很多俄羅斯人來說,2011年普京宣布第三次競選總統是壓斷他們的最后一根稻草。即便是那些一貫對政治漠不關心的人也開始加入到反普的陣列中來。普京所采取的一系列鞏固權力的做法,使其成為眾矢之的。
眼下,那些生活在俄羅斯其他地區的普通民眾沒有對發生在大城市的抗議發揮多少作用,但如果這一點發生改變,普京的統治將岌岌可危。在距離莫斯科450公里之外的一家餐館里,一個叫格帕申科的人說:“現在世道太差,醫院亂收費,老百姓連病都快看不起了。我支持莫斯科的抗議游行,但莫斯科太遠了,我沒錢過去。”
[譯自加拿大《麥考林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