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家倫的新政功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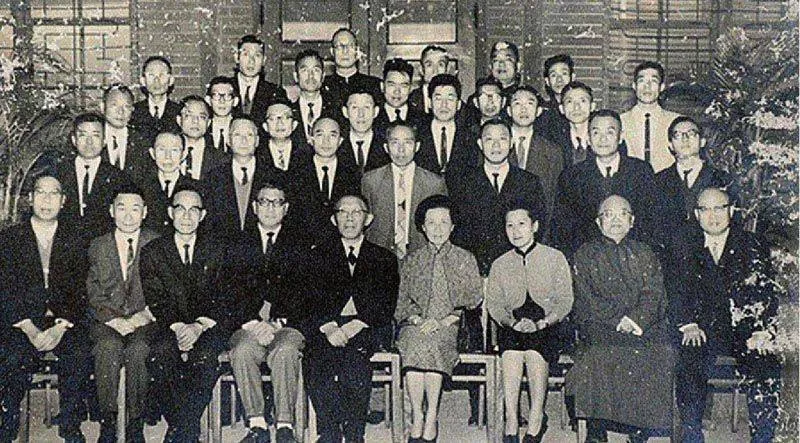

1911年暮春,五四運(yùn)動(dòng)使北京大學(xué)的學(xué)生領(lǐng)袖傅斯年、羅家倫和段錫朋三人一時(shí)間蜚聲海內(nèi),在后來的歲月里,他們活躍在民國(guó)的社會(huì)政治和文化教育領(lǐng)域,均有一番作為和表現(xiàn)。首先提出“五四運(yùn)動(dòng)”名詞的羅家倫便是一例。自192 8年至抗戰(zhàn)中期的十多年里,他基本是在大學(xué)校長(zhǎng)的職位上奔波忙碌,其職責(zé)之重大、作用之關(guān)鍵,略微夸張地說,在當(dāng)時(shí)的高教圈內(nèi)可謂罕有其匹。其執(zhí)掌清華大學(xué)的經(jīng)歷,雖短暫卻對(duì)日后這座中國(guó)一流高等學(xué)府的發(fā)展奠定了重要基礎(chǔ)。
羅家倫(字志希)是清華學(xué)校改制為清華大學(xué)后的首任校長(zhǎng),在不足20個(gè)月的任期內(nèi),差不多逐一理順了遷延許久的校政體制:不僅使該校結(jié)束了長(zhǎng)期游離于中國(guó)教育體系之外的特殊狀態(tài),也將清華賴以生存和發(fā)展的“命根子”——退還庚款的清華基金妥善而獨(dú)立地加以保管;同時(shí),強(qiáng)力引進(jìn)大批優(yōu)秀教師,奠定了“大學(xué)乃有大師之謂也”的基本格局;非但如此,他還極力擴(kuò)充圖書儀器設(shè)備及校內(nèi)基礎(chǔ)設(shè)施,擴(kuò)大了招生規(guī)模,更使清華圖書館由偏重西文書冊(cè)進(jìn)而中西圖書并藏,成為堪與北大圖書館和國(guó)立北平圖書館鼎足而三的文化重鎮(zhèn)。后人大多贊譽(yù)梅貽綺校長(zhǎng)時(shí)代的“清凈無為”,殊不知這與羅家倫執(zhí)掌清華時(shí)大刀闊斧的整頓舉措有著密不可分的因果關(guān)聯(lián)。清華之成為國(guó)內(nèi)一流學(xué)府,實(shí)源自上述開拓之功。
此后,羅家倫繼而“臨危受命”,出任因風(fēng)潮迭起而被教育部解散重組的中央大學(xué)校長(zhǎng),他以“安定、充實(shí)、發(fā)展”的治校思路,重建了這所國(guó)內(nèi)規(guī)模宏大、學(xué)科最健全的“首都大學(xué)”,使之成為南京國(guó)民政府“黃金十年”發(fā)展期的一個(gè)突出亮點(diǎ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