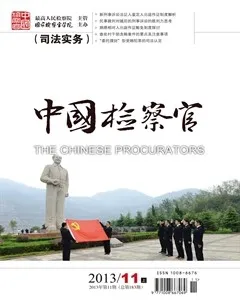小議自動投案
我國《刑法》第67條第1款、第2款規定“犯罪以后自動投案,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對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其中,犯罪較輕的,可以免除處罰。被采取強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實供述司法機關還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論。”自首,雖然在<<刑法>>中有明確規定,但是在司法實踐中自首的認定存在一定的困難。根據刑法及相關司法解釋的規定,自首必須是自動投案或者視為自動投案并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對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一般只要求犯罪分子能如實供述主要犯罪事實即可,同時在供述的持續性上一般要求如果如實供述自己罪行后,又翻供的,只要在一審庭審結束前又如實供述的即可。在司法實踐中,對如實供述不存在什么爭議,但是對如何認定自動投案或者視為自動投案存在較大爭議。筆者認為,在司法實踐中,認定犯罪嫌疑人是否構成自動投案或者視為自動投案,不僅要依據我國刑法及其司法解釋的規定,還應依據我國<<刑事訴訟法>>的規定來認定,犯罪嫌疑人的行為構成自動投案或者視為自動投案時應依法予以認定。現就司法實踐中遇到的幾種情形,談談自己的看法。
一、偵查機關在立案前,對報案、舉報、控告材料進行初步核實過程中,在現有證據已有指向某人為可能的犯罪嫌疑人時,可能的犯罪嫌疑人如實陳述自己罪行,應認定為自動投案
第一,偵查機關在取得可能的犯罪嫌疑人陳述后立案的,或者偵查機關取得可能的犯罪嫌疑人陳述,并根據其陳述收集到其他證據后立案的,應認定為自動投案或者視為自動投案,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但紀檢監察機關移送的案件除外。偵查機關在接到報案、控告、舉報后,僅根據報案、控告、舉報的材料無法判斷是否夠上立案條件,對這些材料進行調查核實是必要的,不僅可以避免對公民任意追訴,也是保障人權的一種表現,這種調查核實是初查。
第二,在初查過程中,偵查機關可以詢問被查對象(即已掌握的證據材料顯示的可能的犯罪嫌疑人),雖然這種詢問,是按詢問證人的方式、程序進行的,這種調查行為也稱為詢問,但是這種詢問和立案后詢問還是存在明顯的不同。立案后詢問證人是一種偵查行為,而在初查中詢問被查對象不是偵查行為,只是一種核實證據材料的行為。這種詢問也不能當作治安案件的詢問,治安案件中的詢問是公安機關明確作為治安案件辦理的案件進行的詢問。這種案件公安機關顯然不是作為治安案件來辦理的,而是按照刑事案件來辦理的。
第三,在司法實踐中,有的偵查機關根據報案、控告、舉報的線索和報案人、控告人、舉報人在報案、控告、舉報時提供的證據,已經能夠判斷出有犯罪事實并需要追究刑事責任,即已達到刑事立案的證據標準,但是因害怕立了案卻破不了案,影響自身考核,或者因其他原因,而故意不立案,使用初查程序或者按治安案件對待,待將犯罪嫌疑人控制后再立案。這種作法是違背程序正義的,是偵查機關不善意履行職責,惡意規避法律的表現,在此不對此種現象進行討論。本文討論的情形,是偵查機關在接到報案、控告、舉報后,在善意執行法律和履行職責的情況下,無法判斷出是否達到立案標準,應予初查的情形。偵查機關對案件進行初查時,雖然偵查機關掌握的線索顯示某人是可能的犯罪嫌疑人(即被查對象),但是初查時是否有犯罪事實并需要追究刑事責任尚不確定,而被查對象是否與犯罪有實質的聯系則更加不確定的。偵查機關在取得被查對象陳述后立案的,或者偵查機關取得被查對象陳述,并根據其陳述收集到其他證據后立案的,是因為被查對象的陳述,才使犯罪與被查對象產生了實質性聯系。
首先,偵查機關在初查中主動接觸被查對象,被查對象如實陳述自己罪行的,應當視為自動投案。
這種情形中,被查對象是被動接觸偵查機關的,并且其實際上已經在偵查機關的控制之下。但是,根據刑事訴訟法的規定,立案是刑事訴訟的開始,偵查機關只有在立案以后,才能實施偵查行為,才能對犯罪分子實施限制人身自由的強制措施。偵查機關在初查時,雖然可以接觸被查對象,并可以對其進行詢問,但是這時接觸被查對象和對其進行詢問,均是以被查對象自愿為前提,如果被查對象不愿意與偵查機關接觸或者不愿接受詢問,偵查機關不能采取任何的強制措施。我國法律規定,任何知曉案情的公民均有作證的義務,但是我國法律并沒有對公民不履行作證義務規定任何法律后果,同時我國法律是禁止對證人采取任何限制或者剝奪其任何權利的措施的,更不能對證人適用任何強制措施。法律僅規定犯罪嫌疑人對偵查人員的訊問,有如實回答的義務,沒有規定證人對偵查人員的訊問有如實回答的義務。同時初查中公民接受詢問的義務,不應該高于立案后的作證義務。故初查中,對被查對象的詢問,是以被查對象同意接受詢問為前提的。
偵查機關進行初查的原因,是尚不能夠確定是否有犯罪事實發生,需要追究刑事責任。在此情況下,是否有犯罪事實發生,需要追究刑事責任尚不能確定,對于所接觸的被查對象是否與犯罪有實質性關系更是不能確定,這時被查對象如實陳述自己的犯罪事實,一是被查對象陳述幫助偵查機關達到了立案標準,使偵查機關把犯罪事實和被查對象實質性的聯系在了一起;二是表明被查對象愿意配合偵查機關查明犯罪事實;三是該陳述犯罪事實的行為本身也暗含將自身交付偵查機關追訴的意愿。試想,如果被查對象在接受詢問時拒絕回答,偵查機關是否可以直接立案,并對被查對象進行訊問,并采取強制措施?答案顯然是不能。因此,筆者認為此種情況,對被查對象應當視為自動投案,如其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后不翻案,或者后來翻案,但在一審庭審終結前又如實供述的,應認定為自首。
其次,偵查機關通過某種方式將被查對象騙至偵查機關,被查對象如實陳述自己的犯罪事實的,應當視為自動投案。
在此種情況下,被查對象到偵查機關不是出于自己的意愿,其到偵查機關的行為本身并不能認定為自動投案。被查對象到偵查機關后即處于偵查機關控制之下,但是偵查機關此時只是在適用初查程序,不能使用任何強制措施,被查對象在法律地位上仍然是自由的公民,其各種權利不受任何的剝奪和限制,其可以根據自己的意愿留在偵查機關配合偵查機關初查,也有權利根據自己的意愿離開偵查機關。
在此種情況下,被查對象如實陳述自己罪行的,其和偵查機關主動接觸被查對象,被查對象如實陳述自己罪行的情形本質上是一致的,也應當認定為視為自動投案,如其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后不翻供,或者后來翻供,但在一審庭審終結前又如實供述的,應認定為自首。
再次,偵查機關通過各種方式通知被查對象到偵查機關,被查對象如實陳述自己的犯罪事實的,應當視為自動投案。
在此種情況下,被查對象雖然是被偵查機關通知到偵查機關的,但是被查對象到偵查機關去這一行為本身還是其自愿所為,其是可以選擇按通知內容去偵查機關和不理會通知不到偵查機關去的。除此之外,被查對象到偵查機關后,仍然享有接受偵查機關詢問和拒絕偵查機關詢問的自由,同時其也享有立即離開偵查機關的權利,偵查機關對被查對象提出的離開偵查機關的要求,在法律上無權加以拒絕。故在此種情況下,被查對象如實陳述自己的犯罪事實的,應當視為自動投案,如其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后不翻供,或者后來翻供,但在一審庭審終結前又如實供述的,應認定為自首。
二、在查辦職務犯罪案件中,紀檢監察機關在案件調查中發現犯罪行為,移送司法機關處理的案件,被調查人在司法機關立案前如實供認犯罪事實的,不能認定為自動投案,也不能認定為自首
此種情況下,司法機關尚未立案,尚未啟動刑事追訴程序,但是被調查人的犯罪事實已經被紀檢監察機關掌握,被調查人供認自己犯罪事實的行為對司法機關將其與犯罪事實實質聯系起來,沒有任何幫助,也無從體現犯罪嫌疑人主動將自身置于司法機關及其人員控制之下,接受法律制裁的意愿。但是,如果被調查人在尚未受到調查談話或者未被宣布采取調查措施之前,主動到紀檢監察機關交代自己犯罪事實的,應認定為自動投案。
三、犯罪行為發生后,犯罪分子主動報案,不管是否表明自己是作案人,只要留在犯罪現場,司法機關到現場后,在詢問時交代自己罪行的,應當視為自動投案
犯罪行為發生后,犯罪分子知道他人報案,在其能夠逃離犯罪現場,而仍然留在犯罪現場,在司法機關趕到犯罪現場后,犯罪分子無拒捕行為,供認自己犯罪事實的,應當視為主動投案。如果犯罪分子因客觀原因,其不能逃離犯罪現場,則不能視為自動投案。
四、罪行未被有關部門、司法機關發覺,僅因形跡可疑被盤問、教育后,主動交代犯罪事實的,應當視為自動投案,但有關部門、司法機關在不依賴犯罪分子交代的情況下,能夠在其身上、隨身攜帶的物品、駕乘的交通工具等處發現與犯罪有關的物品的,不能視為自動投案
如果這些與犯罪有關的物品,在沒有犯罪分子主動交代的情況下,有關部門、司法機關將難以發現的話,仍然應當視為自動投案。此種情況下,是犯罪分子的主動交代行為,使有關部門、司法機關得以發現與犯罪有關的物品,進而將犯罪分子與犯罪事實實質聯系起來,其主動交代行為本身,也表明其主動將自己置于司法機關控制之下,接受法律制裁。
五、司法機關立案后,尚未確定犯罪嫌疑人,在一般性排查階段,犯罪分子主動供認犯罪事實的,應當視為自動投案
不論犯罪嫌疑人是在司法機關以內接受排查,還是在司法機關以外接受排查,均應當視為自動投案。此種情況下,是犯罪分子的主動交代行為,使有關部門、司法機關將其與犯罪事實實質聯系起來,其主動交代行為本身,也表明其主動將自己置于司法機關控制之下,接受法律制裁。
六、司法機關立案后,已經確定了犯罪嫌疑人,通過某種方式將犯罪嫌疑人引誘至司法機關,不能認定為自動投案
在此情況下,犯罪嫌疑人到達司法機關不是出于自己的主觀意愿,從實質上說屬于被動到案。同時在犯罪嫌疑人供述之前,司法機關已經將犯罪事實與犯罪嫌疑人實質聯系了起來,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對司法機關認定犯罪事實與犯罪嫌疑人之間的實質聯系沒有起到關鍵作用。因此,對犯罪嫌疑人不能認定為自動投案。
七、司法機關立案后,已經確定了犯罪嫌疑人,通過某種方式要求犯罪嫌疑人到司法機關就該事情說明情況,不論司法機關是否在通知中說明犯罪嫌疑人的行為是犯罪行為,只要犯罪嫌疑人在接到通知后,主動到司法機關的,應認定為自動投案
首先,犯罪嫌疑人在去司法機關之前,已經知道司法機關在調查某事情;其次,司法機關的通知行為本身,沒有強制性;再次,犯罪嫌疑人在接到司法機關的通知后,仍然可以決定是逃逸,還是到司法機關說明情況。
此種情況和犯罪嫌疑人逃逸后,在司法機關規勸下,到司法機關投案的情形沒有實質的區別,且此種情況,犯罪嫌疑人認罪、悔罪表現更加及時,同時也更加節約司法資源,有利于司法經濟。
八、偵查機關立案后,通過郵寄、委托基層組織代為送達等方式向犯罪嫌疑人送達傳喚通知,進行第一次傳喚,只要不是偵查機關派偵查員直接對犯罪嫌疑人進行傳喚的,犯罪嫌疑人在接到傳喚通知后,按要求到偵查機關接受訊問的,應認定為自動投案。
首先,犯罪嫌疑人接到傳喚通知后,在去司法機關之前,已經知道司法機關正在偵查自己的犯罪行為;其次,傳喚不是強制性措施,犯罪嫌疑人是否按傳喚通知到司法機關接受訊問,取決于犯罪嫌疑人自身的意愿;再次,犯罪嫌疑人在接到的傳喚后,仍然可以決定是逃逸,還是到司法機關說明情況。
在司法實踐中,認定犯罪嫌疑人自動投案或者視為自動投案,應立足于犯罪嫌疑人的自愿性和主動性,只要是犯罪嫌疑人自愿、主動將自己置于司法機關及其人員控制之下,接受法律制裁的,均應認定為自動投案或者視為自動投案。同時,司法機關及其工作人員,應本著善意執行法律,保障人權、無罪推定的理念,在執行法律中依法限制和剝奪犯罪嫌疑人的權利。這不僅是保障人權的應有之義,也是程序正義的必然要求,更是依法治國、社會主義法治理念對我國司法機關和司法人員的基本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