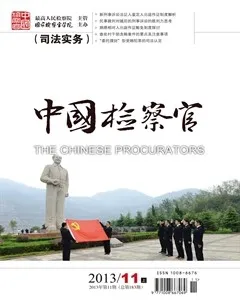民事裁判對隨后的刑事訴訟的既判力思考
一、民事裁判先于刑事判決的可能性論述
在我國,民法的調整對象是平等主體之間公民之間、法人之間,公民和法人之間的財產關系和人身關系。其中,財產既指金錢、物資、房屋、土地等物質財富,又指物權、知識產權、債權和債務。人身關系則是與人身不可分離、以人身利益為內容、不直接體現財產利益的社會關系,括人格關系和身份關系。[1]同時,我國刑法所調整的犯罪客體是我國刑法所保護的,為犯罪行為所侵害的社會關系,包括國家安全、公共安全、社會主義經濟基礎、公民的人身權利、民主權利和其他權利、社會主義社會管理秩序、國防利益、軍事利益等。我國民法和刑法在對人身關系和財產關系的調整上是有一定重合的。事實上,我國民法和刑法調整的都是社會關系,只是根據社會關系的重要性程度,分別運用民法或者刑法等其他規范予以調整。社會關系中的婚姻家庭、經濟秩序等社會關系一般采用民法予以調整保護,其中可能遭受嚴重侵害的,則由刑法予以保護。這樣,在婚姻關系、經濟秩序等方面的社會關系,在民法調整還是刑法調整的問題上,就可能出現法條竟合。由此可見,一個行為往往既觸犯了刑事法律,又導致民事上的損害賠償,或者行為處于民事違法與刑事犯罪的邊緣地帶。這樣,同樣的爭議事項可能既屬于民事訴訟管轄的范圍,又被納入刑事訴訟。[2]我國近年來在金融、經濟領域涌現出大量的民事違法行為,這是市場經濟發展進程中必然付出的代價。在經濟交往中,當事人往往為了實現和維護自己的經濟利益,對于一方當事人的犯罪行為很少向公安機關或者人民檢察院報案,特別是國家利益受損而當事人獲利的案件。而在其對民事解決的結果不滿意時,才會訴求刑事訴訟。[3]而由于當事人收集證據的局限性和刑事訴訟對證據要求的嚴格性,法院依據當事人提供的證據也只能判斷爭議事項屬于民事訴訟。例如以民間借貸為幌子的詐騙犯罪中,由于當事人持有借據等證據,在無法找到行為人時,從自身經濟利益考慮,往往持借據到法院起訴,法院根據當事人提供的證據就以民間借貸糾紛予以受理,并作出缺席判決。而在判決之后,行為人繼續隱匿,判決書也無法執行。同樣從自身利益考慮,當事人向公安機關報案,公安機關受理后認為該案屬于立案范圍,遂對行為人予以追捕。行為人歸案后,對其非法占有的故意予以供認,同時供認為逃避追捕,搬離原住處、改變原通訊聯系方式。這樣,根據公安機關掌握的證據,該案就屬于典型的刑事案件。檢察機關就該案向法院起訴時,就會面臨一個問題就是有關該爭議事項的民事裁判對隨后的刑事訴訟是否具有既判力。
二、我國現有解決民事裁判對隨后的刑事判決影響的法律淵源
1998年4月19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經濟糾紛案件過程中涉及經濟犯罪嫌疑若干問題的規定》第11、12條規定,人民法院作為經濟糾紛受理的案件,經審理認為不屬經濟糾紛案件而有經濟犯罪嫌疑的,應當裁定駁回起訴,將有關材料移送公安機關或檢察機關。同樣,人民法院已立案審理的經濟糾紛案件,公安機關或檢察機關認為有經濟犯罪嫌疑,并說明理由附有關材料函告受理該案的人民法院的,有關人民法院應當認真審查。經過審查,認為確有經濟犯罪嫌疑的,應當將案件移送公安機關或檢察機關,并書面通知當事人,退還案件受理費;如認為確屬經濟糾紛案件的,應當依法繼續審理,并將結果函告有關公安機關或檢察機關。這些規定都是針對民事案件審理過程中發現涉及刑事案件的處理辦法。
遺憾的是,以上司法解釋只是規定了在民事裁判作出之前的作法,但是如果在民事裁判已經作出并生效后,才提起刑事訴訟,則該民事裁判在隨后的刑事訴訟中應當具有何種效力,立法和司法都沒有給出明確的答案。
三、解決民事裁判對隨后的刑事判決影響的設想
實踐中,由于缺乏明確規定,各地對民事裁判對隨后的刑事訴訟是否具有既判力的態度各不相同。根據筆者不完全調查,福建、廣東深圳地區都不承認民事裁判對隨后刑事訴訟的既判力,認為即使就同一事項存在民事裁判,只要該事項事實上屬于刑律所調整,就應當予以受理。而在某市某區,法院以上述98年的司法解釋為依據,認為既然法院已經對爭議事項的性質作出確定,這種定性就具有既判力,刑事審判庭在民事審判庭未撤銷民事裁判之前,按照“一事不再理”的原則,不予受理。筆者認可第一種作法,理由如下:
(一)從案件受理的角度看,民事案件受理時對證據的要求低于刑事訴訟
我國民事訴訟法規定,法院受理起訴時,審查的內容包括實質要件和形式要件。所謂實質要件,就是1.原告是否是與本案有利害關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2.是否有明確的被告;3.是否有具體的訴訟請求和事實;4.爭議事項是否屬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訴訟的范圍和受訴人民法院管轄。所謂形式要件就是民事訴狀中要包括以下內容:1.當事人概況;2.訴訟請求和所根據的事實和理由;3.證據和證據的來源,證人姓名和住所。事實上,法院受理民事訴訟審查的內容中,不管是實質要件還是形式要件,都只是程序上的一種審查,不包括實體上的認定。而我國《刑事訴訟法》的86條規定,“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或者公安機關對于報案、控告、舉報和自首的材料,應當按照管轄范圍,迅速進行審查,認為有犯罪事實需要追究刑事責任的時候,應當立案”。顯然,由于立案往往涉及到行為人的人身自由,所以在受理時除了程序審查外,還要在實體上審查是否“有犯罪事實需要追究刑事責任”,要求明顯高于民事訴訟的案件受理。同時,民事訴訟中的證據不像刑事訴訟中的由公安司法機關主動收集、審查,而是由當事人提供,法院基于其客觀中立地位一般也不主動收集證據。這樣,一方面民事訴訟的受理起訴門檻較低;另一方面民事訴訟中的證據來源狹窄,因此,不能夠要求民事法官對于自己所受理的每宗案件中的刑事因素都有充分考慮而予以移送,更不能以民事法官對爭議事項已作民事裁判而排除刑法的適用。
(二)從證據標準的角度看,民事訴訟奉行優勢證據,而刑事訴訟執行排除合理懷疑的原則
近年來,有些學者開始對證據標準進行比較深入的研究和務實的探索,明確了刑、民訴訟采取不同的證據標準。在刑事訴訟中,為了證明刑法所規定的犯罪構成的實體要件,應采取嚴格的證明標準,僅僅證明某人可能實施了犯罪行為是不夠的,要認定其有罪或者無罪,就必須進一步得出唯一結論,要達到排除一切可能的標準。而在民事訴訟中,如果全案證據顯示某一民事法律關系存在的可能性,明顯地大于其不存在的可能性,盡管還沒有排除其他可能,但在沒有其他證據的情況下,法官也應當可以根據現有的證據認定這一事實。[5]很顯然,沒有理由用一種證明標準較低的訴訟對一種證明標準較高的訴訟施加既判影響。
(三)從訴訟主體的角度看,民事訴訟的主體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而刑事訴訟的主體一般以國家提起訴訟為主
在我國,民事裁判的雙方當事人都是該爭議的民事法律關系的主體,除對生效裁判的抗訴外,國家不會涉入民事糾紛。而刑事訴訟則分為公訴與自訴兩種,公訴案件由國家公訴機關代表國家的利益提起訴訟,與之前的民事訴訟在主體上具有不一致性。因此,民事訴訟和隨后的刑事訴訟中就同一事項進行爭訟的主體是不一致的,即使在民事訴訟中作為公民的起訴方敗訴,也不意味著在刑事訴訟中作為國家公權力代表的國家公訴機關也必然無法就同一爭議事項承擔證明責任。因此,無論前訴的結果如何,都不會影響隨后的刑事訴訟,即民事裁判對刑事訴訟沒有既判力。[6]
注釋:
[1]魏振瀛:《民法》,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9-10頁.
[2]李哲:《刑事裁判的既判力研究》,載《中國政法大學博士學位論文》.
[3]同上.
[4]李浩:《民事舉證責任研究》,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223頁.
[5]常怡:《民事訴訟法學》,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217頁
[6]同[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