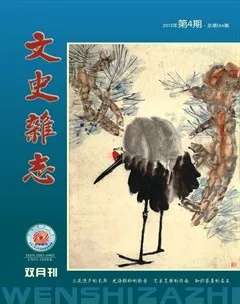《三國志》的敘事編排
2013-12-29 00:00:00墨非
文史雜志 2013年4期
讀司馬遷《史記》,會發現有一種大一統歷史觀貫通其間。而此后它便被史家所繼承,一直貫穿于《史記》以降的中國封建社會的古史典籍中,成為中國史學的一條光彩奪目的生命長鏈。
譬如我們今天讀西晉巴西安漢(今四川南充北)陳壽所撰《三國志》,便充分感悟到里面所強烈跳動著的大一統歷史觀的脈搏。眾所周知,三國的史事有分有合,三國的地位有輕有重,陳壽度量權衡,特為魏帝立紀,作為全史之綱,表明當時雖是“三國鼎立”,但祖國的歷史仍然統一。而一部《三國志》留給讀者的感受,也是一部完整統一的中國斷代史;雖分三國別立三書,只是敘事編排的方式而已。
我們讀《三國志》,深切地感到天下一統的歷史趨勢不可阻擋。《三國志》批評荀彧既為曹操第一謀臣,卻又死抱住東漢皇朝的僵尸不放,不能與時變化;贊揚王朗等人積極佐曹代漢,“誠皆一時之俊偉也”(《三國志·魏書·鐘繇華歆王朗傳·評》)。陳壽將東漢年號下二三十年間的歷史寫入《三國志》中,表明并不留戀徒具空名的東漢王朝。這無疑沿襲了司馬遷的大一統歷史觀。此外,陳壽還繼承了司馬遷不趨時俗,獨立思考和尊重歷史的史德。他為曹操立紀,而用漢朝末帝獻帝的年號編年紀事,說明重史實而輕名份。此外,《三國志》雖為魏帝立紀,但并不以吳、蜀為僭偽。當吳、蜀既滅,晉朝人士目為偽朝之時,陳壽卻將它們與魏并稱“三國”,各寫一書;又在其帝王傳中編年紀事,與帝紀無異。至于《三國志》的卷數安排:《魏書》30卷、《吳書》20卷、《蜀書》15卷,則是依據三國各自擁有的歷史地位或歷史分量而作出的,不應當看作是厚此薄彼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