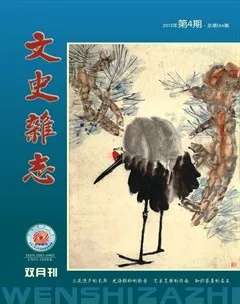《列子》中的兩則歌唱家故事

列子是我國春秋時期的思想家,是老子和莊子之外的又一位道家思想代表人物,與鄭穆公(《史記》稱“鄭繆公”,在位時間是公元前627年—公元前606年)同時。其學本于黃帝老子,主張清靜無為。東漢班固《漢書·藝文志》“道家”部分錄有《列子》八卷。《列子》又名《沖虛經》,是道家重要典籍。今天我們所見到的《列子》全書共載民間故事寓言、神話傳說等134則,題材廣泛,有些頗富教育意義,其中兩則關于歌唱家的故事就是如此。
一、韓娥:“余音繞梁,三日不絕”
“余音繞梁,三日不絕”是一個出自《列子·湯問》的成語,原文是:“昔韓娥東之齊,匱糧,過雍門,鬻歌假食。既去而余音繞梁,三日不絕,左右以其人弗去。過逆旅,逆旅人辱之。韓娥因曼聲哀哭,一里老幼悲愁,垂涕相對,三日不食,遽而追之。娥還,復為曼聲長歌。一里老幼喜躍抃舞,弗能自禁,忘向之悲也,乃厚賂發之。故雍門之人,至今善歌哭,放娥之遺聲。”它講的就是戰國時期民間音樂家韓娥的故事。
戰國時期,韓國有位歌唱家名叫韓娥,她要到位于東方的齊國去。當她風餐露宿,到達齊國都城西邊的雍門時,已經斷糧好幾日了,不得不用賣唱來換取食物。韓娥唱起歌來,情感相當投入,以至在她離開了這個地方以后,美妙絕倫的余音還仿佛在城門的梁柱之間繚繞,竟至三日不絕于耳。
有一天,韓娥來到一家旅店投宿時,店小二見她窮愁潦倒,便當眾羞辱她。韓娥為此傷心至極,禁不住拖著長音痛哭不已。哭聲彌漫開去,竟使得方圓一里之內的人們,無論男女老幼都為之動容,都難過得三天吃不下飯。
后來,韓娥難以安身,便離開了這家旅店。人們發現之后,急急忙忙分頭去追趕她,將她請回來,再為大眾縱情高歌一曲。韓娥的熱情演唱,又引得一里之內的老人和小孩歡呼雀躍,鼓掌助興,忘情地沉浸在歡樂之中,將以往的許多人生悲苦都一掃而光。為了感謝韓娥給他們帶來的歡樂,大家送給她許多財物和禮品,使其滿載而歸。
韓娥的故事說明:好的聲樂是具有強烈的感染力的,是可以做到“余音繞梁,三日不絕”的。一個真正的歌唱家,就應當扎根于人民大眾之中,與大眾共悲歡,成為他們忠實的代言人。
二、秦青:“聲振林木,響遏行云”
“聲振林木,響遏行云”這個成語也來自于《列子·湯問》,原文是:“薛譚學謳于秦青。未窮青之技,自謂盡之,遂辭歸。秦青弗止,餞于郊衢,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云。薛譚乃謝求反。終身不敢言歸。”講的是戰國時期的音樂家秦青、薛譚的故事。
戰國時期的秦國人秦青善歌,以教歌為業,他曾收薛譚為徒。薛譚非常聰明、好學,嗓音又格外甜美嘹亮,學業很優異。學習了一段時間后,薛譚覺得自己對歌唱的決竅掌握得已經不錯了,就想辭別老師,自己去獨立演唱。秦青聽到薛譚講出自己的想法后,想了想說:“你的確已學得不錯了,十分的技藝,你已掌握了七八分。但如果能再學習一段時間,可能會更有進益。”薛譚聽到老師這樣講,覺得低估了自己的能力。秦青也看出了他的心思,微笑著對他說:“好!既然你決心已下,我亦不再阻攔你。我們師生在一起情分不薄,明天我略備薄酒給你送行。”
第二天一早,天空格外晴朗,微風拂面,送來陣陣花香,師徒二人不緊不慢地邊走邊聊。秦青對薛譚說:“送君千里終須別,自此之后,我們二人不知何日才能相見。我當長歌一曲,為你送別。”說完以后,秦青用扇子打著拍子,放聲歌唱了起來:“春風拂面啊送花香,傷別離啊心惶惶。天涯海角啊難相見,人隔千里啊共嬋娟。”歌聲高昂、激越,直上云霄,振動了林木,使森林發出嗡嗡的回響;遏止住天上飄蕩的白云,使它們也停了下來,靜靜地傾聽。這就是我們后來所說的“聲振林木,響遏行云”。
薛譚被這美妙的歌聲所打動,如醉如癡,好半天才醒悟過來。他感動地說:“老師,我不走了,要永遠在您身邊,終身苦學不輟,把您的全部技藝都學下來。”薛譚留下來繼續學習,后來與老師秦青齊名,都是當時著名的歌唱家。
秦青、薛譚的這則故事告訴我們:音樂的學習也應該是“學而不厭”,不應當“淺嘗輒止”,因為“學無止境”啊!還有秦青不是空講大道理的教育方式和薛譚那知錯能改,變驕傲為虛心的學習態度,也值得今人借鑒。
三、音樂是思想情感的表達
由于《漢書·藝文志》所著錄的《列子》八卷早佚,所以,今本《列子》八卷,從思想內容和語言使用上看,很可能是后人根據古代資料編著的,據說是晉人偽作;所以,有人就認為今本《列子》所載韓娥、秦青的傳說故事可能不全準確。不過,西漢劉安的《淮南子》卻承認他們的存在,并對他們的歌唱藝術有過精辟的分析。
《淮南子》又名《淮南鴻烈》,是西漢初年淮南王劉安召集門客,于漢景帝、漢武帝之交時撰寫的一部論文集。劉安(公元前179年—前122年)是漢高祖劉邦的少子淮南厲王劉長之子。淮南厲王因“謀反”獲罪,流徙途中絕食而死,后淮南厲王的封地被一分為三,劉安被策封為淮南王。劉安曾羅致賓客數千人,內中不乏碩學之士,共同編定《淮南子》一書。全書博奧深宏,融道家、陰陽家、墨家、法家、儒家思想于一體,但主要是發揮先秦道家思想,是漢代學者對漢以前的古代文化一次最大規模的匯集與融合。《淮南子》通篇主題為“道”,既講自然之道,也講治世之道,提出了“漠然無為而無不為”,“漠然無治而無不治”的政治理想。《漢書·藝文志》載《淮南子》內21篇,外33篇,今只流傳21篇。該書最后一篇名《要略》,是全書的序言。從《要略》看,全書寫作有統一的計劃和安排;但從內容看,并未完全統一。《漢書·藝文志》把它列入“雜家”是有道理的。著名歷史學家范文瀾先生評價說:“《淮南子》雖以道為歸,但雜采眾家,仍表現出一定的融合傾向。”
在《淮南子》卷十三《氾論》中,它說:“譬猶不知音者之歌也:濁之則郁而無轉,清之則燋而不謳。及至韓娥、秦青、薛譚之謳,侯同、曼聲之歌:憤于志,積于內,盈而發音,則莫不比于律而和于人心。何則?中有本主以定清濁,不受于外而自為儀表也。”
這就是說,韓娥、秦青、薛譚等歌唱家之所以能在歷史上留下影響,關鍵在于他們有內心的思想情感需要表達。這種思想情感到了不可抑制的程度,沖出來的就是歌聲。而且正因為他們是按照內容的要求來控制聲音的清濁變化,而不是單純去追求聲音外在的美,所以才能既有符合聲音變化規律的美的形式,又能夠深深地打動聽眾的心靈,有近乎神奇的藝術魅力。
據《史記·樂書》的記載,其實,早在韓娥以前,當孔子學生子貢去拜見音樂家師乙時,師乙就對歌唱藝術表達過重視歌曲內容并運用相應的技巧與美的聲音去把它表現出來的看法。他說:“夫歌者,直己而陳德;動己而天地應焉,四時和焉,星辰理焉,萬物育焉。”而且他還進一步指出了聲音美必須要達到“上如抗,下如隊,曲如折,止如槁木,居中矩,勾中鉤、累累乎殷如貫珠”。這說明當時對于歌唱藝術是有一定要求的。韓娥等歌唱家就是因為達到了這樣的水平,所以才得到《淮南子》作者的贊賞和推崇。而《淮南子》對韓娥、秦青、薛譚的肯定,他們的故事該是基本可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