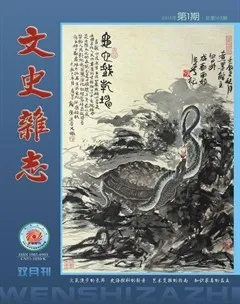信處叫好,疑處商榷
一、“若木就是攀枝花樹”經得起推敲
1. 話不離譜
前段時間,我從互聯網上盡可能全面搜索并認真地拜讀了攀枝花市王文君、劉勝利、劉成東等先生的文章。他們提出“顓頊出生地在金沙、雅礱、安寧三江匯合處”的觀點和理由非常誘人,讓我耳目一新,受益匪淺。在我淺陋狹窄的見識范圍內,他們這個說法,是眾多“顓頊故里”主張中最為靠譜的一個。
我所謂的“譜”,指的是古今學界公認的歷史地理經典與基本取得共識的定論,是可供大家討論說話的概念和定義。
在討論“顓頊故里”這個話題時,我們須先認可《史記》倡說的“黃帝之子昌意降居若水”、“娶了蜀山氏女生了顓頊”以及現代學者(如鄭德坤、任乃強、段渝)所推論的“古蜀在四川”、“若水指的是雅礱江”、“若水得名于若木”等一系列前提。
2. 若木脫魅
對“昌意在若水生了顓頊”這一命題應該說基本是沒有爭議的,爭議發生在究竟生在若水的哪一段。兩千多里長的若水,給古今“覬覦帝位”的人提供了廣袤無垠、穿鑿附會的想象空間。盡管紛紜不斷,迄無定論,但我感到通過攀枝花市學者們的努力,他們在一步一步接近那個“哥德巴赫猜想”。他們提出的“若木就是攀枝花樹”的觀點,朝解決問題的方向進了一大步。[1]
還是從《山海經》那段著名記載說起:“南海之內,黑水之間,有木名曰若木,若水出焉。”袁珂按:“《水經注·若水》云:‘若木之生,非一所也,黑水之間,厥木所植,水出其下,故水受其稱焉。’”[2]
這段材料提示我們,若水的得名一點也不神秘。以植物命地名的做法至今在廣大農村仍然非常普遍。比如“白楊溝”、“苦蒿溝”、“漆樹溝”之類地名,各地俯拾皆是。其地之所以得名,必是那些植物特別多,特別典型,成了一種“地標”。反之,如果僅有一二株白楊、苦蒿在那里煢煢孑立,形影相吊,則斷不會因它們而得名的。
那么,一條巨大的江河因若木所植而被稱為若水,這里的若木必定具有非常強大的陣容,有極其醒目的色彩,以迥異于其他樹木。
有幸我對攀枝花樹非常熟悉,小學時在西昌生活,教室外就有幾株。所以當我一看見攀枝花市學者提出“攀枝花樹就是若木”的文章時,簡直有一種醍醐灌頂之感,因為它實在是太符合歷代典籍對若木的定位與描繪了。
首先,攀枝花樹普遍生長在若水末端三江匯集這一帶。當然,“若木之生,非一所也”,云南、廣東、海南也有,但它們與若水無緣,也就與這場討論無關。
其次,攀枝花樹形態處處與經典描述吻合,讓我們找幾段來按圖索驥——
《山海經·大荒北經》:“灰野之山,上有赤樹,青葉,赤華,名曰若木。”
《淮南子·地形訓》:“若木在建木西,末有十華,其華照下地。”
郭璞詩《若木贊》:“若木之生,昆山是濱。朱華電照,碧葉玉津。食之靈智,為力為仁。”
這些描述突出幾個特征:(1) 花紅、花多(華赤、朱華、十華。十,多的意思,古文中與九、三同)。(2) 高大(其光照下地)。(3) 碧葉。(4) 可食。
我們來看看現實中的攀枝花樹:
(1) 大紅花。世上紅花繁多,但巨大喬木開大紅花者,恐怕絕無僅有。縱令有吧,還得長在若水邊才算數。從雅礱江源頭走到末尾,除了攀枝花樹,誰也沒有入選的條件。它開花時沒有葉子,朵如玉蘭形,色如榴花紅,光禿禿枝條上雄赳赳立滿朱紅色花朵,整棵樹如一把巨大的火炬,故又稱“英雄樹”。
(2) 高大。攀枝花樹最高者達數十米,拔地參天。樹身數人圍,樹冠可蔭蔽一二畝,真正是喬木界之驕子,遙望如垂天之云,實在有點嚇人。
(3) 碧葉。花季過后,滿樹油綠濃蔭,蔭蔽之廣,其它樹木難以企及。
(4) 可食。從小就見同學用彈弓把花打下來(因滿身刺釘,爬不上去),說拿回去燴臘肉。
通過以上脫魅后的類比歸納,若木與攀枝花樹的身影就重合了。
我們可以推想,先民們在一個明媚的春天,突然走到三江匯合一帶,正碰上攀枝花怒放,只見萬山紅遍,層林盡染,轟轟烈烈,攝人心魄。為了記住這個地方,用這些最具地標特征的樹木給腳下不知名的江水命名,實在是一件符合野外生活常識的平凡事。
脫掉若木神秘外衣,相信典籍,相信客觀世界,若木非攀枝花樹莫屬。
3. 聚焦攀西
一直以來,搜索顓頊蹤跡的人們多把目光集中在川西北岷山、岷江一帶(即古蜀),因為文獻與考古都印證了這里的文化與甘、青氐羌馬家窯文化有著明顯的聯系;而以西昌禮州文化為代表的攀西古文明則更多的是與元謀大墩子文化相聯系。(參見段渝《四川通史》卷一)。現在,經“攀枝花樹即若木”的提示,我們有理由把目光南移到若水的末端來。
再考《山海經》里的“黑水之間”。金沙江古稱瀘水,“瀘”是黑的意思;若水的“若”,彝語也是黑的意思;安寧河古稱孫水,西昌、冕寧一帶人讀若“深水“。這就是對《山海經》黑水的有力證明。其實從中國的東北到西南,名黑水或意思是黑水的大江大河不下數十條,無非是說水大水深、顏色墨綠而已。這里三江匯集,黑作一團,其中以若水最為有名,于是由它來代表這個區域。金沙江雖然最大,但古人只把它當作若水的支流;同理,橫斷山諸江都比岷江大,但古人把它們統統看作岷江的支流,蓋因古人認為岷江才是大江(長江)的正源。這說明古人對橫斷山以西的河流缺乏了解,越向西越生疏。無怪清人陳澧在他的《水經注西南諸水考·序》中批評酈道元“身處北朝,其注《水經》,北方諸水,大致精確,至西南諸水,則幾乎無一不誤。”東晉郭璞注《山海經》而言若木“生昆侖西,附西極”,恐怕這“西極”也不出橫斷山以西。所以我們可以說三江匯集處就是“若三角”,它在整個若水流域中占有非常特殊的地位。它很有可能就是昌意若水領地的治所。
馮廣宏先生還提出一個觀點,認為漢《水經》里的若水其實是安寧河,只不過在古代主流與支流名稱常被混用。[3]這是一個很有意義的提示。安寧河谷絕對是人類早期發育不可多得的搖籃,從冕寧到米易一馬平川,沃野幾百里,陽光充足,水流豐沛,是四川的第二大糧倉(正像西昌人宣傳的“人居環境,世界第一”)。任乃強先生在《四川上古史新探》里推測說,這里開發時四川盆地還是一片汪洋,元謀人離它那么近,北上必定最先開墾。昌意管轄若水會放過這片山水相連的膏腴之地嗎?所以說“若三角”至少包括了安寧河下游也是很自然的事。
還有個例子似乎可以為馮廣宏先生的“主流與支流名稱混用說”提供一個旁證。我曾在瀘沽(古臺登)小住,一直對《史記》關于司馬相如在此“橋孫水”(安寧河上架橋)的記載百思不得其解。孫水關遺址并不在安寧河邊,而是在安寧河東岸一條支流上,離安寧河約3公里處的“瀘沽峽”。瀘沽人對這條從喜德縣流出的小河才叫“孫水”,絕沒有人叫安寧河為孫水。這里是靈關古道上的險關要隘,遺跡頗多。司馬相如南征從此進入安寧河道,在這個小孫水上“橋”一下是必要的,也是辦得到的,然后他只要順著安寧河東岸廣闊原野上的大道就可以直抵邛都(西昌)。可是《史記》卻要他“橋”那個大孫水(安寧河),跑到地形極為不便的西岸,然后必須再在下游某個地方第二次“橋”一回孫水,才能回到北岸的西昌。豈非咄咄怪事!再說,安寧河那么寬的水面,那么湍急的流速,漢朝時是否有那架橋的技術,著實可疑。所以我也覺得“小孫水”才是孫水,“大孫水”其實是若水。那么雅礱江是什么水呢?可能就是什么青水、黑水吧?
綜上所述,三江匯合處的“若三角”(包括米易)有若木、有若水、有黑水、有豐腴的安寧河谷,可以說空間條件完全具備,顓頊故里,呼之欲出了。
二、諸多疑難仍須解決
通過指認“若木就是攀枝花樹”而把顓頊故里的范圍縮小已經算是有了很大的進步,但如果認為一切問題已經迎刃而解,那就未免過于樂觀。畢竟,即使解決了“若水命名地”仍然不等于就解決了“顓頊出生地”,二者之間還有很大的差距。至于那些把各種傳說一一穿鑿、坐實的做法,精確的坐標、言之鑿鑿的生動敘述,不僅無助于取得更廣泛的認同,反而會作繭自縛,難以自圓。[4]須知我們探討的對象是一個生活在四千年以前的古史傳說時代的人,他的詳細生平,至今尚無令人信服的文獻或考古成果予以支持。所以,對他的描述模糊和籠統是正常的,清晰準確反而是不正常的。以下提出一些問題與攀西當地學者商榷:
1.時差拷問
既然“昌意降居若水”,那么若水得名自然比昌意早;既然若水得名于若木,那么若木得名則更早。假設昌意在入川之前幾百年若水就已經得名,那么到他“降居”時,這個若水名稱就可能覆蓋雅礱江全程。他從上游到末端的過程是逐步浸潤擴張呢,還是奉王命急宣,急如星火走馬上任呢?當然,我們希望是后者,而且是直奔雅礱江出水口的“治所”。可惜我們無法排除前者的可能性。如果他的愛妻蜀山氏早已身懷六甲,在艱苦卓絕的漫漫長征途中,在雅礱江的某段停下來生個孩子,難道就不可以嗎?畢竟,若水不是他命名的,他也很有可能不知道什么是若木,若木片區在哪、若水命名地在哪,理想中的棲息地“若三角”也可能是事業做大后的結果,這些,都有可能。總之,若水命名與昌意降居之間的時間差可以生發出太多的可能性,除非我們有足夠的證據排除他中途停留。當然,在諸多可能性中,昌意直奔主題的可能性很大,因為“若三角”不僅有神奇的若木,是著名的命名地(假設他預先知道這些),而且廣闊富饒美麗,或許就是若水流域的首府等等;但這些“可能”盡管合情合理,畢竟是推測,無法排他,立論的基礎顯然薄弱。
2.關于米易的大石文化
攀枝花市學者提出本地區眾多的大石文化(濮人墓)以印證昌意、顓頊的足跡。這個問題,其實已經基本得到解決。根據考古結論,安寧河谷的大石墓,屬本地邛都夷文化。它上起商代,下迄西漢,源接新石器晚期的禮州文化,屬于元謀的大墩子文化,根子在南方而不在北方。(參見鄭德坤:《四川古代文化史》;段渝:《四川通史》卷一)而黃帝文化屬仰韶文化,經甘青馬家窯文化進入川西北,然后向南方輻射。
3.關于“在本地娶蜀山氏女”
攀枝花市學者認為:“昌意從中原帶來的人馬……是到了這里后才娶蜀山氏之女為妻的。”她就是“當地少數民族的女子”。我想說,持此論一是缺乏根據,二是沒有必要。蜀山指的是岷江上游的岷山,這基本上已是公論,特別是得到近些年來考古成果的有力支持。昌意到了阿壩,娶了當地蜀女,邏輯上并不影響他繼續順若水南下開拓進取,也不影響他夫妻二人走到攀枝花市才生娃娃。
4.關于“顓頊治水經驗于此地積累”
攀枝花市學者認為:“顓頊從小生長在若水、繩水、孫水三江交匯處”,所以最終能“以水德王天下”。大家都說顓頊10歲就離開若水去了中原,一個孩提能積累多少治水經驗?再說眼前這三條大江,都不是古人可治之水。高山峽谷,既無泛濫之虞,也不必從大江大河討飯吃,山溝水都用不完,攀西一帶至今基本如此。顓頊的治水本領,還是放在黃河流域積累才合情理。顓頊、鯀、禹祖孫三代治水本領、治水地域一脈相承。這關鍵還不是推理是否嚴密,而是并沒有證據。
5.關于當地“獨特的民俗和龍文化”
攀枝花市學者描述了米易本地許多古老而獨特的民風民俗,把它們與顓頊文化相聯系。其實,這些描述與本地土著濮文化更加接近。這些文化源接元謀文化,比從北來的昌意、顓頊更加悠久,對本地歷史發展貢獻更大,更應該贏得尊重,沒有必要把他們硬掛到顓頊的名下。
攀西(包括米易)的歷史文化資源如此豐厚,可供開發利用的“招數”多多益善,何必把所有好牌都塞給顓頊一人呢?“若木就是攀枝花樹”這張靠得住的王牌一出,其他各地“顓頊故里”主張已經無與爭鋒。打好這張牌,保護培植好這棵寶樹,無論在文化、經濟方面都有大文章可做。至于推進、完善“顓頊故里”的理論,盡可從從容容、心平氣和、實事求是去做。結果如何,不急。
注釋:
[1][4]參見王文君:《一朵花的神話》;劉勝利:《顓頊誕生地初探》、《顓頊誕生地再探》;劉成東:《顓頊大帝與顓頊故里龍文化(上、下)》、《若木 若水 后稷》。
[2]袁珂:《山海經校注》第447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3]參見馮廣宏:《顓頊史跡及其改革作為考》,《阿壩師專學報》2006年第1期。
作者單位:滎經中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