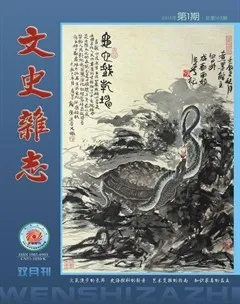哪吒神形象的文化符號學解讀
一、哪吒神形象的文化符號學內容
1. 文化符號學內涵
符號學,顧名思義,就是研究符號的科學,更具體地講,“符號學是系統地研究語言符號和非語言符號的學問”。符號學是研究符號意指作用的科學。符號的種類有圖像、標志、象征等。“確定符號學的恰當地位,這是心理學家的事,語言學家的任務是要確定究竟是什么使得語言在全部符號事實中成為一個特殊的系統。……語言比任何東西都更適宜于使人了解符號的性質。……語言的問題主要是符號學的問題”[1]。符號傳播的要素包括指代對象、符號和編碼、傳播手段、發送者和接收者。符號學的功能有指代功能、情感功能、指令功能或表意功能、詩歌功能或美學功能、交流功能、元語言功能、理解與感覺、意義與信息、注意與參與等。[2]
什么是符號學中的文化?按照莫斯科-塔圖學派的定義,文化是信息的生產、流通、加工和儲存的集體符號機制。因此,文化被看作符號系統,文化是人類的符號活動,是文化系統中各子系統和各層面之間的互動,是“信息的生產、流通、加工和儲存的集體符號機制”[3]。
關于文化文本,莫斯科-塔圖學派的代表人物洛特曼(Yuri Lotman)認為,文本是“文化的縮小模式”(text asa“reduced model of culture”)。文本具有文化特色,具有民族特點,為特定民族的心理模式。文化符號學的文本是信息,是信息的生產、傳遞和儲存,是一種產生意義的復雜的和互動的符號活動。
2.哪吒神形象的文化符號學內涵
哪吒神形象的來源。哪吒,梵文全名那羅鳩婆(Nalakūvara或Nalakūbala),也譯作哪吒俱伐羅。哪吒神的原創是佛教,后經過本土化,成為中國道教文化中的兒童神話人物。哪吒作為神話英雄人物與其他神話一樣,也經歷了真實—故事—傳說—神化的發展過程,最后走上了神壇。哪吒神形象演化為玉皇大帝的戰將,孩童天神,神通廣大,而本相仍是三頭六臂,道教神形象。
哪吒神形象的文化符號學內涵。哪吒神形象的文化符號學是指以哪吒神為依據,通過系統地研究語言符號和非語言符號來解讀道教文化的精神實質,為文化的傳承與發展服務。哪吒的文化文本形成的機制(模式化系統)可以看作符號系統,看作廣泛符號意義上生產文本的一組規則(規則、指令、程序),也可看作多種文本的總合及相互間的功能。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哪吒神形象的主要模式化系統和次要模式化系統。哪吒神形象的主要模式化系統是隨著北方毗沙門天王演化為李靖,而作為北方毗沙門天王的三太子逐漸中國化。李靖是唐朝的軍事家,在唐朝已經被神化。哪吒在古印度原始的基本形象是三頭六臂的兇惡夜叉神、佛教忠誠的守護神。忿怒、兇惡是哪吒神形象在這一時期的性格與外表特征。哪吒神形象到南宋時期演化成為中國正神;明代神魔小說盛行,在《西游記》中哪吒是一位清妍、聰穎、精勇、神奇的孩童道教神仙,身帶六種神器,法力無邊;在《封神演義》中完全成為道教神形象。哪吒神形象的次要模式化系統是指哪吒的外部形象,主要表現在發型、五官、服飾和兵器等道教特征上。各民族(如漢族、羌族、白馬藏族等)依據自身的民族心理對哪吒形象的外部特征表現略有不同。
哪吒神形象作為次要模式化系統的藝術特色。從哪吒神形象的藝術特色來看,主要是語言符號和圖像兩個方面。哪吒神形象在語言符號中表現為民間故事、評書和神魔小說。圖像符號主要為繪畫、雕塑(神像)、戲劇、影視等表現方式,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張仃先生筆下的哪吒神形象,是一個矯健活潑,機智勇敢,英俊、明慧,有思想、有感情、有尊嚴的現代中國的兒童形象。[4]
哪吒神形象的文化符號學包括四個方面的內容。首先,符號范圍(semioshere)。哪吒神形象適用范圍主要是宗教(道教)文化和民俗文化。其次,互文性符號活動(in-tersemiosis)。由語言符號文本和圖像符號文化構成哪吒神形象的文化符號,即在人們頭腦中形成的栩栩如生的小神仙。其三,邊界(boundary)。指能夠接受哪吒神形象的文化符號的人。最后,信息的產生。哪吒神形象的文化符號以文本形式進行傳播。
二、哪吒神形象的文化符號學指示意義
1.哪吒神形象的文字符號是情感表達的載體
哪吒神形象源自佛教,經過神魔小說的藝術創造,產生了具有民族特色的藝術形象。
宗教本身就是人們對地理環境體驗的心理表現形態。哪吒神的外道內佛形象從表面上看是兩種宗教的整合,是民族文化對外來文化的創造性吸收,實質上是明末人們復雜心理的表達,或心理寄托。人們希望有像哪吒一樣的救世主出現,來拯救苦難的人民,保護百姓的平安,這是哪吒神形象深受人們喜愛、在民間廣泛傳播的主要原因。
為了將人們的精神需要表現出來,哪吒神形象是恰當的表達符號,在古代最好的方式是以漢字為工具,用神魔小說這種語言形式來表達。
2.哪吒神形象的民俗符號是傳統文化的展示
哪吒神形象同時也是一種民俗符號。“民俗符號作為民俗的表現體,是用某一個民俗事物作代表,來表現它所能表示的對象,并由相應背景中的人們做出公認的解釋,指明其含義或概念的一種特殊符號。”[5]民俗符號的顯著特點是它的通俗性和易讀性。
3.哪吒神形象的傳播符號是民族文化傳承的體現
哪吒神形象的傳播符號主要是文字符號和圖像符號。各民族依據自身的心理需要、審美特征、文化發展的程度與文化傳承的需要,形成了各具特色傳播符號。
哪吒神形象的圖像符號具有明顯的地域性、民俗性和時代性,形成了完整的圖像符號系統。其中的民俗性是指哪吒神形象在造像過程中主要是當地民間藝人依據人們的審美俗成創造出來的神祇,民俗性濃郁。而時代性則是所有的神祇造像的共同特點。哪吒神形象也不例外,在不同時代,有不同的特點。
4.哪吒神形象的崇拜符號是民族精神的一種寄托
人們為什么要將哪吒神形象作為崇拜符號,是因為哪吒身上所具有的正直、善良、勇敢、堅強的精神,這正是我們的民族精神的主要內容。同時,哪吒身上那典型的孩子天生性格:活潑機靈、調皮可愛和逆反心理等深受兒童喜愛。綜觀哪吒的行為,我們可以看到一個真正的叛逆的精靈,看到一個鮮活獨立的生命意志——這才是哪吒作為民俗神的真正意義。
5.哪吒神形象的教育符號是激勵兒童成才的一種榜樣
哪吒神形象的教育符號是以民俗文化的形態作為教育內容,通過對一代代兒童的教育激勵其成長的榜樣。哪吒神形象隨著歷史的發展,經過不斷創造,始終成為深受少年兒童喜愛的英雄形象。尤其是近三十年來,隨著美術和影視業的快速發展,不同的哪吒形象,共同闡述了哪吒符號的內容,滿足了兒童好奇心的需求。
三、文化融合與傳承中的哪吒神形象
1.哪吒神形象在文化融合中的差異性
哪吒神形象符號地域差異。哪吒神形象在四川江油是英俊少年,在河南是胖小子,在西北地區更接近古印度原型,在港澳臺地區則成了身體強壯的大男孩。
哪吒神形象符號宗教差異。在國內外的差異方面,古印度的哪吒神形象是兇神惡煞的佛教護法神,而在我國則是降魔除妖、外道內佛、天真活潑,具有叛逆精神的少年英雄神。
2.哪吒神形象符號在文化融合中的獨特性
哪吒神形象符號體現了對待外來文化態度的包容性。大唐帝國綜合國力強大,文化方面呈現出繁榮的景象。道教文化面對外來的佛教不是采用抵抗,而是研究其優劣,不斷吸取其有利于發展的成分,使自身得到進一步的發展。陳寅恪先生指出:“綜觀二千年來道教之發展史,每一次之改革,必受一種外來學說之激刺,而所受外來之學說,要以佛教為主。”[6]哪吒神形象符號的形成過程就是對待外來文化態度的包容性的表征。
哪吒神形象符號傳播方式的宗教性和民俗性。哪吒神形象符號的傳播是通過佛教傳入,然后經過道教的改造,最終成為道教神祇。另一傳播方式是民俗性。從明朝到現在,哪吒神形象符號的傳播主要是以民俗文化形態方式進行的。其中最主要的是通過故事和評書在民間廣泛傳播。
哪吒神形象本土化過程的創新性。哪吒神形象由原來的古印度佛教護法神,經過南宋時期由“李靖演化為毗沙門天王,哪吒自然也就成了李靖之子”;明朝“在神魔小說《西游記》中,哪吒演化為孩童天神,他是道教玉皇大帝的天兵統帥托塔李天王的太子和主要戰神,神通廣大,外道內佛”;在神魔小說《封神演義》中“由外在道教內里佛教的神演化為純粹的道教神”。[7]從哪吒神形象的演變過程可以看出,神話人物雖然飄渺神秘,但仍然是根據現實需要來創造的。從另一方面看,哪吒神形象是宗教意識在人們頭腦中經過反復創造所產生的文化符號的結果。
3.哪吒神形象在文化融合中的民族性
哪吒神形象的創新過程是以文化的融合發展為前提,以民族性為內核的文化發展過程。《封神演義》中的哪吒蓮花化身故事是由幾個佛教故事原型演化、組合、變形而成的,而道教因素的介入則徹底改變了初始情節的性質,這為我們理解中國宗教史上的佛道關系問題提供了鮮活的形象演示。[8]因此,講民族性不是說要固步自封,而是要不斷吸收新鮮血液、不斷創新,這才是民族性得以保持和彰顯的源泉。
4.哪吒神形象的靜、動態傳承
哪吒神形象的文化符號是外在的形象與內在的精神之間的統一,從而形成人們頭腦中的相對穩定的形態。這體現出文化傳承的一種靜態面貌。文化在傳承過程中與人文地理環境相結合,不斷賦予新的內涵,使之符合不同時代人們的思想意識形態,寄予人們的思想、情感和期望,這就是文化傳承的動態表現(與靜態面貌相對應)。哪吒神形象在民間的傳承正是如此進行的。無論時代如何變遷,哪吒神形象都受到人們的喜愛,這就是文化傳承動態變化的作用。
哪吒神形象的符號是靜態與動態變化相互儲存、相互作用的統一體。靜態是相對的,暫時的,是文化傳承的穩定形態;動態是絕對的,永久的,是文化傳承的變化形態。
注釋:
[1]索緒爾:《普通語言學教程》,商務印書館1982年版,第37—39頁。
[2] 參見皮埃爾·吉羅著,懷宇譯《符號學概論》,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8年版,第2頁。
[3] 郭 鴻:《文化符號學評介》,《山東外語教學》2006年第3期。
[4]參見布文:《關于哪吒的形象》,《服飾》1980年叢刊第1期。
[5] 茍志效、陳創生:《從符號的觀點看——一種社會文化現象的符號學闡釋》,廣東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74頁。
[6] 陳寅恪:《金明館叢稿初編》,上海古籍出版 1980年版。
[7] 劉文剛:《哪吒神形象演化考論》,《宗教學研究》2009年第3期。
[8] 參見杜萌若:《〈封神演義〉哪吒蓮花化身故事考源》,《哈爾濱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00年第4期。
(本文為四川省教育廳2011年度科研重點項目“哪吒文化的符號解讀”之研究成果)
作者單位:四川幼兒師范高等專科學校(江油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