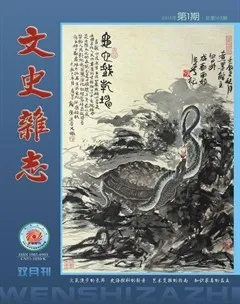山陰道上 畫中行
東晉永和九年(公元353年)三月三日,四十一位寬袍大袖的名人雅士應(yīng)會(huì)稽內(nèi)史王羲之(321-379)之邀,興致勃勃地聚首于會(huì)稽山陰的蘭亭(今浙江紹興西南蘭渚山),觀山賞景,推盞送杯,把酒沐風(fēng),臨水吟詩,造就了中國文化史上一件令人稱羨的風(fēng)流韻事——蘭亭雅集。
這次集會(huì)的一項(xiàng)直接成果,便是王羲之名動(dòng)千古的《蘭亭集序》。據(jù)《蘭亭集序》及宋人施宿《會(huì)稽志》卷十所記,集會(huì)將當(dāng)時(shí)最為顯赫的世家大族的魁首或子弟幾乎網(wǎng)羅無遺。其中瑯邪臨沂王氏家族與會(huì)者七人,除王羲之外,還包括他七個(gè)兒子中的六個(gè):長子王玄之,次子王凝之,三子王渙之,四子王肅之,五子王徽之,七子王獻(xiàn)之。陳郡陽夏謝氏家族二人:謝安、謝萬。潁川鄢陵庾氏家族二人:庾友、庾蘊(yùn),他倆都是前任丞相庾冰的兒子。太原中都孫氏家族三人:孫綽及子孫嗣、兄孫統(tǒng)。時(shí)譙國龍亢桓氏家族的桓溫把持內(nèi)外大權(quán),其子桓偉亦受王羲之之請出席雅集。高平金鄉(xiāng)郗氏家族與會(huì)的代表則系郗曇,他是前太尉郗鑒次子。王、謝、郗、庾,在東晉初期并稱為四大家族。后來“四家”的說法雖有變異,但王、謝始終名列其中。一部東晉的歷史,幾乎成了這兩家的興衰史,正如唐人羊士諤所詠:“山陰道上桂花初,王謝風(fēng)流滿晉書。”王、謝兩家多衣著皂衣,而他們又恰巧居住于建康(今南京)夫子廟附近的烏衣巷(三國吳時(shí)烏衣營所在),時(shí)人故稱其子弟為“烏衣郎”。由是,四百年后,當(dāng)王、謝世家式微之后,方才會(huì)有劉禹錫《金陵五題·烏衣巷》那樣的懷古名篇供人玩味:
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
舊時(shí)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
蘭亭雅集那天的三月初三日,在上古時(shí)代叫“修禊”日或“春禊”日。禊,即祓祭,名義上是消除不祥,實(shí)則是借春光融融而嬉游于水濱林間,到大自然中去放松心情。它最早可追溯到周代。《論語·先進(jìn)》里記有曾點(diǎn)的一段話:
莫(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fēng)乎舞雩,詠而歸。
你看孔子的弟子,讀書累了,便在暮春三月選擇一個(gè)好天氣,穿上新衣服,約上五六個(gè)伙伴,帶上六七個(gè)小孩,去沂水邊洗洗澡,在舞雩臺(tái)上吹吹風(fēng),再一路詠著詩歌走回來,多么愜意呀!這既是曾點(diǎn)的主張.也是他一貫的生活模式。曾點(diǎn)可以說是中國最早的一批提倡休閑文化,懂得勞逸結(jié)合者中的一位。《論語·先進(jìn)》說,孔子聽曾點(diǎn)之言后,“喟然嘆曰:‘吾與點(diǎn)也!’”不用說,孔子當(dāng)是這最早一批提倡休閑文化者的翹楚或?qū)煟彩亲钤缍蒙剿さ娜恕K囊痪洹爸ㄖ牵┱邩匪收邩飞健保ā墩撜Z·雍也》),開啟了中國文人走向山水、審美山水,熱愛山水,與山水和諧相處的門扉。此后,才有莊子那恣肆汪洋的《逍遙游》、屈原那獨(dú)立不遷的《橘頌》、曹操那沉雄宏闊的《步出夏門行·觀滄海》……
古人修禊出游所向,自然是山光水色,春風(fēng)和煦,旖旎喜人。王羲之召集的春游聚所蘭亭一帶,更是江南一處鶯飛草長、林幽泉清、美不勝收之地,歷來飽受文人墨客青睞。特別是從今紹興城往蘭亭的那段山陰道,更是嶂青林秀,波光如鏡,人行其間,恍入太虛境,有如畫中游。《晉書·王羲之列傳》說:“羲之雅好服食養(yǎng)性,不樂在京師,初渡浙江,便有終焉之志,會(huì)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謝安未仕亦居焉。孫綽、李充、許詢、支遁等皆以文義冠世,共筑室東土,與羲之同好。”難怪永和九年三月初三,王羲之組織修禊之會(huì),竟一呼百應(yīng),一下子來了四十一位名聲響亮的雅士。王羲之原來并不想做官(《晉書》載其自書:“吾素自無廊廟志”);爾后既然做了,則不樂在京師而屢求外任,一到了會(huì)稽,便不想再走了,到底終老于此。是會(huì)稽好山好水征服了他。以后他的子孫便世居這里,再?zèng)]有返居臨沂老家。他所鐘愛的小兒子、與他在情趣上最為接近的王獻(xiàn)之亦性愛山水而依戀于會(huì)稽。《世說新語·言語》載王獻(xiàn)之(字子敬)的話說:“從山陰道上行,山川自相映發(fā),使人應(yīng)接不暇。若秋冬之際,尤難為懷。”南朝梁人劉峻注引《會(huì)稽郡記》曰:“會(huì)稽境特多名山水。峰崿隆峻,吐納云霧。松栝楓柏,擢干竦條。潭壑鏡徹,清流寫(瀉)注。王子敬見之,曰:‘山水之美,使人應(yīng)接不暇。’”《世說新語·言語》又載:“顧長康(即顧愷之)從會(huì)稽還,人問山川之美。顧云:‘千巖競秀,萬壑爭流,草木蒙籠其上,若云興霞蔚。’”
山陰道上的詩情畫意到了現(xiàn)代文人魯迅先生筆下,則變成對故鄉(xiāng)山水的一段刻骨銘心的繾綣記憶:
我仿佛記得曾坐小船經(jīng)過山陰道,兩岸邊的烏桕,新禾,野花,雞,狗,叢樹和枯樹,茅屋,塔,伽藍(lán),農(nóng)夫和村婦,村女,曬著的衣裳,和尚,蓑笠,天,云,竹……都倒影在澄碧的小河中,隨著每一打槳,各各夾帶了閃爍的日光,并水里的萍藻游魚,一同蕩漾。諸影諸物,無不解散,而且搖動(dòng),擴(kuò)大,互相融和;剛一融和,卻又退縮,復(fù)近于原形。邊緣都參差如夏云頭,鑲著日光,發(fā)出水銀色焰。凡是我所經(jīng)過的河,都是如此。[1]
正是因?yàn)闀?huì)稽山水之美甲天下,才會(huì)吸引來四方“越名教而任自然”、“歸之自然”的魏晉名士紛至沓來,流連忘返,終至永和九年蘭亭雅集而臻物我相親,“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將至”(《蘭亭集序》)的境界。這里僅錄王羲之《蘭亭集序》的前半節(jié),已可見當(dāng)時(shí)文人屬意山水、會(huì)心于山水的審美方式:
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huì)于會(huì)稽山陰之蘭亭,修禊事也。群賢畢至,少長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為流觴曲水,列坐其次。雖無絲竹管弦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敘幽情。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fēng)和暢。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所以游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信可樂也。
這部分寫山光水色,衣冠繁盛,文筆輕靈,跌宕有致。后半部分則由山水形勝生發(fā)開來,感慨生命的短促和自然的永恒,“俯仰若有余痛”,令人擊節(jié)三嘆,扼腕不已。難怪歷代都視之為散文上品,引為圭臬。而全篇三百二十四字,更是書法飽滿,墨跡圓潤,張弛自如,神采奕奕,被褚遂良譽(yù)為“天下第一行書”。劉熙載《書概》說:“《蘭亭》一序遂如日月經(jīng)天,千秋萬世,照耀壇坫矣。”相傳王羲之在翌日試圖重寫序文,卻一連數(shù)遍,再也難現(xiàn)原稿神韻。這是因?yàn)樵蚴墙柚埔庹d、情緒高昂之際一氣呵成;后來環(huán)境、心境變了,其筆觸也自然風(fēng)光不再。唐太宗對王羲之書法頂禮膜拜,曾在他親自撰寫的《晉書·王羲之列傳·制曰》里推崇備至,稱其“點(diǎn)曳之工,裁成之妙,煙霏露結(jié),狀若斷而還連;鳳翥龍?bào)矗瑒萑缧倍粗薄M嬷挥X為倦,覽之莫識(shí)其端,心慕手追,此人而已。”正是由于唐太宗對王羲之書法鐘愛有加,簡直到了癡迷地步,后來才發(fā)生他派蕭翼智賺《蘭亭集序》而據(jù)為己有,死后也將它一起葬入昭陵的故事。好在太宗良知未泯,生前曾命當(dāng)時(shí)拓書名手馮承素及書法大家虞世南、褚遂良等臨摹數(shù)件副本分賜親貴近臣,所以今天我們還能有幸一睹《蘭亭集序》的大體風(fēng)韻。
當(dāng)時(shí)參與蘭亭雅集的四十二位名士(包括召集人王羲之在內(nèi))齊聚蘭亭這一浙東勝景,聽百鳥絮語,沐熏風(fēng)徐徐,仰萬里晴空,看山川嫵媚,觸摸“天地之大美”,頓覺心澄如鏡,心朗如月而詩興泉涌,遂遵三月三日上巳舊俗,推酒觴(一種橢圓形雙耳飲器)入溪水。水流曲折,隨波逐流,觴但駐于何處,此處之士便要當(dāng)場作詩;倘作詩不成,則要罰酒。按王羲之后來所匯《蘭亭詩》計(jì),時(shí)有二十六人完成詩作,凡四十一首;未完成者則有王獻(xiàn)之等十六人。
應(yīng)該說,《蘭亭詩》集里的這些詩,雖是應(yīng)景之作,卻多出自心靈,以精品居多;當(dāng)然也不乏勉強(qiáng)為之的平庸之作。但作為自覺以山水為審美對象的同題材的詩人群體的作品匯編,它實(shí)為晚晉以前規(guī)模最大者,在中國山水文學(xué)史上具有至關(guān)重要的啟迪意義。而作為曲水流觴的詩人雅集活動(dòng),則在入唐以后隨著遣唐使返航的風(fēng)帆傳入東鄰日本。據(jù)《續(xù)日本紀(jì)》記載,至少在奈良時(shí)代(710- 784年),以三月三日流觴賦詩為主要內(nèi)容的宮廷曲水宴已不是什么稀罕事。現(xiàn)存日本最早的漢詩集《懷風(fēng)藻》,便收入了神龜年間(724-729年)最早的一批漢詩人在曲水宴上的詩作。諸如山田三方“錦若飛瀑激,春岫曄桃開。不憚流水急,唯恨盞遲來”(《三月三日曲水宴》)一類描寫山川景物,感嘆自然代謝的詩句,顯示出日本漢詩人試圖通過學(xué)習(xí)中國文化,創(chuàng)造自己的山水文學(xué)的努力。
“從某種意義上說,發(fā)源于中國的流觴曲水,已經(jīng)變成了漢詩人的節(jié)日。說三月三日是那時(shí)未命名的詩歌節(jié),也并不夸張。那些曲水詩,也正是漢詩在日本從黎明走向清晨的縮影。”[2]今天的日本列島,從北部的巖手縣,中經(jīng)關(guān)西地區(qū)的京都,直至南方的鹿兒島,每當(dāng)春天來臨之后的四五月間,都要在觀光勝地和寺院舉辦曲水宴,在茂林修竹間再現(xiàn)群賢畢至、少長咸集的盛況。其中4月上旬鹿兒島的曲水宴,是在著名的仙巖院遺址上舉行的。據(jù)史料記載,江戶時(shí)代(1603—1867年)鹿兒島上第二十一代藩主島津吉貴于 1736年參考王羲之《蘭亭集序》的描寫,營造了一處可以進(jìn)行曲水流觴的庭院,即仙巖院。其營造所需竹株,乃來自中國浙東地區(qū)——那正是王羲之蘭亭所在地區(qū)。那一時(shí)期的鹿兒島曲水宴,規(guī)模最大,影響最大,但所吟已非漢詩,而是日本本土產(chǎn)生的和歌(短歌);不過其曲水流觴的形式,仍具鮮明的中國特色,至今未有變易。
王羲之不是開創(chuàng)中國曲水流觴韻事的第一人,但卻是將它極度放大,以至名動(dòng)中外,流播千古的大功臣。而那部反映這個(gè)韻事成果的《蘭亭詩》集,“寄傲林丘”、“散懷山水”,于東晉動(dòng)蕩的政治中另辟天地,怡然自得,顯現(xiàn)出深諳莊老之道的文人名士們與山川共舞、與林泉同歌的閑適心態(tài)和樂觀精神。試看王羲之《蘭亭詩》中的五言之二:
三春啟群品,寄暢在所因。
仰望碧天際,俯磐綠水濱。
寥朗無厓觀,寓目理自陳。
大矣造化功,萬殊莫不均。
群籟雖參差,適我無非新。
詩人性愛山水,鐘愛萬物。就在蘭亭雅集后的第三年,即永和十一年(355年)三月,王羲之即稱病辭官,與志同道會(huì)者“盡山水之游”,足跡千里之外,“窮諸名山,泛滄海,又曰:‘我卒當(dāng)以樂死。’”(《晉書·王羲之列傳》)難怪當(dāng)年他置身于會(huì)稽嫵媚春光的溫暖懷抱中,能夠感受到大自然渾厚博大的胸懷、無比創(chuàng)造力和勃勃生機(jī);進(jìn)而能夠在淡忘物我界限的同時(shí)亦認(rèn)識(shí)到人在自然中的重要分量,以至心情愉快,口吐珠璣,和他的同伴一道,造成中國山水詩史上的一處令人神往的勝境。
王羲之之外,《蘭亭詩》中孫統(tǒng)的五言更是以景傳思,情致恬淡,意味雋永:
地主觀山水,仰尋幽人蹤。
回沼激中逵,疏竹間修桐。
因流轉(zhuǎn)輕觴,冷風(fēng)飄落松。
時(shí)禽吟長澗,萬籟吹連峰。
公平地說,孫統(tǒng)的這首五言已屬純粹的模山范水之作。其“表現(xiàn)閑適生活情趣,山水貫串始終,手法熟練,可以認(rèn)為是一成熟的山水詩。”[3]他如謝萬、謝安、孫綽等的詩,在《蘭亭詩》集中也堪稱上乘;特別是被王夫之評為“蘭亭之首唱”的謝萬的四言詩,描摹蘭亭山水,可謂繪聲繪色,展現(xiàn)中國早期山水詩的質(zhì)樸美、清新美、靈動(dòng)美:
肆眺崇阿,寓目高林。
青蘿翳岫,修竹冠岑。
谷流清響,條鼓鳴音。
玄崿吐潤,霏霧成陰。
從總體上看,蘭亭詩人群體仍帶有“魏晉風(fēng)度”的特質(zhì),以沉靜清虛為人格至美,追求一種超越塵俗、擺脫物累的精神境界,希冀把握住真正的自我。所以他們都喜好山水,以擁抱山水達(dá)到與自然“混一不分,同為一體”(阮籍《達(dá)莊論》)的最終目的,以至于他們的山水詩多以玄言詩的面目出現(xiàn),帶有玄言詩的一般特點(diǎn),即以玄學(xué)的虛靜審美方式來觀照山水,形成山水加玄言的藝術(shù)結(jié)構(gòu)。只是這樣的表達(dá)方式并不能完全遮掩住蘭亭詩人筆下或多或少帶有的人生無常,有如白云蒼狗的憂郁色彩。這是時(shí)代的印記,是與東晉朝廷偏安江南,屢次北伐未果,而又吏治腐敗、內(nèi)亂頻仍的政治亂象相關(guān)聯(lián)的。東晉名士們試圖效法魏晉之交的竹林七賢躲進(jìn)山林,“以玄虛宏放為夷達(dá)”的故事立世處身,卻終歸未能忘卻世事。王羲之雖早年決意不仕,最后還是托不過庾亮的情面,出來做了寧遠(yuǎn)將軍、江州刺史,終至右軍將軍、會(huì)稽內(nèi)史方告退。謝安游處會(huì)稽山水間曾達(dá)二十余年,在蘭亭雅集時(shí)尚“無處世意”,可后來竟做官做到宰相大位,成為國家棟梁,以致權(quán)傾朝野,死后贈(zèng)太傅。謝萬在蘭亭雅集前早已入仕為官。孫綽先前也在浙東一帶游放山水十余年,蘭亭會(huì)后便應(yīng)征西大將軍桓溫征辟出山,為著作佐郎,以廷尉卿而終。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總之,蘭亭雅集的與會(huì)者雖以立言宏大自得,卻大多是素懷社稷的有志之士。要他們真正做到莊、老之學(xué)的超越生死、淡看世事浮云的舒卷起伏,實(shí)際很難。當(dāng)他們面對金甌殘缺的多事之秋時(shí),內(nèi)心并非山陰水光那般澄靜無塵,波瀾不驚。《世說新語·言語》記載王羲之與謝安共登冶城(舊址在今南京),“謝悠然遠(yuǎn)想,有高世之志。”王羲之批評他說:現(xiàn)在四處軍事工事林立,國家處在危難之中,大家都應(yīng)該為國家分憂才對。只想著如何不擔(dān)當(dāng)政務(wù),避世清談,恐怕不合時(shí)宜吧?其實(shí),謝安只是說說而已。《晉書·謝安列傳》講簡文帝司馬昱為相時(shí),就將他看得很清楚,說:“安石(謝安字)既與人同樂,必不得不與人同憂,召之必至。”后來謝安果在四十歲時(shí)應(yīng)桓溫之請,出為司馬。此時(shí)中丞高崧開玩笑說:你謝安自恃清高,高臥東山,每次請你出山都不肯。你心里哪里裝有天下百姓啊!現(xiàn)在千呼萬喚到底出來了,讓天下人如何看你!謝安聽后,“甚有愧色”。他其實(shí)已在檢討自己。他之所以終于能夠出來為國家服務(wù),應(yīng)該是與好友王羲之的時(shí)時(shí)敲打有關(guān)聯(lián)的。
王羲之雖說也任性率真,喜山水之游,卻反對玄言家的清談?wù)`國,強(qiáng)調(diào)腳踏實(shí)地,為國家切實(shí)做點(diǎn)事情。所以他在《蘭亭集序》里批評莊、老說:“一死生為虛誕,齊彭殤為妄作”,主張正視人生,回到現(xiàn)實(shí)中來。清人吳楚材、吳調(diào)侯在《古文觀止》里對《蘭亭集序》評價(jià)甚高,稱其“通篇著眼在‘死’、‘生’二字。只為當(dāng)時(shí)士大夫務(wù)清談,鮮效實(shí)……逸少(王羲之字)曠達(dá)人,故蒼涼悲慨之中,自有無窮逸趣。”正是由于王羲之具有較為強(qiáng)烈的憂國憂民情懷,在與山水同樂中亦以山水申其志,故而使他主導(dǎo)的蘭亭詩文(包括謝安、謝萬、孫綽、孫統(tǒng)等的蘭亭詩)在中國山水文學(xué)初興階段便達(dá)到一個(gè)較高水平。只是蘭亭詩人面對的是東晉的殘山剩水,加之受到自何晏、王弼及竹林七賢以來玄言的深刻濡染,所以他們的山水之吟,并沒有魏初曹操《步出夏門行·觀滄海》那樣雄視百代的磅礴大氣,而是盡顯纖巧秀麗、沖淡自然。不過,這個(gè)轉(zhuǎn)變卻為今后中國山水詩的主流風(fēng)格的形成,作出了貢獻(xiàn)。(題圖為方本幼作品)
注釋:
[1]魯迅:《好的故事》,《魯迅全集》第二卷,第190頁,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2005年版。
[2]王曉平:《三月三日的那灣流觴曲水》,《中華讀書報(bào)》2009年3月4日
[3]徐公持編著《魏晉文學(xué)史》,第508頁、509頁,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1999年版。
作者:四川省文史研究館(成都)館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