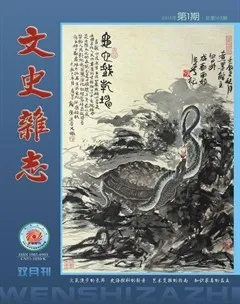關于蒲伯英詩誤植字詞的討論
筆者曾讀《成都日報》9月3日刊登的《保路領袖蒲殿俊:末代進士、四川都督、書法圣手》,疑其引詩有多處誤植。復查網頁,得知該文引詩是抄錄四川大學檔案館《川大文化》所載《蒲殿俊:尊經書院走出的保路領袖》中原詩:
止酒從醫諫,因逃惡稅征。
已無民畏死,安用壯攏人。
饑飽憑毫瀚,興亡聽鬼神。
此身浮來了,差免附朱門。
筆者認為《川大文化》所載蒲詩有誤植文字,理當勘正,于是發信給幾位師友商討,先后收到何崝、文伯倫、馮修齊、劉奇晉、陳稻心、龍克勇和李興輝諸兄回復,多表贊同校勘之意,但意見略有不同。
克勇兄特為搜索網載圖書,陸續發來該詩的幾個文本以供參考。其中《民國舊體詩史稿》(胡迎建編著,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5第1版)載蒲殿俊詩為:
止酒從醫諫,因逃惡稅征。
已無民畏死,安用壯猶人。
饑飽憑毫翰,興亡聽鬼神。
此身浮未了,差免附朱門。
比對之后下,筆者認為后者當是較為可靠的善本。以下先陳述當時個人初見,然后羅列各家見解,據理剖析,最后得出修訂之結論。
一、《川大文化》詩頷聯“攏人”費解,且仄起句式第四字不能用仄聲字。少成最初著眼于抨擊時局,設想原作“攘人”。《論語·子路》:“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辭源》注“攘”字義項為侵奪,則讀陽平聲,如陽切。但閱讀《民國舊體詩史稿》作“猶人”,胡研究員評曰:“民不畏死,自己又何必要這壯健的身體?” 根據這些提示,發覺自己設想有誤,蒲公自嘲之詩,應是切身之言,當是“壯猶人”。
復查《論語·顏淵》:“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史記·李斯列傳》:“ 斯其猶人哉,安足與謀。” 司馬貞索隱:“言我今日猶是人,人道守順,豈能為逆謀。”劉壎《隱居通議·詩歌六》:“ 荊公持論,多不猶人。”《聊齋志異·顏氏》:“閨中人,身不到場屋,便以功名富貴似汝廚下汲水炊白粥,若加冠于頂,恐亦猶人耳!” 謂如同別人。故而可以肯定“壯猶人”之說,其意即“我既已明白民不畏死,何必要求自己強壯如常人”。“猶”,平聲,合乎聲律。
二、頸聯“毫瀚”當作“毫翰”。諸兄均認可。《說文》:“翰,天雞赤羽也。” 后借指毛筆、文章、書信等。葛洪《抱樸子·行品》:“精微之求,存乎其人,固非毫翰之所備縷也。”孟浩然 《洗然弟竹亭》:“逸氣假毫翰,清風在竹林。”“瀚”表“浩大”,與“筆”無關。“瀚海”一作“翰海”,但“翰墨”不作“瀚墨”。蒲公晚年,鬻字自給,當用“毫翰”。正如胡研究員所解:“不過是憑文字稿賺得一口飯吃,是死是活聽由鬼神安排。”此聯令人聯想顧元慶《夷白齋詩話》的:“解元唐子畏,晚年作詩,專用俚語,而意愈新。嘗有詩云:‘不煉金丹不坐禪,不為商賈不耕田。起來就寫青山賣,不使人間造孽錢。’君子可以知其養也。”
三、尾聯“浮來”費解,且平起句第四字不能用平聲字。胡研究員未解釋此句,但評曰:“末以不附權貴自豪。議論堂堂正正,而饒有趣味。”少成起初認為“來”是平聲,不合律,似當用仄聲字“事”,始與 “了”有關聯。《青瑣高議》:“我聞古人之詩曰:‘長江后浪推前浪,浮事新人換舊人。’”
但是文兄認為:“句七作‘未’是。”何兄認為:“‘來’當是‘未’之誤。‘浮’謂浮泛、浮生,此句為前途渺茫之意。”二兄所言甚是!“未了”猶言“未曾了卻”。辛棄疾詞云:“了卻君王天下事,贏得生前身后名。”《后村詩話》載:史相力薦放翁,賜第,其去國自是臺評,王景文乃云:“直翁未了平生事,不了山陰陸務觀。”放翁見詩,笑云:“我字務觀乃去聲,如何作平聲押了。” “未”仄聲,合乎聲律要求。“來”與“未”形近誤植。此聯可以解為蒲公自認“我浮生未了,差可自慰還未曾附身朱門”。
另外必須提及何崝兄另一精辟見解:“此詩四韻,首韻‘征’在‘庚韻’,中二韻為‘真韻’,末韻在‘元韻’。蒲氏從事舉業,不致昧于韻律,或因從事戲劇,致于用韻放寬乎!”
文伯倫兄讀詩慨嘆:“此詩思想性藝術性均臻上乘,惜誤讀誤植,反復糟踐,遂成疑陣。”現經幾位退休老者發揮余熱,花費時日,切磋琢磨,得出如此校勘意見,也覺能盡綿薄,不致浪費余生,聊以獻芹,謹供讀者參考。
四川大學檔案館主辦的《川大文化》,應該是具有學術性、權威性的資料寶庫,提供的文字資料(包括網載文字)應該翔實可靠。如今供讀者下載的《川大文化》中的蒲殿俊史料,居然有如此多的錯誤,實在不利于交流和指導。希望能夠自查,尋覓原本或善本校勘修改那些資料中的誤植文字。
附記:
筆者初疑蒲詩首聯 “因逃”不能與“止酒”對仗。設想可作“逃田”(“逃田”讀音為平平,與“止酒”的仄仄相對)。“惡(音務,去聲。動詞,厭惡,憎惡)稅征”與“從醫諫”對仗。書證為《資治通鑒·后晉齊王天福八年》:“民不勝租賦而逃。王曰:‘但令田在,何憂無谷!’命營田使鄧懿文籍逃田,募民耕藝出租。”葉適《寶謨閣直學士贈光祿大夫劉公墓志銘》:“公以見種實稅均其荒萊,民愿佃者第減之,上供自若而逃田盡復。”想是蒲公當時目睹軍閥割據的防區時代有此現象特為書出。
承何崝兄提示“‘因逃’一語似不誤”,重新思考:首聯“因逃”不必與“止酒”對仗。“惡(入聲。形容詞,兇惡)稅”是偏正結構。首聯兩個分句也就可以視為因果關系的復句。此詩重點不在評論時政,而是蒲公自嘲:我依從醫師的諫言停止喝酒,因此逃脫兇惡苛稅的強征。不必強解為“因厭惡征稅而逃田”,不能改作“逃田”!
筆者遵從梁任公言,起初的設想是“孤證不為定說”,臆測錯誤,理合“遇有力之反證則棄之”!胡迎建研究員的評論很好:“他因止酒自然就逃脫了酒稅的征收,意謂酒稅甚苛。”
作者:四川省文史研究館(成都)館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