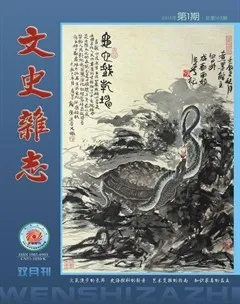陳寅恪的讀書與做人
陳寅恪是著名的國學大師,幾乎同時代的文人都極尊崇他。他在課堂上講授的學問貫通中西;在課余分析各國文字的演變,竟把葡萄酒原產何地,流傳何處的脈絡,給學生講述得一清二楚。他上課時,連清華的教授們也常來聽。
陳寅恪在日本留學時,與魯迅是同學,二人曾有交往。但從陳留下的詩文中,幾乎看不到他與魯迅的交往經歷,倒是魯迅的日記中對此卻有記載。陳說,因為魯迅的名氣越來越大,最后以“民族魂”的大旗覆棺蓋槨,繼而成為“先知先覺”和“全知全覺”的圣人;他怕言及此事,會被國人誤認為自己是魯迅所說的無聊之徒。
陳寅恪在歐洲游學期間,對史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他特別注重各史中的志書,如《史記》的《天官書》、《貨殖列傳》,《漢書·藝文志》,《晉書·天文志》,《隋書·天文志》,《新唐書·地理志》等等。即使德文原版的天文學也是他經常誦讀的史書之一。他誦讀了“十三經”,而且每字必求甚解,這也就奠定了他一生精考細推的治學方法。他認為,中國歷史是中國文化的體現,他選擇歷史學作為終生奮斗的領域,其意也正在于此。
陳寅恪留學回來后,與當時大多數歸國留學生的西裝革履不同:總是一襲長衫,腳踩布履,冬春則棉布馬褂;數九寒冬,就在脖間纏一條五尺圍巾,頭戴厚絨帽,褲腳扎一根布帶。每次上課前,他對學生說:“前人講過的,我不講;近人講過的,我不講;外國人講過的,我不講;我自己過去講過的,也不講。現在只講未曾有人講過的。”
陳寅恪倡導為人治學當有“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他讀書時,習慣將自己的考證、注釋、心得,寫在書籍的書眉上。他的文章有獨特的風格,總是習慣于先引上若干條史料,然后再加上一段按語的做法——給人的感覺,他的文章更像是沒有經過加工的讀書札記。胡適在日記里曾經這樣評價說:“寅恪治史學,當然是今日最淵博、最有識見、最能用材料的人,但他的文章實在寫的不高明。”
陳寅恪曾談到他學習多種外語的經驗,只強調一個“誠”字。在清華執教時,他已名滿天下,但仍然堅持自學西夏文和蒙古文,并且每個星期進城兩天,向德國教授鋼和泰學習梵文。季羨林曾用“泛濫無涯”來形容陳寅恪懂得的語種數量。只是陳寅恪極為謙虛謹慎,從未將所學炫耀于他人。他到底懂得多少種語言文字,直到他去世都未能有定論,世間沒有一個人能說得清楚;即使是他的師友、家人、弟子。
陳寅恪說過:“國可以亡,史不可斷,只要還有人在書寫她的歷史,這個民族的文化就綿延不絕。”蘇聯學者在蒙古發掘出三件突厥碑文,但都看不懂。后來,陳寅恪以突厥文對碑文解釋,各國學者都毫無異詞,同聲嘆服。
最后想感慨一下:陳寅恪游學歐美十余年,上過那么多名牌大學,居然就沒有拿一個博士學位,而且清華國學研究院竟然肯發給他一紙導師聘書,這在今天的人們看來,簡直是匪夷所思。陳寅恪的事例其實啟示我們:讀書做人不要急功近利;對人才的使用,重在看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