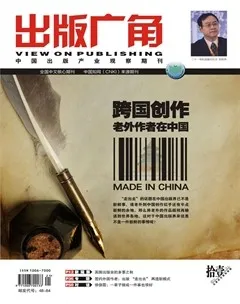細微之處的歷史見證

現實生活,每個人都是參與者。歷史也是同樣,每個人都是歷史的參與者、制造者。歷史,應該是每個人的歷史。
歷史距離我們是遠還是近?似乎很遙遠,因為我們看到的歷史書籍,大多數是帝王將相、政治經濟一類的宏大敘事,都是精英們的歷史,與普通人無關。但細究一下,歷史就是已經過去了的現實。現實生活,每個人都是參與者。歷史也是同樣,每個人都是歷史的參與者、制造者。歷史,應該是每個人的歷史。從這個角度來檢討一下歷史撰述,就感覺到存在著很大的缺憾,關于小人物的歷史著作太少了。
不過近年來,歷史研究、歷史撰述的視野逐漸有從政治投向社會、從上層投向底層的趨勢,并漸成氣候,這方面的著作亦多有問世,可以稍稍彌補之前的遺憾。祝偉坡先生的《微觀歷史:1957-1965》就是其中一本。這本書是祝偉坡先生的日記,主要涉及以下一些歷史事件:反右、大躍進公社化、整風整社、四清運動等。作為那個大時代中的一個小人物,他的日記展現了諸多生動的細節,讓我們既感受到那個時代的火熱、激情與真摯,也感受到了荒誕、殘酷與偏執。
這本書最引起我興趣的,是那一代青年知識分子的內心世界。事實上,一個時代人們的精神世界、心理狀態、觀念信仰,也是歷史有機的組成部分,也是人們認識歷史的重要角度。在日記所涉及的1957年至1965年這八年時光中,祝偉坡先是就讀于河北天津師院中文系,畢業后分配到石家莊師范大學(后改名為河北師范大學)任教。他是一個對新中國充滿了熱情、對中國共產黨無比信任、心地不失善良的年輕人。但他當時所做的很多事情,在他自己后來看來,是荒唐的,嚴重地傷害了無辜的人,比如說,他積極地參加了“反右”運動,后來他反思說:“右派問題,演繹出一場比竇娥還冤的長篇人間大悲劇。每當念此,我就有一種愧疚感,覺得對不起我們班被錯劃為‘右派’的4名同學。”是什么讓一個單純的年輕人,積極地去做“壞事”呢?他們當時是一種怎樣的心態呢?也許,從他們精神世界中,可以找到一部分答案。
在當時青年人的精神世界中,信仰兩個字是極有分量的。從人類信仰的歷史來看,信仰的本質是社會對于個人的一種規制,把社會的制度、文化的要求,內化成為一種個人的心理需求。因此,個人對于信仰的追求,其實就變成了一種尋求社會認同的需要與過程。社會認同度越高,他的生命,在自己眼中,在別人眼中,才變得越有意義。在祝偉坡那一代人的青春時期,他們的信仰是無選擇、無條件、無保留的。與其說是他們選擇了信仰,還不如說是他們把自己交給了信仰。為了表達對信仰的忠誠,也就是為了獲得社會的認同——在當時的語境中,其實就是獲得組織的認同——他們拼命地剖析自己的內心,把組織的意志,變成自己自覺的行動。在祝偉坡的日記中,有大量這方面的自我剖析、自我修煉的記載,比如:“覺悟的提高,不是一朝一夕的問題”“現在才認識到自己需要思想改造的必要性,而且是迫不及待的”;在人際關系上,也要時刻反思政治上是否正確:“與W的關系,有溫情,是屬于個人還是階級感情呢?”在如此這般無數次嚴格地自我剖析、自我修煉之后,“覺悟”的確提高了,但隨之也就逐漸失去了獨立的判斷力,唯上級的意志是從了。很多悲劇,就是這樣發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