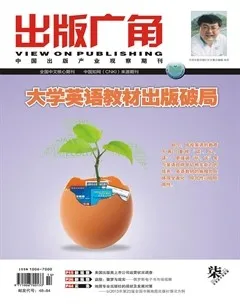閱讀的未來
我們需要思考的是,在數字化的未來,我們是將發(fā)動一場閱讀的革命,還是要革掉閱讀的命?
人類走向讀屏時代
隨著iPhone和iPad掀起的智能手機與觸摸屏電腦席卷全球,谷歌眼鏡廣受追捧,屏幕正在全面滲透進大多數人的日常生活,人類正在全面進入讀屏時代。
對此,美國著名互聯(lián)網觀察家凱文·凱利(Kevin Kelly)提出,隨著屏幕技術不斷發(fā)展,人類社會到處都是屏幕,不光是硬的平板,也可以是軟的可彎曲的,可以是像眼鏡、手表甚至是衣服一樣的材質,可隨身穿戴,甚至就是投影這樣的虛擬屏,這些無處不在的屏幕構成了一個生態(tài)系統(tǒng)。
在人類與屏幕交互方式上,PC時代鍵盤加鼠標是人與機器最好的交互方式;在智能設備普及的時代,觸摸屏幕和語音成了新的更為便捷的方式。在未來,面對由無數屏幕構成的新生態(tài)里,人類可以用身體語言,用3D的操作方式與“移動”變換中的屏幕交流,不斷地打破傳統(tǒng)和標準。
當手持的屏幕功能變得更強大,質量變得更輕,塊頭變得更大,它們將被用來觀察內部虛擬世界的更多東西。當你走在大街上,手持一塊電子屏幕,它將顯示并且記錄大街前方的一景一物:哪里有干凈的洗手間,哪個店鋪出售你想要的東西,你的朋友住在哪里。電腦芯片正變得越來越小,屏幕正變得越來越薄并且越來越便宜,在未來40年,半透明眼鏡的一個功能將是為現實世界提供信息支持。如果你拿起一個物體,通過眼鏡觀察它,該物體的基本信息將分層呈現。通過這種方式,屏幕將讓我們能“閱讀”一切東西,而不僅僅是文本。僅僅是2012年,5×10的18次方個晶體管被嵌入到除計算機之外的其他東西上。很快,大多數產品,從鞋子到湯罐,將內含一塊體積很小的智能隱形芯片,而屏幕將成為我們與之進行溝通的工具。
此外,我們不僅可以從屏幕閱讀相關信息,屏幕還可以從我們的眼光和行為中閱讀信息并進行互動配合。屏幕可用于觀察自己的一舉一動。它們會成為我們的鏡子,用于發(fā)現自我。現在已有數百萬人用袖珍屏幕攝像機記錄自己的所處位置、起居飲食、體重、情緒、睡眠方式和所見所聞。一些潮人已經開始進行生命記錄:記錄生活的每一個細節(jié)、每一句言語、每一個場景和每種活動。一個屏幕就足以成為記錄并且顯示各種活動的海量數據庫。這種全程的自我跟蹤,其結果是獲得一個極為完美的人生“記憶”以及非常客觀的高質量自我形象,這是任何書本所不能達到的。讀屏不僅成為我們生活中的一部分,屏幕還正在變成我們身體的一部分。
讀屏時代,在改變人們的生活方式同時,也直接改變了人們與閱讀相關的所有方面,包括閱讀的內容、讀物的產品形式、人們的閱讀行為模式、人們閱讀的結果等。閱讀正在發(fā)生顛覆性變化。
閱讀再定義
2012年至2013年,是數字閱讀發(fā)生劇烈變化的一年。這一年,移動互聯(lián)網出現井噴式爆發(fā),傳統(tǒng)PC電腦的銷售開始在一些地區(qū)出現歷史少見的下降。手機、平板電腦、數字電視等迅猛發(fā)展,云計算基礎下的多屏共讀成為現實。從1歲兒童到80歲老人,數字閱讀呈現出全民化的趨勢。
據CISCO的統(tǒng)計數據,“到2016年,每人平均將擁有1.4部移動設備,全球移動連接設備數量將達到100億部,包括機器至機器(M2M)模塊,該數量將超過當時的全球總人口(73億人)。”移動互聯(lián)網以及手機、Pad等移動終端的發(fā)展與普及,滿足了人們在移動中對內容的需求,隨時隨地生產與消費內容,也正在成為讀者的一種閱讀習慣。
以APP客戶端、二維碼等為代表的新型數字傳媒入口發(fā)展迅猛,使門戶、搜索引擎的作用在弱化。數字閱讀方式進一步移動化和傻瓜化。微博、微信異軍突起,兩者推動下的碎片化閱讀、社交化閱讀獲得進一步大發(fā)展。微閱讀進一步流行和泛濫。傳統(tǒng)大眾媒體進一步退位。閱讀渠道和閱讀內容被改寫。
以前我們在討論數字閱讀與紙質閱讀的時候,花了很大精力在討論深閱讀與淺閱讀,經典閱讀與娛樂化閱讀。隨著碎片化、微閱讀的進一步擴散,這些討論都越來越失去了基礎。
UGC即用戶創(chuàng)造內容的維基模式進一步擴展,改寫了傳播閱讀內容生產模式。以Self publish、自媒體為代表的新型媒體內容生產和傳播模式正在成為新的主流。從2008年開始,美國自助出版的圖書品種就超過了傳統(tǒng)出版社出版的圖書品種。
現在,隨手拍照和發(fā)微信記錄心得,分享、轉發(fā)別人的微博與微信,已經成為許多年輕人的生活方式。對于他們來說,閱讀的過程就是創(chuàng)作的過程,而創(chuàng)作的過程同時也是閱讀的過程。在這里,分享既是閱讀又是創(chuàng)作,分享成為閱讀的內容來源和閱讀的一種方式。這種方式革新了以前“閱讀是獲得”的觀念,閱讀成為生產和傳播。傳統(tǒng)的出版、發(fā)行、傳播、受眾、作者、讀者,這些清晰的概念都正在被改寫。
根據這一變化,克萊·舍基 (Clay Shirky)提出一個新概念:“認知盈余”(Cognitive Surplus),其核心主題是,隨著在線工具促進了更多的協(xié)作,人們學會更加建設性地利用自由時間來從事創(chuàng)造性活動而不僅僅是消費。分享、對話、協(xié)作、人人參與,構成了認知盈余的基礎,也構成了新的信息化生產與生活模式。舍基提出,人們正經歷一個樂于創(chuàng)造和分享的年代,由于技術使創(chuàng)造和分享變成可能,我們將看到一個人人參與的新時代。
閱讀渠道、閱讀內容、閱讀內容生產方式三個方面的改寫,都指向一個方向:改寫閱讀定義。
長期以來,圖書都是閱讀的代名詞。在中國,閱讀就是讀書,讀者、讀書人都是指圖書的閱讀。雖然報刊也屬于閱讀,但從經典的意義上,閱讀不包括報刊。
隨著電腦、網絡、手機等數字媒體的發(fā)展,對人們的閱讀時間、閱讀內容、閱讀形式均產生了較大沖擊。一方面,閱讀越來越變化無處不在,閱讀“泛在”化;另一方面,數字閱讀呈現出顯著的娛樂化、碎片化和社交化現象,同時媒體影像化、圖片化,使閱讀的定義在重新被改寫。
閱讀的本質,是信息通過間接渠道的傳播與獲取。通過閱讀,我們掌握了我們不能通過自己的眼、耳、鼻、舌、身、意親自體會到的色、聲、香、味、觸、法,文字使我們超越了肉身,超越了時空,使文明跨越時空進行傳遞。然而,自從有了廣播、有了圖片、有了影像,有了數字化,傳統(tǒng)的紙質圖書、期刊、報紙的功能就在一日日被補充、被替代。
我們正在目睹傳統(tǒng)媒體受到沖擊和面臨死亡的六大過程:首先是音像,如錄音帶、錄像帶,光盤,現在,錄音帶錄像帶已經幾近成為文物;其次是電影電視,國際上電影、電視的市場規(guī)模正在大規(guī)模縮水;第三是報紙,2008年金融風暴以后,美國大報的破產已經不能成為新聞,就連《紐約時報》也需要賣樓求生;第四是期刊,《商業(yè)周末》被一美元賣掉,《讀者文摘》經營難以為繼,連色情雜志《花花公子》也要破產;第五是書店,鮑德斯書店的破產一度震驚國際書店業(yè),中國的大量實體書店正面臨如果政府如不出手相救就會大面積死亡的境地;第六是圖書,圖書出版業(yè)曾經被以為是數字化中的凈土,輕易不會被擠跨,但是,自從亞馬遜推出KDP(Kindle Direct Publishing),美國出版界就一天天地感受到了逼人的寒意……
傳統(tǒng)媒體的衰亡,其原因和結果就是傳統(tǒng)閱讀的衰亡。
然而,這一過程還未結束,還在繼續(xù)。
閱讀的未來
讀屏時代,屏幕無處不在,對屏幕的閱讀也因此無處不在。在這個閱讀 “泛在”時代,紙介質的消失從總體上講是必然的事,沒有了紙介質,傳統(tǒng)的書報刊的界限也自然消失。
隨著屏幕的互聯(lián)化,社交式閱讀、拍照式閱讀、分享式閱讀,使閱讀進入讀圖時代,圖片、影像、流媒體都在使文字的作用退化。
3D虛擬現實技術,3D打印技術,Google glass,穿戴電子產品等物聯(lián)網技術的廣泛應用,使二維信息時代進入三維信息時代,圖片、影像等二維顯示技術也逐步弱化,世界進一步還原到三維立體時空。
在這個時空中,學生們通過3D打印設備實際參觀各種物品的生產和應用過程,或者通過3D虛擬現實技術,直接進行實地考察,對世界進行理解和思考,所見即所得。他們看見和體驗到的,就是他們要學習的東西。切身體會,使他們對需要掌握的知識體會得更加深入和透徹。他們再也不用僅憑一紙文字,通過對文字的推測和理解去還原事物的真相。
從這個角度上看,文字是一種古老、陳舊、低效的信息傳播形式。文字信息需要通過寫作的人進行信息轉換,將真相轉換成文字進行傳播,而讀者則需要將文字重新解碼和還原,但這個過程往往意味著大量信息的誤讀和丟失。此外,對于不認識這種文字的人來說,閱讀這些文字無異于天書,完全無從知道里邊包含的信息,就像我們面對失傳的古老文字無法解讀其含義一樣。
如果是這樣,那么,基于文字的閱讀行為會不會有一天退出歷史舞臺?
既然如此,我們還要不要從新生嬰兒就開始訓練兒童的紙質圖書閱讀技能?還是只要讓他們作為數字原住民無師自通地沉浸于屏幕世界就好?
如果這樣,那么當面對越來越多不讀書而只知盯著屏幕津津樂道于拍照、轉發(fā)和分享的年輕人,我們是要嘆息他們的不學無術、不求上進呢,還是應當感嘆我們作為數字移民已經老朽得正在被時代淘汰出局?
但是,由此一來,會不會基于文本閱讀而形成的人類文明,包括數千年面向文字閱讀而建立起來的邏輯思維、抽象思維、想象思維大廈,會不會弱化,抑或更加進步?
總之,我們需要思考的是,在數字化的未來,我們是將發(fā)動一場閱讀的革命,還是要革掉閱讀的命?
(作者系中國新聞出版研究院國民閱讀研究與促進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