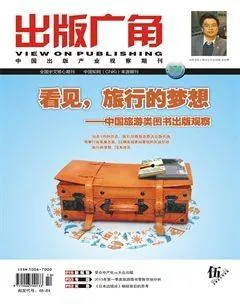民國“邊緣報刊”的發掘、利用與研究
民國報刊是研究民國歷史的珍貴資料庫,離開這個巨大而又豐富的原始資料庫,民國歷史的研究不可想象。
民國報刊是研究民國歷史的珍貴資料庫,離開這個巨大而又豐富的原始資料庫,民國歷史的研究不可想象。研究民國時期的文學(1917—1949)同樣如此。隨著民國文學研究歷史化、古典化成為研究者的一致訴求,如何更有效地利用民國報刊這個豐富的資料庫、如何更進一步深入民國報刊內部去打撈史料,成為擺在每一個文學研究者面前的重要課題。劉濤的《現代作家佚文考信錄》一書 (以下簡稱《考信錄》),提出“邊緣報刊”的概念,從對民國“邊緣報刊”的發掘與整理入手,挖掘出民國時期為數不少的重要作家的大量佚文,有力推動了民國文學研究的進展。他的研究再次揭示了民國報刊對于研究民國歷史包括民國文學的重要價值,值得引起相關研究者重視。
劉濤提出“邊緣報刊”概念,對于民國報刊研究具有重要參考價值和啟發意義。“邊緣”,是相對于“中心”“主流”而言。所謂“邊緣報刊”,概而言之,指的是民國時期那些影響不大或處于地域、政治邊緣的“小”刊物或文化類綜合性期刊、專刊、與文學無關的報紙副刊、出版時間不長影響不大的報紙文學副刊等等。“邊緣報刊”雖在含義上指的是“大報大刊”之外不為人所關注的“小報小刊”,但仔細分析,可看出作者所謂的“邊緣”還包含有其他更豐富的涵義。
首先,劉濤所謂的“邊緣報刊”指的是文學報刊之外的非文學性的文化類、政治類、宗教類、音樂類報紙與期刊以及綜合性的大型文化期刊。作者研究專業為民國文學,對于文學這個中心來說,非文學類報刊大多不在此類研究者的研究視野之內,屬于“邊緣”。例如,本書所關注的《河南中華圣公會會刊》就是一份“邊緣報刊”。該刊由河南中華圣公會編輯發行,是基督教教會刊物。這樣一份教會刊物,所刊文章內容多為宣揚基督教教義,與文學幾無任何關聯,因此,對于民國文學研究者而言,它當然是一份“邊緣刊物”。本書所涉及的其他刊物,如《家庭研究》專門研討家庭問題,《世界展望》專門研究二戰時期國際政治問題,《春之歌選》與《每月新歌選》刊登的大部分是歌詞,其內容皆與文學無涉,對于民國文學研究者而言,也屬“邊緣報刊”。但就是在這些邊緣報刊上,作者卻有不同程度的收獲,如在《家庭研究》上發現成仿吾創作的話劇《離婚》,這是現在發現的成仿吾創作的唯一一部話劇,對于成仿吾研究具有重要價值。在《世界展望》上發現穆時英的系列作品,這些作品可證明穆時英是一位堅定的愛國主義者,而非漢奸。這些佚文,對研究穆時英抗戰時期的思想狀況與政治傾向,對重新評價穆時英,其所具有的重要意義和價值當然自不待言。
民國時期還出現不少各類學校所辦的校級刊物即“校刊”和“學報”,這些校刊和學報由于其內容的綜合性與學術性,與文學關系不太密切,因此,文學研究者對此類刊物也鮮有關注。對于這類邊緣刊物,如《江蘇省立上海中學校半月刊》《光華附中半月刊》《光華年刊》《廈門大學學報》等,《考信錄》也多有涉及。作者在《江蘇省立上海中學校半月刊》上發現鄭振鐸的一篇重要演講《中國的出路在哪里》,在《光華附中半月刊》與《光華年刊》上發現穆時英大學時期創作的系列作品,在福建長汀《廈門大學學報》上發現林庚研究新詩形式的重要論文《新詩形式的研究》,這些佚文的發現,為研究上述作家提供了相當有價值的史料。
由“中心”進入“邊緣”,由文學報刊進入非文學的宗教、政治、文化報刊,說明作者的研究視野已經由文學而延展至宗教、政治、文化,這是一種典型的跨界或越界行為。《考信錄》對非文學類的邊緣報刊的關注與考察,以及由此考察所帶來的豐碩成果,帶給報刊研究者的有益啟示是:在專業的報刊研究中,要學會轉換思路,擴大研究視野,盡量超越專業設置所帶來的知識閾限,這樣才能完成對自我的豐富與超越,帶來意外的成長與收獲。
其次,“邊緣報刊”之“邊緣”還體現在刊物的政治背景上。民國時期的一些綜合性文化期刊或文學報刊,有一部分有著國民黨或汪偽政權的官方背景,屬國民黨或汪偽政權的官辦刊物,這類刊物,作者命之為“灰色報刊”。這類刊物,很長一段時期內,由于政治原因,淡出研究者視野,沒有得到應有的關注和研究,也屬“邊緣報刊”。例如作者所關注的《東南半月刊》《建國青年》及《文化先鋒》周刊、《中央周刊》等刊物,屬國民黨官辦刊物或有著國民黨的官方背景。《東南半月刊》由國民黨中宣部東南區戰地宣傳辦事處主編,發行人為馮有真,出版地在安徽。這是一個時事政治刊物,主要內容為宣傳抗日建國的大政方針。《建國青年》創刊于1946年3月,1947年12月終刊,先在重慶出版,后移至南京。該刊提倡政治革新,所刊文章多為宣傳中國國民黨的政治主張和理論,有一些抨擊中國共產黨的言論。《文化先鋒》由李辰冬編輯,中央文化運動委員會文化先鋒社發行,出版地為重慶。該刊有國民黨的官方背景,上面刊登有一些污蔑共產黨的文章。南京《中央周刊》也屬此類灰色刊物,該刊為國民黨中央機關刊物,創刊于1938年7月,中央周刊社編輯并發行。刊物文章大都是宣揚國民黨政治主張,以三民主義為中心。
作者關注的另一類“灰色報刊”則有汪精衛偽國民政府的背景,如《中大周刊》《中央導報》《新流》等。《中大周刊》是偽中央大學的校刊,偽國立中央大學編纂課編輯周刊。偽中央大學是偽國民政府為粉飾太平于1940年7月宣布成立的,隸屬汪偽政府。《中央導報》周刊,原為中國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員會機關刊物,汪精衛集團叛國后于1940年在南京將其復刊,直屬汪偽國民黨宣傳部,內容側重于宣傳汪偽政府的政策,社長林柏生,總編輯華漢光。《新流》是汪偽時期南京另一個重要漢奸刊物。以上有著汪偽國民政府背景或汪偽政權的官辦刊物,與國民黨的官辦刊物或有國民黨官方背景的刊物一樣,由于政治原因,很長一段時間,被人為遮蔽,或得不到客觀歷史的研究,同樣屬于“邊緣報刊”。
劉增杰先生在《中國現代文學期刊研究的綜合考察》一文中曾指出一些期刊研究,往往或隱或顯地受到二元對立思維模式的潛在影響,大部分國民黨方面的期刊作為“反動刊物” 被有意從報刊目錄中剔除了。他認為應打破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只有多元融匯,才能激活研究主體的生命意識和文學意識,保證史料研究健康發展。用偏狹的視野根本無法認識現實斗爭環境的復雜性所帶來的期刊存在的特殊性,也無法還原意蘊繁復的歷史形態。” 對于此類政治上的邊緣刊物,劉濤在堅持價值評斷的基礎上,能打破二元對立思維方式的束縛,從客觀的歷史角度,對其加以觀照和研究,從中發掘出大量珍貴的史料。《考信錄》對于所謂政治上“灰色報刊”的關注與研究,啟示民國報刊研究者應加大對國民黨官辦刊物、有國民黨官方背景的刊物以及汪偽政權和其他淪陷區日偽報刊的研究力度,進一步增強民國報刊研究的豐富性與歷史性。
第三,“邊緣”還指涉辦刊地點的邊緣。作者不但關注辦刊地處于北京、上海、南京等大的區域中心城市的報刊,而且還關注辦刊地處于全國政治、經濟、文化的邊緣地帶的報刊。這些地方報刊,由于僻處一隅,得不到足夠重視和研究,在它們上面反而容易發現一些有價值的史料。《考信錄》關注的開封《河南中華圣公會會刊》就是這樣一個頗有價值的“邊緣刊物”。民國時期開封雖是河南省省會,但與北京、南京、上海、廣州這些大城市相比,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處于全國的“邊緣”地帶。這樣一份地方性的基督教教會刊物,很少有人關注,即使研究基督教的專業學者也鮮有人提及。而作為現代文學研究者的劉濤,卻從中發現老舍的一篇重要演講,為研究老舍的基督教信仰提供了非常有價值的史料。《考信錄》所涉及的另一重要刊物《廈門大學學報》的辦刊地為福建長汀。《廈門大學學報》作為廈門大學的學術刊物,其辦刊地應為廈門,怎么到了福建的長汀呢?這與抗戰有關。由于抗日戰爭,廈門大學曾一度搬遷至福建長汀,故《廈門大學學報》的辦刊地點也轉移到該地。
民國時期中國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各個方面皆存在區域發展的嚴重不均衡性,這直接導致了名刊大刊多聚集于一線城市,如北京、上海、南京、天津、廣州、香港等。但是,與此種現象同時出現的則是:在一些二三線城市也有為數不少的“小報小刊”。到抗戰時期,隨著中國政治文化中心依次向武漢、長沙、重慶遷移,大批文化人內遷,一度使這些地方及昆明、桂林等地,皆成為一個個分散的文化中心,上述一線城市的名刊大刊皆向上述城市遷移。此外,在內陸其他一些三線或更低一級的邊遠城鎮,也出現了許多報刊。這些報刊由于地處偏遠,得不到有效關注,許多已經流失和損毀。報刊研究者在研究民國報刊時,應加大對于這些邊緣報刊的研究力度。一些學者在這方面已經做出了成績,劉濤就是其中一位。
第四,同為文學報刊,也有“邊緣”與“中心”之別。對于民國文學期刊和報紙的文學副刊,研究者多關注名刊大刊,如《新青年》《小說月報》《新月》《現代》《大公報》“文藝”副刊、《申報》“自由談”副刊等,而對一些不知名的被遺忘、被遮蔽的“小”刊物,則關注不夠,或根本忽略不計。這些處于歷史“邊緣”地帶的文學報刊,如南京《中央日報·文學周刊》、北平《世界日報·明珠》、北平《北平晨報·風雨談》等,同樣也進入劉濤的研究視野。南京《中央日報·文學周刊》由儲安平編輯,1934年5月創刊,1936年4月終刊。與《大公報》“文藝”副刊、《申報》“自由談”等著名的報紙文學副刊相比,《中央日報·文學周刊》幾乎沒有什么名氣,提及的人很少。但就是這樣一份邊緣性的報紙副刊,劉濤通過仔細考察,發現上面刊登過民國許多重要作家的作品,如老舍、李長之、陳夢家、方令孺、曹葆華、臧克家、林庚、孫毓棠、陳銓、陳瘦竹、張夢麟、田漢、洪深、宗白華、邵洵美、儲安平等人。其中不少的作家作品,沒有被作家收集,成為佚文,例如穆時英的文章《內容與形式》與《戴望舒簡論》。北平《世界日報·明珠》、北平《北平晨報·風雨談》與《中央日報·文學周刊》同為純文學副刊,《明珠》在當時有一定影響,《風雨談》則由于出版時間短,在當時的影響力就有限。時過境遷,《明珠》副刊還得到一些研究者的關注,而《風雨談》則完全被人們遺忘。在這兩個文學副刊上,劉濤同樣發現了非常豐富的現代文學史料。由此可見,所謂的“小刊”不“小”,“邊緣報刊”并非真的“邊緣”。所謂“小”,所謂“邊緣”,不過是文學史和報刊史的一種人為設定而已。后來的文學史研究者或報刊研究者,要以歷史的態度,超越政治、意識形態所設定的差序格局,發掘和彰顯被歷史所遮蔽的文學報刊,這樣才能逼近和還原文學史本來的無限豐富性與多元共生性。
劉濤抱著人棄我取的態度,舍中心而趨邊緣,他對民國大量邊緣報刊的精細考察,說明他的治史眼光很獨到,值得報刊研究者借鑒。當然,由于劉濤并非純粹的報刊研究者,他的專業是民國文學研究,因此,他對于民國報刊的研究,就不是僅僅關注于報刊本身,而是為文學研究服務。他從文學角度對于民國報刊的利用與發掘,同樣也可給文學研究者帶來一些有益的啟示。這些啟示簡要歸納起來有三點。首先,報刊是民國文學研究的源頭活水,文學研究者只有進入到民國報刊這個雖雜亂無章但又豐富迷人的資料庫中,才能使其研究保持歷史的客觀性與科學性,才能使自己的研究永葆青春活力。其次,《考信錄》通過對作家佚文的考察,深入歷史地理空間的深層,發現了被作家主體所故意遮蔽的隱秘事實,揭示了佚文生成與作家、時代、政治之間的復雜關系。作者發現,作家佚文的生成有兩種成因,一種為時間久遠所帶來的無意疏漏,即作家佚文之“佚”不是出自作家故意,而是客觀歷史原因,如歷史久遠帶來的遺忘、報刊之難以追尋或遺失損毀等。一種為作家出于政治考慮,對自己的主體與歷史的刻意建構與遮蔽。如臧克家、冰心、曹禺等人的佚文,出現在國民黨的官辦刊物或有著國民黨官方背景的刊物上,而這些文章本身,在特定的歷史時期,也與所謂的“政治正確”存有較大距離。因此,這些文章之“佚”,并非單純的無意遺漏,而是出自作家的有意遮蔽。第三,《考信錄》揭示出現代報刊對于歷史人物所起的“起居注”功能,為研究民國報刊與歷史之關系,提供了一個非常獨特的認知角度。通過對北平《世界日報》的“教育界”專版的細讀,劉濤發現“教育界”對于一些學界名流如胡適、周作人、冰心等人的報道,是跟蹤式的連續報道,對于胡適的報道,甚至可看作是他的“起居注”。這說明民國報刊特別是報紙,在記錄民國歷史包括民國文學方面,承擔著無可替代的作用,研究民國歷史,除檔案記錄外,另一重要渠道就是民國報刊。
(作者單位:河南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