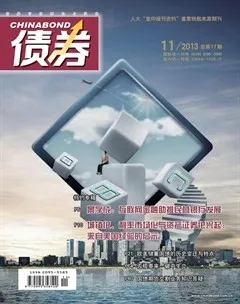在迷茫與困惑中尋找方向
中國的債券市場變了,變得讓債市人似曾相識又倍感陌生。券還是那些券,人還是那些人,但債市好像與我們漸行漸遠,不再如往日般熟識與親密,她的性情忽然變得陰晴不定,行為變得難以揣度,令人無所適從。
6月份以來,債券市場經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債券市場的整肅、監管政策的頻出、貨幣政策的主導、銀行間流動性的稀缺、債券供需的階段性與時點性失衡、宏觀數據的沖擊等,都使得債券市場走勢難以如往昔般可研判。10月至今,收益率不斷創出新高,研究員亦唏噓傳統分析架構與邏輯似乎受到了重大挑戰而瀕臨失效,個中無奈諸多。
10月至今,債券收益率走勢大致可分為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十一長假后至10月中旬。收益率較節前小幅上行,主要是節后首周資金面整體保持相對緊張,利率債一級市場供給接近千億規模對需求造成了較大沖擊,信用利差有所收窄。
第二階段:10月中旬至22日。期間收益率有一定跳升,源于9月宏觀數據的繼續好轉,一級市場供給繼續大幅增加,市場對資金面的擔憂等。
第三階段:10月23日至11月5日。收益率處于高位區間震蕩并有小幅下行,期間面臨企業繳稅、央行暫停逆回購操作、宏觀數據回暖以及供給端沖擊等。隨著央行重啟逆回購,雖然中標利率有所上行,但維穩意圖明顯,隨后資金面有小幅好轉,對市場起到了穩定器的作用,收益率維持相對穩定并有小幅下行。
第四階段:11月6日之后。收益率繼續大幅跳升,主要原因是一級市場債券發行仍保持高位,一級市場中標利率對二級市場產生帶動作用,二級市場收益率反過來影響一級市場中標利率。此外,受市場對未來通脹擔憂的影響,機構對未來資金面的改善不抱預期,恐慌性拋盤涌現,機構開始止損清盤,使得收益率急速跳升,而高位接盤機構卻聊聊無幾,預計近期收益率仍將在高位盤整。
下半年以來的市場走勢,債市人雖身臨其境,卻又有“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處”的疑惑與迷茫,市場走勢變得難以判斷,經驗主義者損失慘重。不論市場走勢分YdMlp7/6+oiT9wB3eLTyPg==幾個階段,亦拋開具體的影響因素,筆者認為6月以來債券市場主要受監管政策主導,可以稱之為“政策市”、“改革市”。
首先,資金面唱主角。“6·20”給債市人上了一節生動的教育課。長期以來,在“雙順差”、人民幣升值預期強、FDI穩定增長的共同作用下,外匯占款維持高位,國內流動性充裕,資金利率低。但2012年開始,上述因素波動性明顯加大,外匯占款數月呈現負增長態勢,傳統的資金投放模式受到沖擊。隨著外匯局加強外匯資金流入管理的通知出臺,美國量化寬松政策退出預期增強,游資流出新興市場壓力加大,銀行間流動性受到嚴峻考驗。
其次,資金需求旺盛強化了流動性緊張。當前我國實體經濟的擴張主要依靠基礎設施建設。但長期以來,投資拉動的邊際效應在遞減,加之企業杠桿率已經達到高點,地方融資平臺還本付息壓力巨大,都增加了對資金的需求。但資金供給端在“用好增量,盤活存量”的總體要求下難以大幅度寬松。銀行間市場經歷了債市整頓,也在逐步降低杠桿,交易量急劇減少,銀行間貨幣流通速度降低,加之傳統資金融出機構撥備率提高,融出意愿降低,使得資金需求更加難以得到滿足。
再次,金融改革推進,監管不斷強化。債市清理整頓“丙類戶”,限制代持交易等杠桿行為,債券發行市場灰色地帶陽光化,機構自營戶與理財戶的防火墻設置等措施都大大凈化了市場。但同時市場交易及債券需求也出現了階段性下降。利率市場化進程的加快、定價機制的不斷完善,在客觀上加大了市場對資金的爭奪,整個社會資金利率中樞有趨勢性上行態勢。
第四,機構投資交易行為轉變。債市監管制度趨嚴,市場交易類賬戶偃旗息鼓,一級半市場價差趨零,代持類交易驟減,去杠桿化加速,銀行間交易量不斷走低。作為需求主力的投資類機構一、二級交易亦受到影響,隨著收益率的不斷走高,投資意愿逐步下降。銀行理財賬戶失去了與其自營賬戶的交易權,雖然取得了法定的二級市場交易權,但受制于一些機構部門設置的限制,多數理財賬戶并未取得在二級市場直接交易的權利,限制了其波段操作。加之監管部門規范非標資產后,其絕對收益的吸引力使得理財賬戶更傾向于做大非標資產,而對標準債券的需求并未有多大提升。泛基金類機構債券需求不斷萎靡,主要傾向于高收益債券和通道業務,對普通債券的需求大大降低。需求端的行為變化直接導致供需矛盾加大。
最后,供給沖擊明顯。實體經濟資金需求增強,但信貸可得性降低,由此對銀行間市場直接融資的需求增加,造成債券供給不斷增加。另一方面,上述因素造成的需求萎靡以及需求轉向使得原本較為合理的債券供給量變得相對超需求,供需矛盾突出,一級市場帶動二級市場收益率不斷攀升。
筆者認為,現階段債券市場的走勢與基本面背離只是階段性的,并不能得出傳統的債市分析邏輯已經失效的結論。在利率市場化、金融體制改革不斷推進的背景下,政策措施超出市場預期實屬正常,對市場的影響也是必然的。債市人感覺迷茫是因為沒有用發展的眼光來看待市場的變革。隨著市場的逐步穩定,機構從業人員思維的轉變亦應有所突破,債券市場必將實現新的均衡。但是,債券收益率歸根結底取決于經濟的發展,通貨膨脹的高低,資金面和政策面的變化只是階段性的,雖然對中短期交易影響很大,但對長周期的大類資產配置影響有限。隨著本屆政府對經濟增長容忍度的提高,“調結構”、“促改革”的推進,債券收益率長期大幅背離經濟基本面并不可期,在到達一定高位后必將遇到天花板效應。
雖然筆者也和多數同行一樣處于迷茫期,感覺離市場越來越遠,但只要我們能在長期內堅信傳統債券分析邏輯,在中短期內及時適應市場的新變化,把握政策脈搏,深入分析各項政策的影響,相信市場還會與我們親密依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