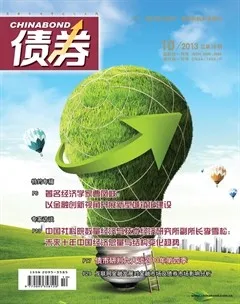邁向常態經濟的通貨膨脹和貨幣政策

盡管幾乎所有經濟學家都贊同弗里德曼的名言,即“通貨膨脹無論何時何地都是一種貨幣現象”(Friedman,1963),但貨幣主義的實踐并不理想。就連弗里德曼本人也承認,貨幣供應目標制并不如他希望的那樣成功(Nelson,2007)。現實中貨幣的超發并不會引起所有商品價格的同步上升。特別是,由于工資和大宗商品價格上漲速度更快,很多經濟學家都將通脹歸咎于成本快速上升,這也促使認同弗里德曼的學者們不得不認真思考成本沖擊對通脹和貨幣政策的影響,而這對當前的中國更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與1990年代之前物質短缺時期由需求推動引發的通脹不同,新世紀以來中國的物價上漲更多表現出成本推動特征。2006年以來的通貨膨脹就是在全球流動性過剩和初級產品國際市場價格快速上漲的背景下出現的。與此同時,國內工資也出現大幅上漲且部分地區開始勞動力短缺。與需求型通脹不同,在成本沖擊下,緊縮性政策可能造成有效供給不足,從而加劇經濟收縮壓力,成本推動型通脹治理難度更大。雖然應主要采取促進產出效率的供給政策,但這并不意味著貨幣政策毫無作用的空間。
伍戈博士和李斌博士的新作《成本沖擊、通脹容忍度與宏觀政策》(中國金融出版社,2013年出版)就是這方面研究的出色成果。作者并沒有僅僅針對成本沖擊來分析通脹,而是通過對日韓臺灣等典型經濟體和歷次國際大宗商品價格沖擊的考察,發現如果同時考慮貨幣供給因素,成本沖擊對通貨膨脹的邊際解釋力幾乎為零,這實際上強有力地支持了貨幣主義觀點。
雖然勞動力價格和國際大宗商品都屬于成本沖擊,但對總供給曲線和宏觀經濟影響不同。前者對總供給曲線斜率產生影響并在短期產生不可逆的中長期沖擊,而后者僅體現在斜率的變化。面對勞動力成本沖擊,應適當降低經濟增長預期并更多地改善效率提高供給,這對于正處于劉易斯拐點和人口紅利逐步消失,已經歷長達三十年約10%高速增長并將逐步回歸中低速度常態經濟增長的中國來說,具有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由于大宗商品價格沖擊是短暫且可逆的,因而決策者一般不需要考慮修正其既定的中長期經濟增長及通脹目標,但可以適當提高短期通脹容忍度。這種做法其實與1990年代以來很多國家采用的事實上的彈性通脹目標制策略是一致的。雖然不同國家策略不同,但Svensson(2002)認為只要是遵循跨期通脹和產出缺口模式,都是彈性通脹目標制,幾乎所有獨立貨幣政策的中央銀行都可歸為此類(Mishkin,2011),這對中國貨幣政策轉型也具有非常重要的啟示意義。
作者還對日益全面融入全球經濟情況下的成本沖擊和中國通脹新形勢,以及如何以成本沖擊的觀點看待貨幣數量論的現實背離等問題,進行了深入的分析。雖然研究的題目是成本沖擊,但該書具有非常強烈的貨幣主義色彩,這可能與作者身份有關。考慮到中央銀行家對通脹都持有高度警惕的職業心態,這對中國來說無疑是件大幸事。更難得的是,該書無論在理論模型、計量檢驗,還是在國際經驗比較等方面,都遵循了嚴格的學術規范,并且結合大量專欄案例深入淺出進行說明,邏輯嚴密結論可靠。通過該書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國宏觀經濟和貨幣政策,也可從中觀察未來貨幣政策當局的決策方向。
作者單位:廣東金融學院
責任編輯:廖雯雯
注:
Friedman, M., 1963, Inflation: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New York: Asia Publishing House.
Mishkin, F., 2011, “Monetary Policy Strategy: Lessons from the Crisis”, NBER Working Papers, No.16755.
Nelson, E., 2007, “Milton Friedman and U.S. Monetary History 1961-2006”,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t. Louis Review, Vol.89, p.153-182.
Svensson, L., 2002, “Monetary Policy and Real Stabilization”, Rethinking Stabilization Policy,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Kansas City Jackson Hole Symposium, p.261-3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