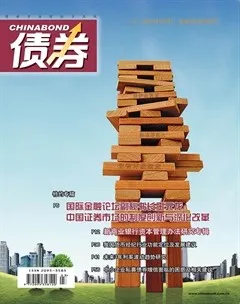未來3年利率波動趨勢研究
摘要:本文從庫存短周期視角出發,并結合利率市場化、劉易斯拐點等長期因素,研究了未來3年利率的波動趨勢。作者認為,若單純考慮短周期因素,未來3年利率將隨經濟先升后降,但考慮到利率市場化和劉易斯拐點等長期制度性因素影響,未來利率走平的概率較大,波動性有望下降,信用利差將趨于分化。
關鍵詞:利率波動 庫存短周期 利率市場化 劉易斯拐點
從短周期視角看,中國過去的庫存短周期一般為3年左右,我們認為,目前恰逢新一輪短周期的起點;從長期因素看,結合國外經驗和國內發展階段,我們認為未來3年將是利率市場化推進的關鍵時期,同時劉易斯拐點對通脹中樞的影響也可能顯現。
因此,若要探尋未來3年的利率波動形態,必須將短周期視角和利率市場化、劉易斯拐點等長期因素結合起來分析。
未來3年利率波動形態展望:從短周期視角出發
要分析未來3年利率波動形態,應采取經濟短周期分析法,先判定當前所處經濟短周期階段,再對未來波動進行展望。
經濟周期較為普遍地劃分為庫存周期、朱格拉周期和康德拉季夫周期,驅動因素分別是庫存變動、設備投資和產業演進,時間跨度分別為40個月、9-10年和50-60年,因此也被稱為短周期、中周期和長周期。根據時長接近性,未來3年這一時間跨度可從庫存短周期視角來分析。
3年內利率市場化的節奏猜測
未來3年,利率市場化等長期制度性因素將怎樣影響利率市場?要回答這個問題,需要對未來3年利率市場化的推進內容和節奏進行把握。
為了把握未來3年利率市場化的脈絡,首先必須明確目前我國利率市場化所處的階段。
我國利率市場化也屬于漸進式改革,從1986年拆借利率市場化開始計算,目前已經經歷了26年,而如果從1999年存貸款利率市場化實質性啟動開始計算,也已經歷了13年。
考慮到東亞國家和地區一般用時15年左右,且我國利率市場化也已經達到了“貸款利率管下限、存款利率管上限”的階段性目標,未來只需再進一步放開貸款利率下限和存款利率上限,因此,單從時間上考慮,我國利率市場化有可能在3-5年的較快時間內完成。
當然,作此推測離不開一系列的制度因素,包括國內經濟通脹環境穩定、顯性存款保險制度快速建立、央行調控方式和金融機構改革進一步推進等。在樂觀條件下,我國利率市場化已經具備了在3-5年內完成的條件,按此推算,未來3年將是以上一系列現象發生的關鍵時期。
3年內劉易斯拐點的影響判斷
近年來,有關中國通脹壓力將長期存在的論調甚囂塵上,邏輯是中國將迎來劉易斯拐點,此后工資將持續上漲,通脹中樞也將趨勢性上移。但從費雪方程式來看,價格應當由需求與供給兩方面共同決定:
根據上述理論,供不應求時就會產生通脹壓力。其中,貨幣供應的上升會增加需求,從而產生需求拉動型通脹;而資源、勞動力以及技術的瓶頸會影響供給,從而產生成本推動型通脹。人口瓶頸不過是影響通脹的一個因素,而資源瓶頸、貨幣供應以及技術進步都會對通脹產生影響,如果貨幣供應收縮,同時資源瓶頸改善,那么人口拐點也未必意味著通脹出現轉折點。對通脹的整體判斷需要綜合考察各個因素的影響。
由于西方主要發達國家早已邁過劉易斯拐點,日韓經驗對我國更有借鑒意義。日本在1960年前后、韓國在1980年前后,其農業勞動力轉移速度明顯放緩,這符合判斷拐點的數量標準,也代表它們各自邁過了劉易斯拐點。
先看韓國的例子。韓國在1980年左右跨過劉易斯拐點后,通脹中樞反而較70年代有明顯下降。而且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其實際工資1980年后持續攀升,但在1980-1984年間CPI和名義工資漲幅都是持續下跌的(見圖3)。著眼當時全球經濟背景,不難發現,70年代全球流動性泛濫,資源也出現瓶頸,其產生的疊加效應明顯高于韓國80年代人口瓶頸的單一影響,因此劉易斯拐點后韓國通脹中樞反而下降。
再看日本的例子。日本的通脹確實在1960年劉易斯拐點出現以后顯著上升,但是為什么其在1975年以后顯著下降呢?要知道,70年代中后期日本應該同時經歷人口、資源的瓶頸,但通脹奇跡般地下降了。另一方面,美國的劉易斯拐點顯然比日本更早,為什么同樣是在1960年通脹上升,而且持續到1980年,持續時間比日本還要長?
答案不在供給方,而在需求方的貨幣上:日本和美國在70年代采取了不同的政策應對。美國依然保持了寬松的貨幣政策刺激;而日本的貨幣供應在1974年以后就顯著下降,貨幣政策相對緊縮(見圖4)。日美案例表明,控制了貨幣,也就是收縮了需求,足以抵消人口、資源等供給瓶頸對通脹上升的影響。
日本在石油危機后仍緊縮貨幣的深層次原因,是前20年信貸高增、地價暴漲10多倍后,舊發展模式面臨日益增加的經濟、社會壓力,經濟轉型刻不容緩。日本1973年開始的經濟轉型,其一大特色就是嚴控貸款增速(貨幣增速)、壓抑地產,同時政府通過大舉發行公債(國債、地方債)、加大杠桿來對沖經濟下滑,取得了經濟轉型、增速維穩的成績,同時信貸、貨幣增速大降,通脹壓力大為緩解。
中國過去的經濟發展模式與日本轉型前類似,即經濟發展靠信貸,信貸擴張造貨幣,貨幣擴張導致通脹(滯后貨幣增速1年左右),通脹抬頭引發緊縮壓力,陷入循環波動的怪圈,發展模式不可持續。
如前所述,未來中國通脹中樞演變要綜合考慮劉易斯拐點、直接融資發展等長期因素,若政府在經濟轉型時期容忍經濟下臺階,控制信貸、貨幣,發展債券市場,則劉易斯拐點后未必通脹(見圖5)。
利率波動水平展望
綜上所述,未來3年利率的波動除了考慮短周期的波動形態,還必須考慮利率市場化和劉易斯拐點等長期制度性因素影響下的利率波動水平。
(一)利率債利率:維持穩定
從實際利率和通脹這兩個決定債券利率最重要的因素看,未來利率走平的概率較大。
從全球經驗來看,利率非市場化國家的實際利率大多低于市場均衡水平,負利率普遍存在。而在利率市場化時期,大多數國家和地區實際利率都有所上行,負利率基本消除。例如,美國(開始于1970年)、日本(開始于1977年)利率市場化后,負利率基本消除,達到與實際GDP增速接近或略高的水平。
另一方面,我們注意到,美國、日本利率市場化無論是始末點、進程還是結果都迥然相異,實際利率走勢卻如出一轍(見圖6),表明驅動兩國實際利率波動的,主要是全球經濟通脹趨勢、貨幣政策和國際資本流動等基本面因素,利率市場化的制度紅利不能否認,但也不宜夸大。
中國的實際利率(以5年期國債利率-CPI來衡量)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利率市場化初始階段出現大幅負值的情況,但此后逐步改善,目前已經為正,且2012年以來,盡管經濟通脹持續下降,但利率債收益率并沒有隨之下降,從而使得實際利率始終保持正值。
一方面,中國目前的實際利率已經為正,即便假定未來幾年中國利率市場化加速,但經濟下一臺階基本已成共識,實際利率需要攀升的幅度下降;另一方面,劉易斯拐點后通脹未必上升,且如果直接融資占比能顯著提升,那貨幣擴張速度將下降,通脹或已不是大問題。因此,從實際利率+通脹的框架看,國債名義利率應維穩。
直接從國債利率整體看,日本1977年利率市場化后,長債利率中樞相對比較穩定,并未出現明顯上移,且隨著日本經濟臺階式下移,日本國債名義收益率反而穩中有降(見圖7)。
中國長期國債利率從1986年債券利率市場化之后曾經有過一次飆升,在90年代甚至短暫超過了名義GDP增速,此后又再度大幅低于GDP增速。目前來看,兩者差距處于歷史中值上方,差距正在逐步縮小(見圖8)。未來伴隨著GDP實際增速的下降和通脹的穩定,即使長期國債利率保持不變,名義GDP增速和長期國債利率也有望進一步收斂。
(二)信用債利率:分化
美國信用債市場高度發達,日本卻只發展國債市場,其信用債市場十分滯后,中國信用債市場發展路徑主要是學習美國模式。
美國經驗表明,利率市場化過程中信用分化將不斷加劇,優質大企業發債成本趨于下降,高風險小企業發債成本上升,高低等級信用利差顯著拉大(見圖9)。結合美國經驗、中國實際,預計:(1)大型央企、政府支持企業的債券收益率穩中有降;(2)中小型民營企業的債券收益率穩中有升,發債主體范圍不斷擴大到信用資質更差、收益率更高的主體上,導致計算出的中低等級收益率顯著攀升。
整體債券利率波動率:趨于下降
利率市場化有助于市場主體經濟預期的穩定,從而使得完成利率市場化的國家經濟通脹的長期波動率出現下降。
以美國為例,利率市場化后,經濟通脹均值和波動率均出現了下降,相應長短端債券波動率也明顯下降(見表3)。
日本利率市場化后經濟通脹均值同樣出現了下降,經濟通脹波動率和債券波動率也都下降(見表4)。
因此,從日美經驗看,隨著利率市場化的推進和完成,預計我國經濟通脹均值有望逐步下降,而經濟通脹波動率和債券波動率也有進一步下降的空間。
小結
未來3年一系列關鍵因素將重合在一起,共同作用于中國的利率走勢:從短周期看,未來3年將經歷新一輪庫存短周期的啟動,利率或將經歷先升后降的過程。從長期因素看,未來3年我國也面臨轉型的關鍵階段,一方面,利率市場化將進入攻堅階段,利率有望與經濟增速逐步接軌;另一方面,劉易斯拐點后,通脹壓力的確會有所上升,但如果能控制住貨幣供應量,或者通過技術轉型突破資源瓶頸,再加上直接融資若能取得突破,將會對通脹起到明顯的緩解作用。
綜合來看,未來3年利率波動形態或將先升后降,波動水平有望維穩,信用利差將趨于分化,整體經濟、通脹和債券的波動率均會下降。
作者單位:國泰君安債券研究團隊
責任編輯:劉穎 羅邦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