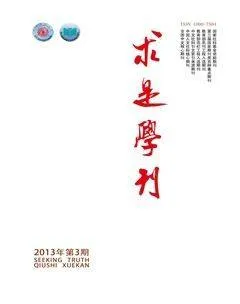后現代語境下的經典闡釋
文學經典的產生與構成并非一個自明的、孤立的存在。無論是西方語境下的“classic”或“canon”,還是漢語語境下的“經”、“典”之釋,經典都含有某種典范、權威、法則的意義,客觀上成為其他文本效仿和參照的范本。隨著后現代的來臨和文化研究的興起,經典面臨著被質疑、責難甚至解構的命運,其闡釋具有了多重意指和多元視角的張力,不可避免地帶有后現代的表征。
一、經典化:一種現代性的話語模式
按照通常文化分期的觀點,人類社會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的轉型導致了文化的前現代、現代和后現代的出現,這種文化分期又關聯著經典生產從傳統向現代的轉換:從古典(前現代)時期文學的本真性自為生產到現代時期經典的他律、建構行為,再到后現代的碎片式生產。文學經典系統隨著歷史語境的變化移步換景,流轉變異。雖然經典化是多種因素合力的結果,但在這樣的分期內,關乎經典生成的標志無疑是西方啟蒙運動以來的現代性。目前,關于現代性的內涵盡管有多種理解,但有一點是共識:現代性就是作為主體性的人所擁有的理性主義、個人主義和自由意識,它與理性、中心、自我、民族主義、殖民等密切相關。進一步說,現代性的興起、發展過程始終伴隨著資本主義的殖民擴張,現代社會所建立起來的規則、自由與資本主義的發展和殖民統治同步。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作為反思和批判現代性的重要力量,后現代主義視殖民性為現代性與生俱來的內在屬性,如利奧塔、湯林森都認為以殖民擴張為代表的資本主義是現代性的代名詞。基于此,資本主義可以憑借強有力的霸權話語、認同邏輯和利益需求預設文學經典品質的合法性,獲得場域內的支配權,使作品在同質化之中被傳播,然后以優越的身份自為存在著,即“強加了一種語言,現代性的語言,每個人都必須使用這種語言,不論它能否恰當地描述他們的現實”[1](P248)。因此,“這意味著‘現代’的話語——我們沒有思考就滑進去的話語——從來就不是純粹描述性的,它具有一段彼此爭鋒的話語歷史”[2](P51)。在后現代看來,經典是特定階層強化話語優勢的專有模式,所謂啟蒙與現代性的宏大敘事帶來的只是經典與權力的復雜聯系,其價值取決于自主的存在場與意義序列,折射出福柯所謂“權力話語”的運作機制。由此,作為一種話語模式,文學的經典化與現代性存在某種共謀關系。
從詞源學考查,“經典”作為文學的專用詞也是現代性的產物。據劉象愚考證,“經典”的英語對應詞classic最早是表示等級的術語,canon最早指一種度量工具,引申為“規則、律條”等意。直到18世紀之后,經典才是以文學形式存在的權威性文本。[3](總序)經典的豐富內涵為經典與意識形態的關系預設了彈性空間。因此,經典一進入文學場域,其等級、規則等就意味著先天帶有標尺的性質。這一切,直到現代性興起之后才成為可能。一個典型做法就是經典文本往往采用美丑二元對立的敘述模式,置入作為弱者的“他者”形象。比如,《魯濱孫漂流記》中,魯濱孫用槍和《圣經》馴化作為客體的星期五;《簡·愛》中,那個從殖民地來的女人伯莎·梅森不僅被作者用代詞“it”指稱,還以失語、瘋子等形象完全浸沒于作品敘事之中。諸如此類的文本,無疑是作家有意或無意以西方的立場、現代性的話語方式展開的歷史敘事。因此,這才有了后殖民主義對西方現代性的反思,只不過后殖民理論反思的重點是現代性中的殖民話語,批判經典文本中的歐洲中心主義和帝國意識。
二、表征性解釋與鑒賞性解釋:經典闡釋的共時維度
卡勒在《文學理論》中曾區別了兩種文本解釋方法:一種是文化研究對文本的“表征性解釋”,一種是文學研究對文本的“鑒賞性解釋”。[4]“表征性解釋”強調文化產品的基本社會政治結構問題,“鑒賞性解釋”強調文本解讀的審美實踐過程。這兩種解釋方法的背后反映出西方理論界長期以來關于經典的標準性和恒久性問題的論爭。因此,在后現代性語境下審視經典的歷時生成,揭示經典背后的社會和政治,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還應將其置于共時維度之中,揭示經典闡釋的不同立場。
以女性主義、后現代主義、后殖民主義等為代表的文化研究派認為經典的選擇不單純是一個文學行為,它關系到政治話語權的爭奪和民族文化認同問題,由此質疑經典的永恒價值。如女性主義批評對文學敘事中男性中心和男權話語系統對女性的遮蔽進行批判,后殖民主義者通過從文化角度反思現代性(殖民性),對西方文學中固有的種族偏見、地域偏見進行揭露。在這個意義上,文化研究對文學經典的詮釋呈現出去經典化和非精英化特征,更多秉承了知識社會學的立場;相反,一些學者則持守純審美的經典標準,維護經典的自律性和恒久性,對文化研究的“表征性解釋”進行抨擊。美國學者布魯姆堅持審美理想和精英批評傾向,在《西方正典》中認為經典的特質和遴選標準只能是“審美價值”。因此,閱讀經典是一種個人化、陌生化、精英化行為,與政治和道德無關。布魯姆還將女權主義、非洲中心論、馬克思主義、新歷史主義或解構主義等稱為“憎恨學派”,對其去經典化行為表示強烈不滿。經典的原創性如何才能一代代傳承下去?布魯姆提出“影響的焦慮”理論。在他看來,前代“強者詩人”創造的巨擘成就,使后代詩人無法走出其偉大作品和傳統的陰影,從而產生一種基于傳統“影響”的精神壓力和心理焦慮。為了避免這種焦慮,詩人可通過對前人作品的修正式誤讀、創造性校正等策略消除前輩的影響。這樣,“影響的焦慮”又給詩人提供一個超越前驅的支點,體現繼承傳統與張揚個性的統一。無疑,這是確保對經典進行“鑒賞性解釋”的有效途徑。
文化研究派對傳統經典觀的質疑和摧毀正是對現代性中的理性化、權威性和殖民性的回應。在文化研究者看來,自啟蒙運動以來的現代性把一切差異性、個別性納入到理性化和主體化的進程之中,加深了社會矛盾和文化危機。因此,二十世紀中葉以后,隨著多元文化的盛行,女性主義批評、文化唯物主義、后現代主義等對傳統經典的建構標準進行質疑,從文化立場剖析現代性的弊端,讓被壓抑的聲音講話,在對現代性反思、批判和肢解的后現代語境中尋求經典的闡釋維度,由此確立了一種他律的文化立場。在文化研究大行塵世的語境下,以布魯姆為代表的審美派強調作品的審美自主性和原創性的主導地位,無疑是對審美現代性的具體闡釋。他與文化研究者的爭執實際是“本質論”與“建構論”之間的矛盾。當然,布魯姆對經典問題的認識與當代美國的文化激進派和保守派的交戈論爭分不開。其實,無論哪一種闡釋行為,都不可避免地帶有一定的視域限制和主觀因素。布魯姆信誓旦旦地反對經典建構,但其《西方正典》中選取的26位作家也是一個以莎士比亞為中心、英語作家為主的體系,同樣帶有純個人的心理因素。
三、身份的焦慮與影響的焦慮:經典闡釋的身份訴求
無論是文化研究對文本采取的“表征性解釋”,還是恪守審美自律的“鑒賞性解釋”,其背后都隱含著因身份訴求而帶來的焦慮感。例如,女權主義者因文本中女性身份的缺席而產生“身份的焦慮”,以身體寫作來摧毀男權視域下的清規戒律和等級秩序;后殖民主義者基于文本中暗含的歐洲中心論以及西方對東方的扭曲產生了民族身份焦慮,通過改寫、重述等方式解構殖民者的話語侵略。尤其是近年來以薩義德、斯皮瓦克和霍米·巴巴等為代表的流散寫作,更因作者所處文化的雙重性及其位居的閾限空間,產生了嚴重的身份認同危機和無家可歸的焦慮意識。而布魯姆基于“影響的焦慮”建構起原創性和審美性經典系統,以恢復西方文學的“道統”,印證經典是“影響”的結果而非建構的產物,其最終也指向了身份訴求。
這種身份焦慮意識顯然與后現代語境密切相關。貝爾在《資本主義文化矛盾》中視人的身份變化和身份認同為現代社會的標記,這種身份認同在吉登斯看來,乃是隨著地方性和全球性的影響,由現代制度所直接塑造,而“在保持解放的可能性之外,現代制度同時也創造自我壓迫而不是自我實現的機制”[5](P6)。泰勒則在《現代性之隱憂》中揭示了當代文化和社會呈現的“三個隱憂”——意義的喪失和道德視野的褪色、工具主義理性猖獗面前的目的晦暗以及自由的喪失。在現代制度的影響之下,人開始走向焦慮、困惑和不安。另一方面,現代性發展過程也是資本主義以強勢話語、價值體系對其他國家的主體意識進行干擾、消解甚至取代的過程,這就勢必使其他國家的民眾在民族利益認同、集體意識感知和個人價值歸屬方面發生斷裂、失語現象,進而產生身份焦慮感。這在具有移民身份的學者那里表現尤其突出。如布魯姆作為猶太移民后裔,生活在充滿矛盾的美國主流社會中,自然擺脫不了西方強勢學者的“影響的焦慮”。為了克服內心的疏離、壓抑,布魯姆或通過《影響的焦慮》引入同是猶太人的弗洛伊德的精神學說,或在《誤讀之圖》中對美國學者愛默生贊譽有加,試圖以理論建構和“布魯姆式”的修正從邊緣階層移入主流社會。因此,置身于多元文化背景中,因身份的認同危機使得經典闡釋通向了身份建構和文化確認,帶有深刻的多重文化印跡,成為作家在異域中延續話語權的有效方式。
對于文學經典,我們可以以不同的方式接近它們。無論是布魯姆們,還是文化研究者們,他們對經典的言說不過是實現了他們各自的想法:將研究目標置于更廣闊的社會歷史視域中,為經典的重構和闡釋提供別樣視角。但無論怎樣的論爭、沖突,保持必要的思維張力和動態的、融合的視域是有益的,這應當為當下中國的文學發展提供某種啟示。
參 考 文 獻
[1] 謝少波,王逢振. 文化研究訪談錄[M].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
[2] 哈貝馬斯等. 文化現代性精粹讀本,周憲編[C]. 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
[3] 韋勒克,沃倫. 文學理論,劉象愚譯[M]. 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
[4] 陳太勝. 文學經典與文化研究的身份政治[J]. 文藝研究,2005,(10).
[5] 安東尼·吉登斯. 現代性與自我認同,趙旭東,方文譯[M]. 北京:三聯書店,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