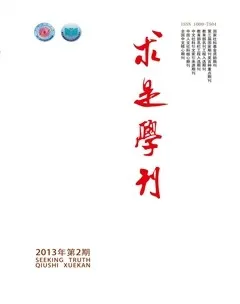尼采是“古希臘人”嗎?
摘 要:尼采并不反對(duì)一切價(jià)值觀,只是堅(jiān)持價(jià)值觀應(yīng)該服從于生命意志,在此前提下,尼采有其自己的一套價(jià)值觀。他并非直接將古希臘價(jià)值觀拿來(lái)與中世紀(jì)以來(lái)的所謂“奴隸道德”相抗衡,他所持的價(jià)值觀實(shí)際是經(jīng)過中世紀(jì)與近代主體主義熏染之后的古希臘價(jià)值觀。無(wú)論是尼采對(duì)古希臘價(jià)值觀的繼承,還是對(duì)它的背離,都有著濃厚的主體主義色彩。
關(guān)鍵詞:尼采;古希臘價(jià)值觀;主體主義
作者簡(jiǎn)介:張瑞臣,男,《云南大學(xué)學(xué)報(bào)》(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版)編輯,從事西方哲學(xué)史研究。
中圖分類號(hào):B516.47 文獻(xiàn)標(biāo)識(shí)碼:A 文章編號(hào):1000-7504(2013)02-0045-07
尼采從青年時(shí)代起就浸潤(rùn)于古希臘文化之中,單就其作品的名稱來(lái)看,他的多部作品都是以古希臘文化為題,而從其作品的內(nèi)容上說,古希臘文化對(duì)他的影響,或者說他對(duì)古希臘文化的解讀,幾乎遍及他的每一部作品。尼采逝世后的一個(gè)多世紀(jì)以來(lái),對(duì)他與古希臘思想之關(guān)系的研究,幾乎從沒有間斷過,關(guān)心存在史的海德格爾說他以顛倒的形式終結(jié)了形而上學(xué),而法國(guó)后現(xiàn)代主義與解構(gòu)主義諸家也毫不猶豫地將這位用“錘子”從事哲學(xué)的思想家引為同道。在尼采與形而上學(xué)、奴隸道德、虛無(wú)主義這些宏大的現(xiàn)象之關(guān)系——這幕熙熙攘攘的大戲背后,我們似乎應(yīng)該稍稍冷靜下來(lái)思考一個(gè)問題:尼采衡量和批評(píng)基督教道德與現(xiàn)代文化所用的尺度是古希臘的嗎?他在多大程度上繼承了古希臘思想,又在多大程度上偏離了它?本文試圖繞開尼采正面討論古希臘文化的文本,從一則考察現(xiàn)代科學(xué)求真意志的箴言入手,來(lái)看看這一問題。
表面看來(lái),《快樂的科學(xué)》第344節(jié)根本沒有提到任何古希ChE9589rK854ZuvRqLzPmVjBANNQl1LpAStkgMzB9/c=臘思想家乃至古希臘文化現(xiàn)象,通篇談的都是現(xiàn)代問題,但細(xì)讀之下會(huì)發(fā)現(xiàn),沒有對(duì)古希臘秩序觀的洞見,他根本不可能找到什么有力的武器來(lái)批判現(xiàn)代求真意志。從尼采研究界常用的宏大敘事話語(yǔ)框架來(lái)看,這一節(jié)研究的無(wú)非是現(xiàn)代實(shí)證科學(xué)的求真意志追求“另一個(gè)世界”,從而使得我們生活于其中的現(xiàn)實(shí)世界顯得“不道德”了,而這就違背和損害了生命意志本身,由此尼采產(chǎn)生了對(duì)求真意志的懷疑。這樣看來(lái),這一節(jié)文字不過是尼采眾多的批判基督教奴隸道德與現(xiàn)代科學(xué)的文本中的又一個(gè),毫不起眼。但如果我們深挖下去,問題就一個(gè)個(gè)出來(lái)了:尼采否定求真意志的價(jià)值觀1,是因?yàn)樗磳?duì)一切價(jià)值觀,還是拿了另一種價(jià)值觀作為判斷尺度?如果是后者,那么,這種價(jià)值觀的具體內(nèi)涵又是什么呢?從這種內(nèi)涵來(lái)看尼采所提出的解決之道,尼采究竟是不是“古希臘人”1呢?本文依此思路展開。
一、求真意志與道德
尼采的這一節(jié)文字分成三個(gè)部分,分別討論了逐層加深的三個(gè)問題:號(hào)稱沒有任何未經(jīng)檢驗(yàn)之物的現(xiàn)代實(shí)證科學(xué),其根基恰恰是未經(jīng)檢驗(yàn)的而又最為專橫霸道的,那就是求真意志;求真意志分為兩種類型,那就是“不愿受騙”與“不愿騙人”,前者是一種功利的考量,后者則有了道德的自律,是比前者更高的一種類型,但這種求真意志恰恰可能妨礙生命的成長(zhǎng);求真意志妨礙生命的原因在于它設(shè)立了“另一個(gè)世界”,將這個(gè)現(xiàn)實(shí)的世界判定為“不道德的”,既然如此,我們就應(yīng)該質(zhì)疑它。
1. 尼采看到,在19世紀(jì)盛極一時(shí)的實(shí)證主義思潮,其實(shí)代表了當(dāng)代科學(xué)的整體趨勢(shì),這種思潮的特征是,它已不相信之前時(shí)代種種自在地崇高的秩序及人對(duì)這些秩序的推尊與服從有什么意義,而是號(hào)稱它的倉(cāng)庫(kù)里的一切都是沒有預(yù)設(shè)的(即都是經(jīng)過證實(shí)的),任何信念只有停止成為對(duì)某種實(shí)在力量的無(wú)條件順服,向?qū)嵶C科學(xué)的方法論投降,才被允許進(jìn)入科學(xué)之中,因?yàn)槟菢拥捻樂?jù)說是盲目而愚昧的。這種思潮體現(xiàn)的正是現(xiàn)代文化的一種基本特征:人類有了檢驗(yàn)一切的雄心和志氣,可是正因?yàn)槿绱艘采隽艘环N史無(wú)前例的專橫與傲慢。
尼采對(duì)此洞若觀火。他說:“為了使約束生效,是否必須存在一種專橫強(qiáng)制的、絕對(duì)的信念,以便使其他信念淪為它的犧牲品呢?”[1](P216)這就是說,在科學(xué)自信滿滿地展示的武器庫(kù)的地下,掩藏著它最不愿意展示的一種偏執(zhí)精神,因?yàn)檫@種偏執(zhí)精神恰恰未經(jīng)檢驗(yàn)。但這種精神卻又專橫地要求其他的一切都必須經(jīng)受檢驗(yàn),它就是執(zhí)意要追求真理的那種不受約束的意志,它認(rèn)為,“沒有什么比真理更必要了;與真理相比,其余一切事物只有次等價(jià)值”[1](P216)。這種求真意志,實(shí)際上不是一兩個(gè)人的主觀意志,而是整個(gè)科學(xué)乃至現(xiàn)代文化的總體趨向,我們?cè)诤竺鏁?huì)看到,這種總體趨向?yàn)楝F(xiàn)代社會(huì)樹立了一種價(jià)值尺度,即以真理為好,以謬誤為壞。
2. 尼采認(rèn)為,求真意志不可一概而論,它分為兩種:比較初步的趨利避害和更高一等的追求,即探索真理與傳播真理。
首先,普羅大眾和相當(dāng)一部分的學(xué)者之所以學(xué)習(xí)科學(xué),從消極的意義來(lái)講,是為了防止受騙,即明辨是非,以免利益受損;從積極的意義來(lái)講,是為了促進(jìn)自己的福利,尋求自身利益的擴(kuò)大。在平常,這種想法的確可以使人獲得一種相對(duì)比較安寧的生活,但只要生活中出現(xiàn)那種煽動(dòng)家,或者只要我們對(duì)這樣的生活進(jìn)行一種根本反思,我們就會(huì)發(fā)生一種質(zhì)疑:“什么‘自己不愿受騙’真的就會(huì)少受損害嗎?危險(xiǎn)和災(zāi)難就會(huì)少些嗎?”[1](P216)上述表面上的寧?kù)o無(wú)法掩蓋其根基不穩(wěn)的事實(shí),因?yàn)椤澳銈儗?duì)生活的特性有何了解,從而判斷最大的益處是在于絕對(duì)的不信還是絕對(duì)的信?”[1](P216)比如,在“牛頓力學(xué)是否站得住腳”這樣的純自然科學(xué)問題上,持相反意見的雙方所發(fā)生的爭(zhēng)論,在普通人看來(lái),既無(wú)關(guān)乎生活,又令人傷神,似乎徒勞無(wú)益,雖然科學(xué)家們極力爭(zhēng)持,雙方都拿出同樣精深的證據(jù)來(lái)證明自己的觀點(diǎn),也認(rèn)為這樣的問題極為重要,是支撐生活的根本性問題,但普通人的態(tài)度,表面看來(lái)是不愿搭理,實(shí)際上是沒有能力決定自己的取舍,因?yàn)樗麄冊(cè)緦?duì)于科學(xué)的態(tài)度就只是一種工具理性的想法,只是拿科學(xué)來(lái)便利自己的生活而已。普通人寧愿選擇一些科普教材上的觀點(diǎn),或者人云亦云的說法,只要對(duì)生活沒有妨害就可以了。對(duì)于社會(huì)科學(xué)方面的一些根本問題,比如,“孺子入井,是否該救”等,普通人的態(tài)度同樣如此。
但尼采顯然不贊同這種常人的態(tài)度。因?yàn)檫@種態(tài)度無(wú)法面對(duì)生活中的一些根本性危險(xiǎn),比如煽動(dòng)家的出現(xiàn),就會(huì)鼓動(dòng)盲目的大眾,掀起巨大的災(zāi)難。尼采認(rèn)為,科學(xué)的實(shí)際存在已經(jīng)反過來(lái)證明,并非所有人都持這種常人的態(tài)度,還有一部分人持另一種更負(fù)責(zé)的態(tài)度。
其次,另一種態(tài)度就是主動(dòng)去拓展與深化真理,尼采將這種態(tài)度稱作“不騙人”,它包括追求真理(即“不騙自己”)與傳播真理(即“不騙他人”)。如果說上述的前一種態(tài)度只是功利的考量,那么,這里的態(tài)度就多了幾分崇高感,它對(duì)人自身有了一種自律,上升了一個(gè)層次,“于是我們就有了道德基石”[1](P217)。真理與道德如何會(huì)有關(guān)系?這兩者在現(xiàn)代人看來(lái)簡(jiǎn)直是風(fēng)馬牛不相及,追求真理如何就使人立于道德的基礎(chǔ)之上了呢?道德為尼采評(píng)價(jià)科學(xué)的求真意志提供了評(píng)判標(biāo)準(zhǔn),是整個(gè)這一節(jié)文字的根據(jù)所在,這也正是我們下文將要討論的核心問題,此處暫且按下不表。我們先順著尼采的思路走下去。
尼采認(rèn)為,追求真理實(shí)際上就是樹立了一種價(jià)值秩序,這種價(jià)值秩序表面看來(lái)是為了避免生活中的假象和錯(cuò)誤,實(shí)際上卻可能會(huì)走向堂吉訶德式的狂熱,或基督教那樣仇視與毀滅生命的原則,怎么會(huì)這樣呢?
3. 在最后一個(gè)部分,尼采道出了求真意志之所以走向敵視生命的原委。求真意志汲汲于追求真理,而且認(rèn)定真理一定是不同于現(xiàn)實(shí)世界的另一個(gè)世界,相較之下,現(xiàn)實(shí)世界就成了“不道德的”了,成了人應(yīng)該鄙棄乃至擺脫的對(duì)象。[1](P217)尼采的意思,并不是在保留科學(xué)真理的“另一個(gè)世界”的同時(shí),直接將科學(xué)求真意志的做法顛倒過來(lái),頑固堅(jiān)持現(xiàn)實(shí)世界,他所要求的毋寧是要整個(gè)地懷疑科學(xué)求真意志所設(shè)立的這一套將真理當(dāng)作一種超越性的終極目標(biāo)的價(jià)值秩序本身。
尼采說,求真意志是一種形而上學(xué)的信仰。尼采特意將“形而上學(xué)”加上重點(diǎn)號(hào),明顯有強(qiáng)調(diào)其詞源的意思:物理學(xué)研究的是這個(gè)世界的自然之理,而形而上學(xué)就是研究在此之后與之上者的學(xué)問,它的本性就是追求“另一個(gè)世界”的。尼采將這種信仰的源頭確定為柏拉圖與基督教,后者當(dāng)無(wú)疑義,而前者則有明辨的必要。柏拉圖那里的理念是事物所追求的理想狀態(tài),并不是后來(lái)基督教上帝的那種超越性、人格性存在,也并不處在我們可以思議的這個(gè)現(xiàn)實(shí)世界之外,并不在某個(gè)天國(guó)中——柏拉圖自己的確說過理念的世界是另一個(gè)世界,但那是在它不同于感性事物的流變的意義上講的,并不是說它完全超越于這個(gè)世界及其意義之外。1
觀其結(jié)構(gòu),我們不難明白支撐這一節(jié)的核心論點(diǎn)是:道德不應(yīng)戕害生命,而應(yīng)該為生命所設(shè)立,但求真意志背后的道德觀恰恰妨礙了生命,甚至仇視生命。但是問題在于,為什么道德不應(yīng)戕害生命呢?如果道德就是現(xiàn)代規(guī)范倫理學(xué)意義上的那些由人承認(rèn)與訂立的道德規(guī)范,又何來(lái)道德是否戕害生命的問題呢?尼采在行文中沒有交代這個(gè)問題,他選擇留給讀者自己去思考。
二、尼采眼中的古希臘價(jià)值觀
尼采沒有亮出的底牌,實(shí)際上是經(jīng)過他解讀的古希臘價(jià)值觀,而他的這一解讀是否適當(dāng),是否合乎古希臘人的本義,則是評(píng)判他的生命意志學(xué)說的根本。考察這一問題,是本文接下來(lái)要嘗試的任務(wù)。
尼采作品中提到“道德”時(shí),絕大部分是貶義,即指一種壓制生命意志的奴隸性道德,但也有少數(shù)地方是例外,這些地方間接透露出了他自己所持的價(jià)值觀:“只要支配道德價(jià)值判斷的那種功用僅僅是畜群的功用,只要人們僅僅考慮共同體的保存,而非道德的東西則恰恰與唯一地在看來(lái)對(duì)共同體之持久存在構(gòu)成危險(xiǎn)的事物中去尋求——那就不可能有任何‘鄰人之愛’的道德存在。假定即便在那里,也已經(jīng)有了體諒、憐憫、公正、溫和、相互協(xié)助的一種持續(xù)而瑣碎的實(shí)施;假定即便在那個(gè)社會(huì)狀態(tài)下,所有在往后得到‘美德’的榮譽(yù)稱號(hào),最終幾乎與‘道德’概念合為一體的的那些驅(qū)動(dòng)力也在活動(dòng)了——在那個(gè)時(shí)期,它們根本還不屬于道德評(píng)價(jià)的領(lǐng)域;它們還是道德之外的。”[2](P214)2緊接著,尼采明確指出,在羅馬社會(huì)的鼎盛時(shí)期,憐憫或許會(huì)受到稱贊,但同樣有別的人鄙視它,人們并不普遍地把憐憫本身當(dāng)作道德,因?yàn)榱_馬社會(huì)的道德全在于共同體的維持,這就明白無(wú)誤地指出了基督教道德的歷史性,它是在異于它的另一種道德觀的腹中生長(zhǎng)起來(lái)的,也就是說,它并非西方自來(lái)就有的,而是在與猶太文化的互動(dòng)中引進(jìn)來(lái)的。但尼采并非反過來(lái)肯定羅馬的道德觀,相反,他認(rèn)為羅馬的那種以群體的保存為目的的道德還是以苦和樂為標(biāo)準(zhǔn)的道德,這種道德是一種主次顛倒:“無(wú)論是享樂主義、悲觀主義,還是功利主義、幸福論——所有這些思維方式,皆依照樂和苦(它們只是附帶現(xiàn)象,而且完全是次要的)來(lái)衡量事物的價(jià)值,這些思維方式都是處在突出地位的思想方式和思想簡(jiǎn)單的東西,每個(gè)意識(shí)到創(chuàng)造力和某種藝術(shù)家良心的人,都會(huì)不無(wú)奚落,也不無(wú)憐憫地蔑視它們。”[2](P242)1這里已經(jīng)可以看出,他所欣賞的是一種創(chuàng)造力,一種起統(tǒng)治作用的、增長(zhǎng)著的意志[2](P248),就是后來(lái)他所謂的“權(quán)力意志”。這樣一種追求創(chuàng)造,追求生命力不受阻礙地發(fā)展的思想,并非尼采空穴來(lái)風(fēng)式的獨(dú)創(chuàng),而是其本有的。
尼采提出,要把人重新回譯成自然,也就是說,人要回到他的生成的源頭——自然那里。這樣一種與自然貫通一體,而又不局限于現(xiàn)代意義上的種種規(guī)范倫理學(xué)、功利主義倫理學(xué)觀點(diǎn)2的道德,不是作為內(nèi)心決斷的、狹窄的“善惡”意義上的道德,而是作為廣義的“好壞”的道德,即順從并推進(jìn)生命意志之生長(zhǎng),對(duì)生命意志有利者為道德,反之壓制生命意志者則為不道德——這里對(duì)于生命意志而言的利害已經(jīng)不同于上面所說的苦樂,它不再是一己的感受或群體的利弊,而是對(duì)存在本身的趨勢(shì)與方向的順從或阻礙。
我們暫時(shí)撇開尼采濃重的主體主義色彩不表,先考察一下,他那種與自然相貫通的宏大價(jià)值觀來(lái)源于哪里?無(wú)疑是古希臘的美德觀。著名的古典學(xué)家耶格爾(Werner Jeager)如此解讀古希臘的“德性”和“善”的概念:“一個(gè)器具、一個(gè)身體、一個(gè)靈魂或一個(gè)生物中的德性或卓越,并非偶然產(chǎn)生的,而是僅僅通過正當(dāng)?shù)闹刃蚝椭?jǐn)慎的技藝產(chǎn)生的。任何事物,當(dāng)它自己特定類型的秩序,它的有秩序之整體,成了最高的,而且被實(shí)現(xiàn)于它之中的時(shí)候,就變成善的了。”[3](P146)他的話至少透露了兩個(gè)事實(shí):首先,德性并非人及人的行動(dòng)所專有,它幾乎可以用來(lái)描述自然存在的或人造的任何事物,包括無(wú)生命物,它廣大而遍及于一切存在者;其次,德性的關(guān)鍵在于事物是否趨向于它所應(yīng)當(dāng)具有的那種秩序,當(dāng)事物成為它所當(dāng)是的那種格局和狀態(tài),亦即與該事物相應(yīng)的那種秩序(比如,美之于雕像,勇敢之于武士)的極致狀態(tài)體現(xiàn)于該事物中時(shí),古希臘人便認(rèn)為該事物是有德性的,是善的。耶格爾在下文中的一句話將這個(gè)意思說得更明白了:“請(qǐng)記住,表示‘善’的古希臘文(Agathos)并不僅僅具有我們賦予它的那種狹窄的倫理含義,而是與名詞‘德性’(Areté)相應(yīng)的形容詞,因而就意味著任何意義上的‘卓越’。從這個(gè)觀點(diǎn)來(lái)看,倫理只是萬(wàn)物爭(zhēng)取完善的努力的一種特定的情形。”[3](P146)可見,古希臘人眼中的“善”指的是“完善”,指的是“好”(在西文中,“善”與“好”原本就是一個(gè)詞)。也就是說,事物符合與趨向于其應(yīng)當(dāng)成為的理想狀態(tài),而不管它是真正達(dá)到了理想的狀態(tài)(實(shí)際上,那在現(xiàn)實(shí)生活中是不可能的),還是處在這樣的追求過程中,便都是善的;相反地,“不善”并非有某種明確的實(shí)體性狀態(tài)作為其標(biāo)準(zhǔn),不善僅僅是善的缺乏,也就是說,事物處在廢墜或惰性的狀態(tài),不追求它所當(dāng)成為的理想狀態(tài),便是不善的。古希臘人也據(jù)此價(jià)值尺度來(lái)評(píng)價(jià)人與事物是否具有德性,是否善:比如,赫拉克利特說人在糊涂的狀態(tài)下,靈魂是潮濕的,就像被莽撞的年輕人帶著走路一樣,這種狀態(tài)是不值得追求的,真正應(yīng)該追求的是智慧與世界上的那些“共同者”,而不是沉陷到無(wú)所用心的醉夢(mèng)狀態(tài)中去;蘇格拉底所謂的“德性即知識(shí)”,指的也是人要對(duì)各種有德性的狀態(tài)有清醒的認(rèn)識(shí),并主動(dòng)去追求它,而與這種有意發(fā)動(dòng)起來(lái)追求德性的狀態(tài)相反的,往往是無(wú)所用心、無(wú)所措意,或者陷溺到感性生活的享受中去,而不是有意追求某個(gè)明確的“惡”的狀態(tài)(古希臘人對(duì)中世紀(jì)基督教式的實(shí)體化的惡是很陌生的)——這就是他所謂的“人不會(huì)有意作惡”的意思,因?yàn)橐坏坝幸狻保鋵?shí)就已經(jīng)開始朝向德性,朝向理念,追求理念了。
到了中世紀(jì)基督教,人們的善惡觀與價(jià)值尺度發(fā)生了一種很大的轉(zhuǎn)變。這倒不是說,基督教將先前人們認(rèn)為善的東西顛倒為惡的東西了,而是說,它將古代人認(rèn)為客觀存在且召喚著人去遵從與追求的那套價(jià)值秩序內(nèi)化為上帝的觀念,這就意味著將它轉(zhuǎn)化為上帝這一人格主體所設(shè)立的對(duì)象,同時(shí)又將惡實(shí)體化為現(xiàn)世的一切造物內(nèi)在固有的特征——只要它們還存在于此世。但大體而言,基督教的價(jià)值觀仍然繼承了古代社會(huì)的兩個(gè)基本特征:一是古代的價(jià)值秩序雖然經(jīng)過了基督教上帝的內(nèi)在觀念化,但其大體格局——至少?gòu)男问缴峡础廊晃醋儯@就是說,古代人認(rèn)為好的事物,基督教承襲過來(lái),基本上不會(huì)將其全然顛倒,認(rèn)其為“惡”的,比如,勇敢、智慧、審慎、正義、健康等古代人討論得最多的德性,中世紀(jì)人依然認(rèn)其為善——當(dāng)然在具體教義上常有將古代非常重視的一些德目排得不那么高的現(xiàn)象,比如對(duì)知識(shí)、美等的看法在中世紀(jì)就發(fā)生了一些變化,但這和我們前面所說的意思并不沖突,也不在同一個(gè)問題層面,需要另撰專文討論。另一個(gè)和古代相似的地方是,中世紀(jì)人仍然深深地服膺于人之上的一些崇高理念和力量,以一種容易為啟蒙時(shí)代貶斥為“迷信”、“盲信”的熱誠(chéng),全身心地投入到上帝為他們規(guī)定下來(lái)的一些超越于人之外的秩序之中。
進(jìn)入近代以后,上帝雖然不再居于舞臺(tái)的前方,以絕對(duì)權(quán)威的口吻向人發(fā)布命令,但他化身為種種“絕對(duì)者”——實(shí)體、最高單子、絕對(duì)自我、絕對(duì)精神——的面目,以費(fèi)爾巴哈為整個(gè)近代哲學(xué)總結(jié)出來(lái)的“泛神論”的形態(tài)存在,但這不意味著近代價(jià)值觀只是與中世紀(jì)基督教價(jià)值觀的名號(hào)不同,換湯不換藥而已,因?yàn)榻鷥r(jià)值觀越來(lái)越傾向于要求以往的一切價(jià)值都須經(jīng)過人的認(rèn)可方能保持其地位。我們簡(jiǎn)單看幾個(gè)例子就明白這一趨勢(shì)了:這一點(diǎn)在笛卡兒和維科那里分別通過二人對(duì)自然事物和歷史事物的討論已經(jīng)非常明顯。維科認(rèn)為“真理即創(chuàng)造”,他固然認(rèn)為人能像上帝創(chuàng)造自然界一樣,從無(wú)到有地產(chǎn)生自己的創(chuàng)造物,但他的這一原則的真義并不在于主張人從上帝那里爭(zhēng)奪創(chuàng)造的主導(dǎo)權(quán),而在于人遍歷世界上的各種意義,所謂的“創(chuàng)造”就是對(duì)這些意義的經(jīng)歷,只有人經(jīng)歷過或可以經(jīng)歷的意義,人才能承認(rèn)其存在,維科甚至暗示,連上帝的存在也需要人的承認(rèn)。[4](P175-176)這并不意味著近代人以為那些價(jià)值是人創(chuàng)造的,而只是意味著,諸種價(jià)值需要人經(jīng)歷一遭,承認(rèn)其有價(jià)值,方才以充分的意義在人類的生活世界中存在,否則近代人會(huì)對(duì)其抱以懷疑的態(tài)度,乃至推翻它。我們看看后來(lái)的思想史就不難明白,維科的這個(gè)原則其實(shí)被整個(gè)近代延續(xù)下去了。最明顯的幾個(gè)代表是:萊布尼茨的單子看待其他單子乃至全世界的視角明顯是從個(gè)體主體內(nèi)部出發(fā)的,一切意義只有向個(gè)體主體的內(nèi)核或內(nèi)心顯現(xiàn),才被認(rèn)可為“存在的”;康德的現(xiàn)象主義同樣以事物向人的顯現(xiàn)(Erscheinung,顯象,與此相關(guān)的是Ph?nomen,現(xiàn)象)為基礎(chǔ),只有向人顯現(xiàn)出來(lái),即可以為人的直觀方式與范疇所理解的事物,才被認(rèn)為在這個(gè)世界上存在;黑格爾那里(《精神現(xiàn)象學(xué)》)的人,處在世界的“審核者”(Prüfer)的地位,我們當(dāng)然不能說世界的秩序是人所創(chuàng)造的,但又不得不承認(rèn),在黑格爾看來(lái),世界的秩序就是人所能理解的邏各斯,它有其客觀性,但同時(shí)又是人理解事物的方式,甚至它本身也是一個(gè)自身運(yùn)動(dòng)著的主體。
黑格爾之后,這種思想趨勢(shì)又發(fā)展到了一個(gè)新的階段:在人們紛紛對(duì)他進(jìn)行反叛的過程中,從費(fèi)爾巴哈和馬克思開始,以往的種種崇高的秩序與理念開始被人們認(rèn)為只是人類精神的產(chǎn)物,它們的存在不僅僅是以人的認(rèn)可為條件,而且簡(jiǎn)直成了人的創(chuàng)造物。費(fèi)爾巴哈在其《未來(lái)哲學(xué)原理》中指責(zé)前人所認(rèn)識(shí)到的一切世界秩序不過是人的思維的產(chǎn)物罷了,他認(rèn)為前人并沒有認(rèn)識(shí)到這一點(diǎn),而他自己則要在對(duì)這一點(diǎn)的明確意識(shí)之上,在“物質(zhì)”的基礎(chǔ)上,重建以前的秩序,這個(gè)秩序因?yàn)槠浠A(chǔ)已與前人那里根本不同,所以有理由比前人那里的世界秩序更堅(jiān)固。費(fèi)爾巴哈在試圖重拾古代“質(zhì)料”概念為我所用的同時(shí),也將以往的一切秩序都降格為思維產(chǎn)物,消除了它們的客觀性(這種做法恐怕是黑格爾及他之前的思想家們所不能接受的)。馬克思推進(jìn)了費(fèi)爾巴哈的“物質(zhì)”概念,將問題的重心放到了人類社會(huì)領(lǐng)域,他認(rèn)為離開與人的關(guān)系來(lái)談“物質(zhì)”,是一種抽象的、非歷史性的做法,沒有切中當(dāng)前現(xiàn)實(shí)問題的實(shí)質(zhì)。撇開馬克思與費(fèi)爾巴哈思想的重大差異——那已逸出本文范圍之外了——不談,他們共同接受的一點(diǎn)就是,事物的意義要由主體來(lái)賦予,離開人的思維與實(shí)踐,根本沒有獨(dú)立而客觀的意義,在他們看來(lái),談?wù)撃菢拥目陀^性反而是一種人為的做作,是一種不正常的主體性,簡(jiǎn)而言之,他們一致地推進(jìn)了對(duì)古代以來(lái)的世界秩序之客觀性的消解。在他們之后的種種思潮,比如,實(shí)證主義、歷史主義與生命哲學(xué),在這一點(diǎn)上都沒有什么根本性的突破。
在這樣的思想史背景下,尼采對(duì)古希臘價(jià)值觀的解讀,當(dāng)然受到他所處的時(shí)代背景影響。眾所周知,尼采對(duì)以溫克爾曼為代表的德國(guó)學(xué)者的古希臘文化研究深表不滿,認(rèn)為文藝復(fù)興以來(lái)歐洲人對(duì)古希臘文化的理解太受理性主義的影響,過于強(qiáng)調(diào)肅穆與寧?kù)o,認(rèn)為這種解讀方式背后是蘇格拉底以來(lái)的理性主義對(duì)“另一個(gè)世界”的追求(實(shí)際上就是他在上述那則箴言中提到的“求真意志”),而他本人則提倡一種生命意志與自然、宇宙一體貫穿的理解,將酒神精神及發(fā)源于酒神崇拜的古希臘悲劇突出出來(lái),作為古希臘真精神的代表。這些都為學(xué)者們耳熟能詳,但很少有人追究下面這些問題:為什么蘇格拉底、柏拉圖以來(lái)的秩序觀被尼采視作對(duì)生命意志的壓制?肅穆與寧?kù)o作為古希臘文化的基本特征,難道真是從代表古希臘真精神的古希臘酒神與悲劇文化中生出的歧路嗎?這種解讀方式背后,是否有尼采作為一個(gè)現(xiàn)代人所帶有的偏見在起作用?
三、尼采是古希臘人嗎?
按照海德格爾的觀點(diǎn),站在近代思想與現(xiàn)代思想之間隘口處的尼采,扮演了一個(gè)以顛覆形而上學(xué)的方式為形而上學(xué)送終者的角色。他以摧枯拉朽的偉力,發(fā)起了對(duì)整個(gè)形而上學(xué)史的激烈反叛,這種做法往往令人目眩,使人誤認(rèn)為他除了服膺前蘇格拉底哲學(xué)家(頂多再加上斯賓諾莎等個(gè)別近代思想家思想的一些個(gè)別的方面),簡(jiǎn)直將整個(gè)形而上學(xué)全盤推倒,而容易忽視他繼承古代、中世紀(jì)與近代思想的一面。
尼采對(duì)古希臘價(jià)值觀的改造有兩個(gè)方面,這兩個(gè)方面都體現(xiàn)出近代思想對(duì)他的直接影響。首先,他堅(jiān)持作為“好壞”的那種廣義的貫通性價(jià)值觀。這種廣大的價(jià)值觀并非只在涉及人與人之間的利害關(guān)系時(shí)才冒出來(lái),而是與人和萬(wàn)物都須臾不可離的,因?yàn)樗P(guān)乎存在本身,而不僅僅關(guān)乎倫理行為。從隱而未發(fā)的質(zhì)料狀態(tài)、潛在狀態(tài)到內(nèi)在力量完全實(shí)現(xiàn)出來(lái)的狀態(tài)之間,有一條連貫的道路,但凡符合這條道路由下往上之指向性的事物,都被視作“善”的,反之怠惰、乏力、卑躬屈膝或中輟等種種現(xiàn)象,就被視作不善的。在這里沒有與現(xiàn)實(shí)世界相分離的,處在另一個(gè)世界的理念或上帝,也沒有什么人與其他造物從存在伊始就帶有的“原罪”。尼采的這一思路,毫無(wú)疑問是來(lái)自于古希臘的,因?yàn)槲覀儫o(wú)法從猶太教、基督教價(jià)值觀乃至近代功利主義倫理學(xué)與規(guī)范倫理學(xué)中找到可以為尼采提供這一強(qiáng)勁思路的思想資源。
但是,繞開中世紀(jì)以來(lái)直到黑格爾為止曾經(jīng)風(fēng)行過的種種有神論、泛神論與觀念論的價(jià)值觀,而到自然與生命中另尋世界之根基的做法,卻并非尼采的獨(dú)創(chuàng),而是源于近代思想的影響,我們最少也可以將這一影響上溯至費(fèi)爾巴哈。費(fèi)爾巴哈認(rèn)為,中世紀(jì)以來(lái)的哲學(xué)都在觀念和精神的范圍內(nèi)打轉(zhuǎn),都沒有超出主體觀念的范圍(無(wú)論這個(gè)主體是上帝,還是近代哲學(xué)所設(shè)置的理性、絕對(duì)精神等),費(fèi)爾巴哈還將這種觀念性最終歸結(jié)為人類精神與思維的產(chǎn)物,而他自己則主張走出這種觀念性之外,因?yàn)樵谥黧w觀念性之外,已經(jīng)有物質(zhì)作為這種觀念性的前提了,物質(zhì)是原本就已存在的前提,而不是我們?nèi)嗽O(shè)立的什么對(duì)象,在人這方面,與這種物質(zhì)相對(duì)應(yīng)的認(rèn)識(shí)方式是直觀和愛,而不是前人所重視的理性概念。費(fèi)爾巴哈并非要走向概念之前的神秘主義,而只是要在物質(zhì)這一新基礎(chǔ)上,重新改造與吸納以往人們對(duì)自然、社會(huì)和精神領(lǐng)域的種種認(rèn)識(shí),或者說在物質(zhì)基礎(chǔ)上將那些認(rèn)識(shí)重新建立起來(lái)。這樣重新建立起來(lái)的認(rèn)識(shí),就不會(huì)再以思維的產(chǎn)物代替物質(zhì),而是直接與物質(zhì)相貫通。為此,費(fèi)爾巴哈甚至將自己的物質(zhì)觀上貫到古希臘的“質(zhì)料”概念。[5](P20)尼采提倡生命意志的做法與此如出一轍,尼采重視生命意志,其實(shí)并非主張完全拋棄理性、秩序、崇高等,恰恰相反,他只是要在新的基礎(chǔ)上,即在現(xiàn)實(shí)世界的基礎(chǔ)上,重新建立起一種不妨礙生命本身之生長(zhǎng),而為這種生長(zhǎng)服務(wù)的秩序。
其次,他的價(jià)值觀又帶有濃厚的近代主體性特征。尼采這里自然生發(fā)的力量,并非如古代那樣從質(zhì)料狀態(tài)中涌現(xiàn)出來(lái)的追求理念的非主體性力量,而是一種主體,這個(gè)主體嚴(yán)格區(qū)分內(nèi)在意志與外在世界,這一點(diǎn)從尼采將這種力量先后稱作“生命意志”和“權(quán)力意志”的做法中,便可見一斑。意志總是主體的意欲,是一種時(shí)刻尋求付諸實(shí)行的控制性欲求,它不可能如古代人對(duì)自己的定位那樣,將自己視為自然涌現(xiàn)過程中的一個(gè)全身心參與者,視為自然洪流的一個(gè)通道而已。在尼采這里,價(jià)值成為生命意志自身的設(shè)定,任何外來(lái)的壓制性價(jià)值,生命意志都不予承認(rèn),除非它主動(dòng)設(shè)立這樣一種壓制性價(jià)值,也就是說,價(jià)值絕對(duì)不能妨礙生命意志自身的生長(zhǎng)。尼采價(jià)值觀的這個(gè)方面,與近代以來(lái)主體要求一切價(jià)值與意義都必須得到自身認(rèn)可的趨勢(shì)完全一致。
那么一個(gè)關(guān)鍵的問題是,在尼采這里,是主體服從于價(jià)值本身,還是價(jià)值服從于主體呢?由于尼采的生命意志在外延上絲毫不遜色于叔本華的“求生意志”,它存在于萬(wàn)物之中,所以上述貫通性價(jià)值觀中的種種價(jià)值,全部成為生命意志自身的設(shè)定物。也就是說,價(jià)值完全服從于主體,而主體的根據(jù)不在別處,就在主體自身,一切都為了主體的自我確認(rèn)而存在,而主體的意志是一種只以該意志的擴(kuò)張為目的的意志,即為“權(quán)力意志”。
經(jīng)過上面的考察,反觀《快樂的科學(xué)》第344節(jié)中的論述,尼采對(duì)求真意志與道德之間關(guān)系問題的觀點(diǎn),也就不難理解了。在尼采看來(lái),求真意志并非與道德了無(wú)干系,它反而以一種強(qiáng)勁的道德為基礎(chǔ):以真為道德的,以偽為不道德的。正是因?yàn)榍笳嬉庵緦⒏行缘默F(xiàn)實(shí)世界判定為變動(dòng)不居的“現(xiàn)象”世界,充滿了假象與迷惑,所以才認(rèn)為它“不道德”。這樣的求真意志,在尼采看來(lái)只會(huì)妨礙生命意志,它不啻于西方精神史上的一種病毒,所以尼采總是不忘抓住機(jī)會(huì),對(duì)現(xiàn)代世界引以為傲的真理觀,乃至其先祖蘇格拉底以來(lái)的整個(gè)西方價(jià)值觀大逞顛覆之能,痛加撻伐。但尼采這位善于洞察種種狐假虎威的衛(wèi)道士背后弱點(diǎn)的思想家,恰恰可能對(duì)自己背后的根據(jù)反思得不夠:上述近代哲學(xué)流傳下來(lái)的主體性特征,恰恰是尼采的軟肋。
參 考 文 獻(xiàn)
[1] 尼采﹒快樂的科學(xué),黃明嘉譯[M]﹒桂林:漓江出版社,2007﹒
[2] 尼采﹒論道德的譜系·善惡之彼岸,謝地坤,宋祖良,程志民譯[M]﹒桂林:漓江出版社,2007﹒
[3] Werner Jaeger.Paideia:the Ideals of Greek Culture,Vol. II:In Search of the Centre,trans. by Gilbert Highet[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43﹒
[4] 維柯﹒新科學(xué),朱光潛譯[M]﹒北京:商務(wù)印書館,1986﹒
[5] 費(fèi)爾巴哈﹒未來(lái)哲學(xué)原理,洪謙譯[M]﹒北京:三聯(lián)書店,1955﹒
[責(zé)任編輯 付洪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