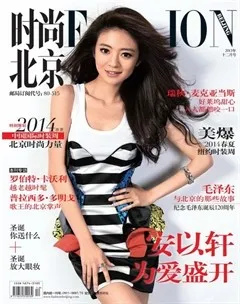潘怡良 女王很酷



做針織服裝設計的人最驕傲的事兒莫過于被同行問到,你這塊布料在哪里買的。答曰:“這是我自己織出來的。”潘怡良被稱為臺灣的針織女王,她不是簡簡單單“唧唧復唧唧”地織布,她是可以織出高級定制的立體服裝。她皮膚白皙,柔和輪廓的臉型,直發齊劉海、高鼻梁大眼睛,美美的,她所詮釋的衣裳的美是多變的,亦酷亦優雅,亦簡約亦神秘。
款款熠熠閃光的針織禮服有著迷人的背后。經過立裁得出版后,潘怡良會再計算,然后用機器把禮服織出來,紗線的旦數與密度等計算精準,才能保證禮服的合體。普通設計師可能只能織出一張張針織布,再去裁剪成衣服,潘怡良的計算過程像個謎。
用白坯布立裁,在原型紙板上畫版,再計算,在日本文化服裝學院這堂將立體裁剪運用到針織服裝上的課程曾讓潘姑娘頭疼,現在卻成為了她將服裝“計算”出來,并且“零失誤”的獨門絕技。
去日本學習之前,潘怡良早早就在家里針織工廠的氛圍中體會到可能會陪伴她度過一生的她熟悉的紗線。兒時的她只看到工人們在那兒“唰唰唰”,她不懂工藝,不在乎棒針或是鉤針,只見那一團團各種顏色的紗線,很好玩。偶爾學校舉行典禮式的活動,家里人會給她織一身針織小禮服,這讓她在同學當中很是特別。
家里的針織工廠在80,90年代主要接美國、日本的外單線。在她長大的過程中,工廠由于整體人力成本的提高,逐漸往內地轉移,留在臺灣的生產線越來越精致化。未去日本,潘怡良也在家里合作的日本服裝公司身上看到了他們的嚴謹,留給她最經典的畫面是,來工廠談合作時,日本人會用手擦拭機器看上面是否有灰塵。
從出了名的又講理論又培養動手能力,學生經常熬夜學習的日本文化服裝學院畢業以后,潘怡良回歸到家中的事業,做日文翻譯,有時讓師傅們跟她一塊兒實驗做新款針織服裝。在日本學習了從基礎工藝開始的織品設計制作的本領,可是到了工廠實踐后她發現,很多細節做法又跟學校學的不一樣,最明顯的不同是,學校用原型設計出的板型,在實際應用中,由于人們年齡的增長體型的變化,不能套用,需要不斷改變,以適應不斷變化的體型標準與非標準體型的消費者。早已走精品路線的工廠有許多針織工藝功力深厚的師傅,他們重視細節,如何體現針織的垂墜感,又如何讓某個細節更加挺括,如何把扣子縫得靠上一點避免垂墜帶來的誤差,如何用工藝去控制讓一件外套更加挺括,潘怡良認為那是影響她對針織的認識最深刻的幾年時光,她也在那段時間做出了自己滿意的針織魚尾裙。
潘怡良將針織的垂墜感利用到極致,這支優雅線條的針織禮服路線,從她90年代在工廠與師傅們研究開始,從未間斷。中間遇見過張梓琳,她在被選為中國小姐,再參加世界小姐的競賽時,請潘怡良為她量身定制,最后穿上那套后來廣為人知的經典藍色金蔥紗針織禮服奪冠,那也成為歷屆世界小姐奪冠禮服中第一件針織禮服。
潘怡良對人們穿衣的適度比例有很精準的感受力,連衣裙的線條在哪個角度時會表現得更優雅,迷你裙會在幾公分時最好看,她在未學設計之前就對此有天生的很強的判斷能力,她曾以此為興趣,“看人家的服裝,這個長一點,或者那個短一點,會更好看些”,這樣的興趣成為她后來做禮服設計與生俱來的優勢。
那條針織禮服的優雅路線延續到現在,是剛剛結束的中國國際時裝周上的表現,潘怡良受設計師張肇達邀請,與其同臺演繹禮服系列。“你的那幾個切割線,切到我心里了。”張肇達開玩笑地說,在看完潘怡良去年那場“末日”的發布后,他發出這樣的感嘆,因為造型、因為比例、因為切割線,二人所用材質與設計風格雖不同,但是視覺上的節奏感卻能調和在一起。
在經歷許多年無數次演變后,作為很成熟的作品,潘怡良的針織禮服識別度很高,成為經典。
針織作品的設計最后成形的過程有時是在機器上完成,對于潘怡良來說,那個等待的過程會讓她欣喜焦急,不過,創作時最痛苦的不是等待服裝織出來,而是你明明知道你一定有一款最滿意的設計,可是那在你腦海里還沒有勾勒出來。
這個時候,她會很焦急。“跟朋友們吃飯,喝酒,唱歌,都不能讓我高興,那個怎么還沒有跑出來?在哪里?為什么我還看不到?”潘怡良會進行這樣的思想運動。
去年“末日”主題發布,當最后的“有點露又不太露,線條纏繞的”那件作品做出來時,當時她就覺得,“哇,這60套衣服中,終于有一套最棒的!”
她熱愛設計。當一種風格已經確定后,她卻不想把自己禁錮在唯一的風格里。她喜歡搖滾,鉚釘,哥特風,神秘黑,與優雅女人味截然不同的個性,是藏在優雅禮服背后的另外一面,如果不能在禮服上融合酷酷的重金屬音樂,那就換個玩兒法。
“末日”體現了她手工制作的精致,很多針織作品完全是用立裁的方法織出來,她在針織元素中加入雪紡、絲綢、皮革,在濃重的黑色,獨特的紋理、結構與層次設計之下表達她對個性的追求。
“其實我一開始沒有打算全用黑色,后來做了很多套黑色之后,發現其他的顏色不好加進去,所以就干脆全用黑色,還挺酷的。”潘怡良說。黑色,山本耀司的黑色,川久保玲的黑色,潘怡良的黑色情結可以拉回到曾經在日本,學生們受那些日本80年代設計師影響的時代。
媽媽把她過去那套靈感來源于18,19世紀法國宮廷風格的畢業作品珍藏至今,只是,她自己在變化。“我沒想過自己要當公主,可是后來發現我很多發布秀的最后壓軸作品,一男,一女,女生總是有蓬蓬袖,那時我認為那個是好看的。”潘怡良說。她喜歡優雅,也喜歡簡約,后來又很喜歡前衛,視覺強烈的風格。“我得做我自己。我本身就想做一個快樂的設計師,沒有一點刺激我是不行的,哪怕今天變哥特,明天變朋克,哪天再變搖滾,我不變我受不了。哪怕那一件不賣錢,我也不要因為各種原因改變這個。”她說。
今年與華孚合作高級成衣設計,與過去的禮服與去年的“末日”完全不同,表達了她在成衣設計上的簡約風格,明年她又將與旭化成合作發布,事實上,10多年來,她參與了國內外許多交流展示活動,每一次新的合作都會帶給她對未知的好奇與新收獲的滿足,設計行為不斷繼續著。
“什么樣的東西最好賣?
“是我現在自己最想穿什么,那個最好賣。”
在她的作品從純粹做概念,到其中市場需求的比例逐漸增大,從高端的高級定制到禮服,再到針織與梭織結合,純粹成衣作品的同時,品牌也在發展。
早在90年代,潘怡良為了將來設計師品牌的發展,在臺灣輔仁大學織品研究所學習了品牌的運作,畢業論文為“文化產業結盟所產生的不一致對品牌形象偏好度的影響”,具有共同文化訴求的,不同領域的產品是可以合作共贏的,后來GIOIA PAN品牌在臺灣也與奔馳酒、酩悅香檳等高端品牌跨界合作。
“按這個脈絡來想,其實您那時就已經想過自己的規劃,我需要做什么?”
“對。品牌是可以經營多類別產品的,比如我喜歡喝酒,我有可能在我的店里賣紅酒,其實還可以賣眼鏡等。我當時為什么把品牌定位定得很高。我不是只要走高的路線,可是當我走很高的路線后,我再來走副牌,走中端時,可以降下來,會賣得很好,可是如果開始做低端的話,是上不去的。這些都不是在你做品牌以后才出現的,而是在還沒有做品牌時你就把整體規劃好了。”
當品牌的高端形象已經很強烈后,純粹追求優雅的禮服路線,從做品牌的角度來說,發展速度相對較慢,純粹追求個性與前衛的設計,產品又需要2,3年之后才好賣,潘怡良在不斷調整,保持經典,又努力去實現品牌延伸,建立品牌的架構。從外界來看,本來是一條路線,后來又多了女裝,本來主要是女裝,男裝又從僅僅是秀場上的點綴到男裝產品線。
潘怡良身邊從1個助理到多個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