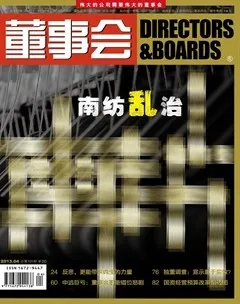意識匱乏何談內控
有關部門2012年4月對境內外同時上市的67家公司做了一份內控調查,報告顯示,內部控制存在缺陷的有49家,占比高達73.1%。
像導入其他的管控工具一樣,內控的導入也需要引進專業的人才和投入必要的成本。一項政策能否真正落實到位,關鍵是看其背后的利益驅動機制設置。但在很多上市公司看來,編制內控報告僅僅是一項應盡的義務。某上市公司老總直言,“內控規范對公司來說無非是根據上市要求,寫寫內控規范手冊而已。不知道公司做這樣的內控建設到底價值何在?”
從解決信息不對稱的角度來看,內控報告應該服務于不參與經營的外部投資者,為其提供甄選投資機會的依據,但上市公司的信息發布似乎并沒有堅持這樣的立場,而是精心鉆研“消息市”的運作機制。2011年,凱迪電力董事長陳義龍喊出了“1萬億”的響亮口號,將凱迪電力的股價拉升至25.25元。遺憾的是,緊接著這則消息的不是高瞻遠矚的市場布局,而是凱迪控股“6個月內不低于5%”的大幅減持公告。
若嚴格按照財政部、證監會等五部委下發的《企業內部控制基本規范》、《企業內部控制配套指引》,上市公司要建立起內部環境、風險評估、控制活動、信息與溝通、內部監督五環相扣的內控體系的確需要耗費大量的人力和財力。但從追逐利潤最大化的公司本質來看,上市公司缺乏盡心進行內控的源動力。試想一下,上市公司是內控報告的編制主體,但內控報告的受益主體卻是外部投資者,上市公司怎么會心甘情愿地花錢向“外人”揭露自己的短處?
從科學管理的角度來講,管理模式必須適用于企業自身所處的發展階段。對比西方400年的企業史,除了舉全國之力構建起的央企巨頭,中國的大部分企業都尚處在成長期,其管理主題表現為“成長、發展”,而非“統一、管控”。所以,內控缺失恰恰是中國企業特定發展階段的真實寫照。
很多人認為,在審核制的背景下,過了IPO這道門,昔日的“游擊隊”就脫胎換骨般地加入了“正規公司”的行列。從書面制度建設來看,在中介機構的協助下,這種蛻變完全可以速成,但企業不可能在一夜之間從成長期跨入成熟期。當然,追逐私利的小老板也不可能搖身一變成為拯救股民的救世主。
真正提升上市公司的內控質量,強制執行監管部門下發的某項規定顯示不是標本兼治之策。從本源來看,必須使內控主體與內控受益群體的利益保持高度一致。有關調查顯示,實施股權激勵的上市公司內控水平明顯高于未實施股權激勵的公司。在眾多直接參與經營管理的激勵對象監督下,內控主體與內控受益群體之間的信息不對稱程度大大降低,這縱然不能改進內控的系統性,但卻可能提升內控信息的真實性。
站在上市公司掌門人的立場上,是否推進內控,關鍵取決于內控能否給上市公司帶來價值。這就需要回答一個本源的問題——內控的本質是什么?內控不是簡單地照章披露信息或者避免造假,而是推動企業高管層從注重業務管理向強化公司治理的思維跨越,注重塑造長期企業價值,而非僅僅關注短期業務利潤。
上市公司區別于非上市公司,關鍵在于企業價值的體現方式不同,前者靠可預期的盈利能力,后者靠已累積的財務利潤。如果我們要堅持IPO的審核制,那么作為管理當局,不能僅僅審核擬上市公司過去的業務,更應該審核擬上市企業老板的價值取向。
不要懷疑中國人的聰明才智,只要意識轉變、激勵到位,任何難題都可攻破。內控,真正缺的不是人才和標準,而是提升企業長期價值的內控意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