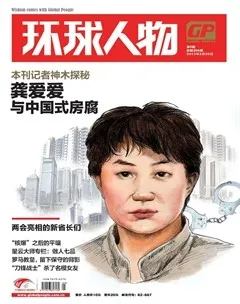“車和人一樣,活的就是口氣”



天空湛藍(lán),殘雪未消,大片的雜草中,一列列蒸汽機(jī)車安靜地躺在鐵軌上……李彥平眉頭皺了皺,嘆了口氣說:“車和人一樣,活的就是口氣。車淘汰了,沒人理了,就成了今天的樣子。”
46歲的李彥平是呼和浩特鐵路局包頭西機(jī)務(wù)段的一名司機(jī),從蒸汽機(jī)車、內(nèi)燃機(jī)車到電力機(jī)車,他跟機(jī)車打了近30年交道。“人生最好的十幾年,都是在這上頭過來的。”
蒸汽機(jī)車曾是一個時(shí)代的象征,從1952年新中國生產(chǎn)出第一臺蒸汽機(jī)車,到2005年最后一輛蒸汽機(jī)車退役,半個多世紀(jì)里,它不但承載著人們遠(yuǎn)行,更承載著久別重逢的渴望與喜悅。如今,這些蒸汽機(jī)車已消失在人們的視線中。李彥平這批司機(jī),也就成了最后一批蒸汽機(jī)車司機(jī)。
跑一趟車要添近30噸煤
李彥平對蒸汽機(jī)車的情感,源于父親。李彥平的父親參加過抗美援朝,后來在包頭到蘭州的鐵路線上干了大半輩子。在他的記憶里,每當(dāng)父親穿上工服,拿起裝著飯盒和洗漱用具的籃子時(shí),那就是又要出車了。“后來,父親年齡大了,開不了車了,就負(fù)責(zé)機(jī)車的質(zhì)量檢修。他一輩子沒離開蒸汽機(jī)車。”
父親的車到站了,兒子的車開動了。1985年,18歲的李彥平接了父親的班。雖然從小聽著火車汽笛聲長大,但真上了車,他才知道這個“鐵飯碗”不好端。李彥平邊比劃邊說,蒸汽機(jī)車由3部分組成,前面是蒸汽機(jī)和鍋爐,中間是司機(jī)室,后面是煤水車——上半部分盛煤,下半部分裝水。所以,要想讓這個鐵家伙跑起來,需要3個人,司爐、副司機(jī)和司機(jī)。“司爐?”記者怕沒聽清,又問了一遍。李彥平笑了笑,說:“司爐主要負(fù)責(zé)燒鍋爐,副司機(jī)除了燒鍋爐還要給機(jī)車加油,司機(jī)就是開車。想當(dāng)司機(jī)必須得先干司爐,把煤燒夠了,才有資格開車。”
當(dāng)時(shí)的解放型機(jī)車,跑一趟包蘭線10多個小時(shí),要“吃”掉近30噸煤。“我要干的活,就是把這些煤從后面的煤水車一鍬鍬地鏟到前面的鍋爐里。一趟下來,除了眼仁是白的,從頭到腳全是黑的。”那會兒,他們最怕遇到刮風(fēng)和上坡,不使勁給煤,那鐵家伙就會撂挑子。“算沒算過一分鐘要鏟多少鍬?”記者問。“有人說最多的時(shí)候得50鍬,咱也沒算過,哪有空數(shù)那個!”李彥平笑道。
“那時(shí)候的人就是能吃苦,還有一點(diǎn),就是不能給師傅丟臉。”李彥平說,他們剛上車時(shí),都有師傅帶,一般就是車上的副司機(jī)。一趟車上,兩個人要輪流運(yùn)煤,師傅還要給機(jī)車加油。“以前有個干司爐的小伙子,因?yàn)閷?shí)在干不動,火車一到站就坐在地上哭了。開始,師傅還想替他,但后來怎么都不行,最后這個小伙子就被調(diào)去做其他工作了。”
這一路上,司爐除了運(yùn)煤還得留心看著火候,不能讓煤燒得太急,如果沒到地方就沒煤了,那可是大事故。此外,司爐還得給車加水,清理煤灰、煤渣,到站了還得擦洗火車頭。把這個“吃煤喝水”的家伙伺候好了,李彥平才能休息,“累得就想直接倒在床上。”
火車司機(jī)有“三怕”
1994年,李彥平終于當(dāng)上了蒸汽機(jī)車司機(jī)。“如果說以前費(fèi)的是體力,當(dāng)司機(jī)耗的就是心力。”他說,司機(jī)最重要的就是保證行車安全,蒸汽機(jī)車卻有一個要命的問題:視野不好。司機(jī)室前面的鍋爐就像堵墻,把前方堵得嚴(yán)嚴(yán)實(shí)實(shí);兩側(cè)的小窗也常被蒸汽機(jī)噴出的霧氣弄得模模糊糊。唯一的辦法,就是打開窗,探出半身去看。“夏天還好,冬天可就遭罪了。內(nèi)蒙古的冬天很冷,司機(jī)室常常會掛著一層霜,剛暖和點(diǎn),開窗一探頭,那點(diǎn)熱乎氣就全跑光了。再遇上個下雪刮大風(fēng),腦袋都快凍掉了。”
“遭點(diǎn)罪不要緊,最擔(dān)心的還是鐵道上突然蹦出個人來。”由于鐵路運(yùn)行區(qū)間沒有完全封閉的護(hù)網(wǎng),人們?yōu)榱朔奖愠T阼F道上穿行。李彥平說,蒸汽機(jī)車的時(shí)速大概在50—60公里/小時(shí),一般制動距離是在800米以內(nèi),等看清人再制動,那就晚了。讓李彥平欣慰的是,這么多年來,他沒出過一起事故。
路上有路上的難,下車有下車的怕。李彥平說,火車司機(jī)有三怕:一是找不著媳婦,二是家里有事,三是生病。李彥平跑包蘭線的時(shí)候,是三班倒。開10個小時(shí)到蘭州,休息10個小時(shí);然后接車開回包頭,休息16個小時(shí)后再出車。如此往復(fù),節(jié)假日也不休息,趕上高峰期,更是說走就走。“哪有時(shí)間談戀愛,再說每天一身煤灰誰稀罕你。”李彥平說,他們車間有五六百人,大多是男的,找對象就成了大問題。“還好我‘下手’早,妻子是鐵路醫(yī)院的護(hù)士,比較理解我的工作,但有時(shí)也會抱怨幾句。”
李彥平唯一沒被埋怨的事,就是女兒出生時(shí),他陪在了妻子身邊。“那次您倒休得可真巧啊。”記者和他開玩笑。李彥平卻苦笑著說:“結(jié)婚的時(shí)候,我沒舍得休婚假,一直攢著在孩子出生后休了18天,那是我最長的假期了。”
至于“第三怕”,李彥平不愿多說。常年的體力勞動和睡眠不足,內(nèi)分泌失調(diào)、關(guān)節(jié)炎、胃病已成了這些司機(jī)的通病。兩年前,一個和他一批的蒸汽機(jī)車司機(jī),下車睡了一覺,就再沒醒過來。“他還沒到50歲”,李彥平嘆息。
火車型號和時(shí)代聯(lián)系在一起
還在開蒸汽機(jī)車時(shí),李彥平就已逐漸感覺到“時(shí)代要變了”。隨著鐵路運(yùn)輸系統(tǒng)大規(guī)模更新?lián)Q代,包西機(jī)務(wù)段大批的蒸汽機(jī)車被內(nèi)燃機(jī)車取代,很多相關(guān)工作人員也被分流、調(diào)崗。2000年,李彥平成了一名內(nèi)燃機(jī)車司機(jī)。
工作條件好了,李彥平反而對蒸汽機(jī)車越發(fā)割舍不下了。“這十幾年,眼見著我們機(jī)務(wù)段原有的120多臺蒸汽機(jī)車,報(bào)廢的報(bào)廢、賣的賣,如今就剩下眼前這幾十臺了,看著這些我難過啊。”
蒸汽機(jī)車上,留下的都是記憶:帶個飯往鍋爐上放一會兒就能吃;渴了鏟一鍬炭,一壺水一會兒就開了……最讓李彥平懷念的,是蒸汽機(jī)車所記錄的歷史。“火車型號是和時(shí)代聯(lián)系在一起的。上世紀(jì)三四十年代,生產(chǎn)的蒸汽機(jī)車叫‘反帝型’;新中國成立后,我們又有了‘解放型’;50年代末和蘇聯(lián)關(guān)系惡化后,我們把仿蘇聯(lián)建的蒸汽機(jī)車又叫做‘反修型’;再后來,又有了‘勝利型’和‘前進(jìn)型’。每列火車都是歷史的一個縮影,現(xiàn)在留下的這幾十臺最起碼也能代表半部中國蒸汽機(jī)車的發(fā)展史。”
前幾年,包西機(jī)務(wù)段想建個“火車博物館”,可籌來的錢太少,剛搭了個棚子,就沒了。如今,廢棄的蒸汽機(jī)車大多窗玻璃破裂、銹跡斑斑。“放進(jìn)博物館之前得先把它們修好。”“都這樣了,還修得好嗎?”“當(dāng)然修得好,換上零件,刷了漆,照樣能用。最起碼可以讓年輕人知道這段歷史,知道還有人開過蒸汽機(jī)車。”
- 環(huán)球人物的其它文章
- 漫畫和段子
- 箴言
- 我的墨鏡爸爸
- 小鞋匠“挽救”大公司
- 只看笑臉丟王位
- 危急關(guān)頭的奢華婚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