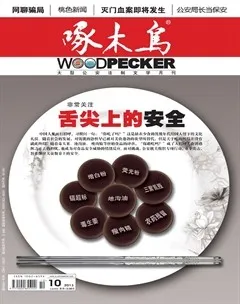逃犯

終于回到曾經度過童年和少年時光的故鄉。故鄉還是我離開時的模樣,破敗,枯萎,仿佛被時間拋棄,被世界遺忘,就像我姑滄桑的臉。我父母早逝,是我姑把我拉扯大的。村里人都夸我姑,說她為了照顧我,一輩子沒嫁人。我也一直這么認為,直到我姑下葬那天。
那天出席葬禮的,除了我三叔兩口子,就是村里的幾個老人,帶著不懂事的孫輩或重孫輩,年輕人都像我一樣,逃難似的跑到外面混生活去了,棄故鄉如敝履。葬禮簡單潦草,幾抔黃土,一座新墳,不久之后,就會被荒草淹沒,再也看不出痕跡。
其他人陸續離去,就剩下我和三叔三嬸在墳前默立。遠處開來一輛警車,下來一行三人,兩個穿著制服,一個戴著手銬。戴手銬的男人兩鬢斑白,他在兩個警察的押解下在我姑的墳前鞠了三個躬,又看了看三叔和三嬸,嘴唇動了動,卻沒說話。三叔早已熱淚盈眶,三嬸則靠在三叔的肩頭輕聲啜泣。
他們走了,給我留下了一連串疑問。我問三叔這是誰。三叔嘆息,他叫四平,原本該是你姑夫的……
那年我還沒出生。四平二十五六,和我姑有那么點兒意思,村里人都看出來了。之所以沒提婚嫁的事,是因為山里太窮了。窮到什么程度,隨便舉個例子。那時候山里頭不通電,山里人也沒什么時間概念,白天看日頭晚上看星星,除了村委會,只有村長家有臺老式座鐘,據說是村長老爸斗地主的時候分的。村里人但凡有點兒什么事需要知道準確的時間,經常到村長家瞻仰那臺大座鐘。因為窮,村里的姑娘都嫁到外面去了,村里的男人娶媳婦是個難事。好在四平是村里的小伙中數一數二的,干農活、打獵,都是一把好手,我爺爺奶奶也就默許了,就差媒人上門提親了。
只可惜看上四平的不止我姑,還有村長的老婆。村長的老婆比村長小十好幾歲,還不到三十,經常找各種借口把四平叫到家里,幫忙搬點兒東西啊,修個房頂啊,當然,那會兒村長肯定是不在家的。四平實誠,叫干嗎干嗎,大概他覺得鄉里鄉親,幫忙是應該的,再說,他也不敢不去,誰叫那是村長的老婆。村長老婆越來越無所顧忌,時間長了,風言風語終于傳到了四平耳朵里,他嚇壞了,再不敢去村長家。可村長老婆不干了。
村長老婆往四平家門縫里塞了張紙條,大意是,今晚收工后你來我家,如果你不來,我就告訴村長你非禮我。當晚,村長家傳來一聲槍響。鄰居聽到槍聲,跑到村長家一看,村長老婆腦袋破了一個大洞,已經斷氣,地上扔著一把獵槍。就在這時,村長家的大座鐘半點報時,響了一聲,于是鄰居記住了案發時間——六點半。鄰居趕緊去找村長,那時村長正從村委會出來往家走。事后,村民們認出了那支槍,是四平的,第二天警察趕到后——山路不好走,在四平家里找到了村長老婆留的那張紙條。但他們沒找到四平。四平逃了,從此再沒回來過。
四平成了通緝犯,一逃就是三十多年。我猜四平和老家一直有聯系,否則他不會知道我姑過世的消息。大概他也是逃累了,給縣公安局打電話要自首,但有一個條件,就是最后看我姑一眼。于是就有了葬禮上的那一幕。
我托刑警隊的朋友秋生拐彎抹角幫我打聽了一下,得知四平自首是自首了,但并沒認罪。他堅持說他沒殺人。那天,他看到紙條,擔心村長老婆真的鬧起來,不敢不去。傍晚,他從山上打獵回來,把槍靠墻放在村長家院子門口,然后進了屋。村長老婆聲淚俱下對他訴衷腸,他聽得頭暈腦脹,不敢答應,也不敢不答應,擔心村長回家撞見,匆匆跑了,獵槍卻忘了拿。警察問他記不記得當時是幾點,他說當時頭腦一片混亂,記不清了。
秋生說證據對四平很不利。不過,這案子里有個疑點,關系到村長本人。按說,既然村里有風言風語,村長不可能不知道。換句話說,村長也有嫌疑。當然,村長有不在現場的證明。從村委會到村長家,正常走路要十五分鐘,當時天黑,可能還要長一點兒。村里的會計、婦女主任、治保主任作證說,下午村長一直在和他們玩牌,大概六點半左右,天黑下來看不清牌了才離開。而槍響是在六點半之前,因此村長沒有作案時間。秋生說疑點就在這兒,只是因為四平的嫌疑太過明顯,所以這種可能當時被調查的民警忽略了。其實,村長也是有機會作案的。
那么,讀者朋友,如果是村長作的案,他是如何制造不在現場證明的呢?
(10月31日截止答案,參考答案見第11期,“十月偵探榜”見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