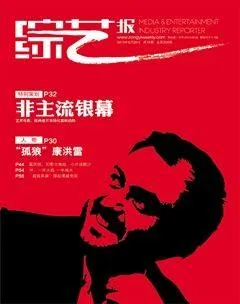《唐宮燕》飛上熒屏“鬼才”陳十三內地冒險
被冠以“鬼才”之稱的影視創作者,總是不按常理出牌,以一己想象力構建出奇妙王國,觀眾在一輪又一輪的驚詫中,刷新三觀。這類創作者,更容易被銘記,比如被譽為“鬼才編劇”的陳十三。即使亞視經典劇《我和僵尸有個約會》系列(以下簡稱“僵尸”系列)的最后一部已過去近十年,死忠粉們還在盼望著第四部,期盼再度進入“永恒國度”。
由陳十三擔任編劇的《唐宮燕》8月24日起在湖南衛視第一周播劇場播出。他和湖南衛視的周播劇場頗有緣分。之前參與的《軒轅劍之天之痕》(以下簡稱《軒轅劍》)去年7月播出時,是湖南衛視改版后推出的第一部周播劇。由游戲改編的《軒轅劍》與陳十三以往天馬行空的風格契合,但最后的成品并不那么“陳十三”。有種說法是,陳十三只參與了劇本大綱和前幾集的劇本創作,其余則由唐人的編劇完成。
從某種意義上說,新劇《唐宮燕》才是陳十三與內地影視公司合作的第一次亮相。《唐宮燕》主要講述武則天在位后期皇位之爭的故事,著力渲染后宮女子爭奪權力的煞費心機。這個題材聽上去不那么 “陳十三”。

陳十三Style
陳十三的代表作品有《我和春天有個約會》《我和僵尸有個約會》《倩女幽魂》等。他對于劇本的野心,從來不止于一個故事,而是創造一個世界。“僵尸”系列將傳統的“僵尸”形象與西方的“吸血鬼”形象組合,故事背景置于現代都市,改變了觀眾對香港僵尸電影中“頭上貼道符,只會蹦著走”的固有印象。他筆下的角色,無論正邪,都寄托著某種極致的情感。《我和春天有個約會》以四姐妹的情誼折射香港的時代變遷,小蝶和家豪的愛情唏噓了一代人;“僵尸”系列中“僵尸”愛上“女天師”的設定,把兩性的對立放大到極致,這種“天敵之愛”早于《暮光之城》出現,帶給觀眾耳目一新的感受。
粉絲最佩服陳十三的想象力,“明知道是瞎編,卻依然為之著迷。”對粉絲來說,偶像來到內地發展是一件喜憂參半的事,喜的是能看到更多作品,卻擔心以天馬行空見長的陳十三在內地施展不開拳腳。陳十三也有同樣的擔心,“說沒有影響是假的”,但他的態度依然樂觀,“正如所有比賽有規則一樣,只要認清規則是什么,依照規則公平進行,就可以盡情參與和享受比賽。”《軒轅劍》中,“月河城夢境”一段依然是典型的陳十三風格:長相丑陋的平凡女子如煙為了得到愛情,用生命和妖怪做交易,把心愛的人困在自己制造的夢境中,后被愛情打動,犧牲自己,成全愛人。
對陳十三來說,眼前的形勢很樂觀,與之合作的內地公司都給予他廣闊的創作空間,只要題材能通過審批,有合適的商業元素,劇本任他自由發揮。不少合作伙伴更是期待他能寫出內地市場沒有的題材,開創新的戲劇路線。
冒險即快感
2004年結束《我和僵尸有個約會Ⅲ》后,陳十三停止電視劇創作,名字偶爾出現在電影的主創名單上,直到2010年,以《軒轅劍》為契機,重新回歸電視劇創作。
其實自2000年開始,他已很少編寫電視劇本,大部分時間放在制作、行政及創作策劃的工作上。2005—2010年,陳十三與多位香港電影導演合作了高清電影系列,擔任電影的創作總監,大部分作品成為香港電影節參展作品。
早在1998年左右,創作《少年英雄方世玉》時,陳十三已與內地影視圈接觸。那是另一部讓80后記憶深刻的電視劇,也開啟了張衛健在內地觀眾心中的無厘頭形象。
陳十三說自己勉強算是第一批來到內地工作的香港編劇,見證了十多年來內地影視行業的起飛過程。從上世紀末開始,他一直以不同身份參與內地影視業,優秀的影視人才不斷涌現,讓他感覺興奮,同時又憂心于題材的多元性不足。“一套劇集火了,便有十多套同樣題材的劇集在趕拍。同一礦坑若開采過度,會帶來很多后遺癥。”但他也承認,這是影視發展的必經之路,中外都一樣。
新作《唐宮燕》從題材上看,與內地近幾年大熱的宮斗劇重疊。宮廷戲是陳十三之前不曾涉獵過的題材,此番冒險是因為唐朝是他最喜愛的朝代,而武則天這個人物更是讓他著迷。 “冒險本身就是一種快感。況且翻開神武晚期直至韋后亂幃這段歷史,頁頁精彩,絕對是劇本創作的寶庫。”在宮廷戲這個已經泛濫的題材中,陳十三找出了自己喜歡的創作角度。《唐宮燕》的新穎之處在于,選擇武則天臨終前發生的事件為創作藍本,這部劇中的女人,爭奪的不再是男人,而是權力。
《唐宮燕》是陳十三與“僵尸”系列中“王珍珍”扮演者楊恭如多年后的再度合作。除這位前亞視一姐外,飾演李旦的駱達華也是前亞視藝員,加上陳十三的亞視背景,亞視的昔日輝煌在內地宮廷劇中小規模復興。
七百萬到十三億
兩年多前,陳十三在香港設立了創作工作室,團隊包括香港的資深編劇及內地新生代編劇,主要為內地媒體公司提供影視劇本和項目策劃。其中,也跟某些公司如拉風傳媒簽訂了長期的合作協議,與拉風傳媒的合作是亞洲電視前制作副總監楊紹鴻撮合的。陳十三選擇合作對象的標準是具備創造力、能欣賞接受他的思維、用心用力把作品做好的公司。
在內地的編劇工作仍然沿用香港集體創作模式,但陳十三堅持把守第一關到最后一關。對他來說,戲劇作品必須有個人風格。他參與劇本的全部創作過程,需要修改及重寫的,親自動筆的習慣也沒有改變。不僅工作方式不變,生活狀態也沒多大改變,陳十三依然是盡力寫喜歡的劇本,過簡簡單單的生活,“惟一的不同是現在可以多花一點時間培育年輕編劇。”
因為工作室設在香港,陳十三的生活重心還在香港。借助發達的通訊技術,很多事務通過網絡溝通。他一年只需要到內地幾次,把工作的大方向落實好,在開拍前參與籌備過程,便可以安心在香港工作。這也導致他的普通話進步緩慢,“我的普通話蠻爛的,真是辛苦內地的朋友了。”跟導演工作相比,環境的變更對編劇的挑戰更大,需要克服文化和語言的障礙,寫出契合相應市場的對白。雖然說不好普通話,但聘用的內地編劇可輔助陳十三解決很多對白上的問題。
“從七百多萬人口的香港轉戰十三億人口的內地,有著挑戰巨人的感覺”,陳十三著迷于這種感覺。而內地公司資源充沛、拼勁十足、尊重創作者,亦讓他工作得如魚得水。未來數年內,他還是會專注在內地發展,讓更多觀眾在他建構的戲劇世界中同喜同泣,“希望編寫出一部挑戰觀眾想象力卻又能被廣泛接受的作品。”目前其完成創作的兩部都是古裝劇,時代劇是下一個挑戰目標,“題材已想好了,希望會在2014年達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