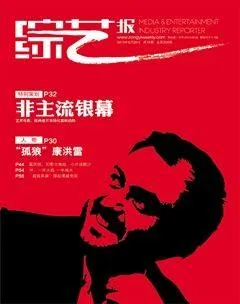“第六代”的商業征途
《綜藝》:你在轉型商業片的頭兩年連續拍了3部電影,但之后為什么一度停下了?
王光利:一開始做商業片時是做本土喜劇,但我一直想做警匪,可是運作中遇到了很多障礙,好幾個項目夭折了。之前也花了好幾年的時間反思,當時覺得好像是碰到了一面墻。《制服》是我嘗試破局的第一步。
《綜藝》:據說《制服》最初是王晶的點子?
王光利:之前我和王晶一起在香港做過《臥虎》,合作得很愉快。2009年我們想籌備續集,但劇本在內地遇到了些問題。后來在別人的啟發下,希望能把香港拍警匪片的一些經驗帶到內地來,所以就做了這個。最初我們是想拍個小成本影片,像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的意大利警匪片那樣比較講究故事而不是場面的風格。但劇本出來后,王晶覺得做個小片有點可惜,最后增加了預算和明星。
《綜藝》:你接下來的新片也是警匪吧,為什么這么看好這個類型?
王光利:在全球范圍內,警匪都是電影一個很重要的種類,市場空間很大。此外,警匪片往往以極端的方式來表現人性,我覺得這對中國的當下特別有價值。中國當前正處于社會轉型期,一方面經濟發展很快,但很多長期積累的問題也開始浮現,無論是自然環境、食品污染還是教育、醫療等。我覺得這些根本上都是道德和精神層面的問題,這也是我在《制服》里想表達的。片中那些扭曲的犯罪不僅是商業性的包裝,里面也有我的思考——罪行越是扭曲,越是有道德的意味蘊含其中。
《綜藝》:香港電影對這個類型一直都很擅長,內地做警匪片的優勢何在?
王光利:與香港的警匪片相比,我們的優勢很明顯。我們對自己身邊的事情更了解,現在社會上各種各樣的相關事件和報道也很多,這些都是現實中的素材。當然在內地,警匪這塊一直沒做起來。一些大導演其實之前也籌備過類似的項目,但最后都沒拍出來。年輕的導演則缺少經驗,對規則的空間和彈性都不了解,做這個也難。其實做之前我也猶豫過,想過要不要先做個容易點的,但最終還是覺得值得冒險。
《綜藝》:《制服》的成片相比最初設計,完成度如何?
王光利:應該說想做的基本都完成了,當然細節上還是有些修改。其實好萊塢也一樣,為了獲得更大的觀眾群,內容方面就得有所節制。至于在電影中嘗試一些較為邊緣的東西,我覺得現在是個時機。市場的空間越來越大也越來越多元化,本地電影的類型也越來越豐富。
《綜藝》:賈樟柯新推出的《天注定》,也是講復仇的。
王光利:是,雖然他的是藝術片,我的是商業片。這當然是巧合,但深層次里可能還是因為我們對中國現實的共同關注,盡管選的道路不一樣。我和賈樟柯一直是好朋友,我的第一部商業片他還客串過。
《綜藝》:你也是拍藝術片出身,為什么后來轉做商業片?
王光利:商業片的格局和空間更大些,我很希望能在自己的國家獲得更多觀眾。當然對于賈樟柯、王小帥、婁燁他們的選擇和堅持,我非常尊重也很欽佩。但電影總需要各種類型,他們是更自我的“私房菜”,我做的則是面向更多客戶的“火鍋”。我覺得電影產業的發展,這兩塊必不可少。將來隨著中國電影的發展和成熟,這兩塊也會互相滲透和交叉,電影也能更兼具觀賞性和藝術性,就像姜文已經做到的那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