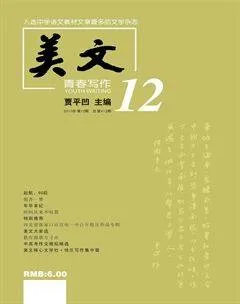道道道
尼采說哲學已死,我想這是真的。
前些日子去北大哲學夏令營,聽了三天的凡人之爭,看了三天別人的眼睛。
我不知從什么時候起開始喜歡看別人的眼睛,無論是陌生人的還是熟人的。通常,我愛引一個有趣的話題,然后默默地聽他或她講。同時,我開始享受地看他或他的眼睛。人的眼睛真的好奇怪,它與人的年齡不總是同步的。孩子可以有渾濁的眼睛,少年的眼睛最冷漠,而老人的眼睛也可以像嬰兒一樣充滿好奇。如果我沒有記錯,在《圣經·雅歌》里良人漂亮的眼睛被比做鴿子眼。我仔細看過好多人的眼睛,像鴿子眼的雙眸很少見,除了嬰孩外,我只發現兩個人有這么好看的眼睛。只是我不敢正視那雙活靈活現的鴿子眼,我怕它的主人會生氣。這里有一個有趣的悖論,通常長著尋常眼睛的人在侃侃而談,尤其是面對一個少說多聽的好聽眾(如我)時,總不會注意到我在認真瞧他或她的眼睛。相反,若我偷偷瞥那鴿子眼,便可以感到我的目光順著這雙眼睛悄悄地滑著跌進這眼睛主人的心里。我不忍心我的目光像磨鈍后長滿毛刺的竹器把他或她的心揪地一挑,所以我總不愿瞧他或她的眼睛。雖然那眼睛真的很美。
還好,哲學夏令營沒有給我機會讓我再面對這種想看卻不能看的矛盾。的確,那些為往圣繼絕學的哲學夏令營營員們都是國之棟梁。他們不僅熟悉哲學史,熟悉哲學原典,而且博聞強識。我見到帶圓形鏡片滿口之乎者也四書五經的北大附中學生,我見到那么遠又那么近的黃岡中學學生。當然,我還是習慣性地沉默,安靜地聽教授在希臘文德文古文里跳躍,安靜地看同齡人爭論得面紅耳赤。我心里默默笑著,想起一位教授驚異地問:不知是因為哲學,還是因為北大,這屆夏令營竟有這么多人。其實我知道那個選擇問句錯了,真正引來這么多人的是優秀學員自主招生免初試的蜜糖。為了成為優秀學員,自然要“秀”。于是,我看到好問的優“秀”同學們拖住了教授,被大學生們冷落許久的教授被這股來自優“秀”中學生的熱情感染竟錯過了午飯時間。于是,我看到善思的優“秀”同學們在主題不限的班會課上竟主題異常鮮明地討論了一晚上“自殺”這種終極話題。
若是以前的我,行文至此,定會如決堤洪水,透著尖酸刻薄一路寫下去。但正如沈從文曾寫道“難道不知道諷刺同魯迅一道死去了嗎?”我們通常喜愛犀利的文章,不羈的筆調,而且寫這樣的文章(或者叫做雜文)最為簡單,只需將一腔憤怒一股酸勁用筆記下,這樣便是直插敵人心臟的匕首了。可是,細細想想,卻終是可嘆了。姑且將中國人數定為十三億,如果我總是站在十三億減一的立場上說話,自然瀟灑痛快。可是事實上,我不過是十三億分之一罷了。我在那夏令營中,便是其中的一份,優與劣我皆占著。
我說夏令營里沒有很美的鴿子眼,可是我對鏡自視,同樣沒有看到十分漂亮的眼睛。相反的,這眼睛布滿血絲與不屑,還有透著嫉妒的滑稽可笑。十幾年未曾撣過灰的眼睛看到的世界總是霧蒙蒙、臟兮兮的。我突然想起食指的詩句“她有洗去歷史灰塵的睫毛”,心肌陡然收縮,差些涌出些無用的淚來。這未涌出的淚讓我記起夏令營里一位高個子的大男孩,之所以這么稱呼,是因為他的眼睛。我現在可以再看到當教授與我們討論時,所有人包括我都在“秀”自己的“優”,我們極力地口吐蓮花,句句用典。當時,柏拉圖與亞里士多德時常從我們嘴里滑落,尼采的強力意志,康德的觀念論,叔本華關于欲望經驗的理論悉數登場。可以說作為哲學的哲學史正在我們頭腦中滾動。那個大個子男孩眼圈發紅,抱著胳膊,蜷伏在桌上一言未發。我記得他自我介紹時說他對哲學家并不了解,只是喜歡自己想想世界。我記得他后來發言說他很失望。很奇怪,我覺得我的心能聽懂他的話,可是在優秀學生極力“秀”優時,我攥著奧勒留和《煉金術師》賣弄學問,扮演著令他討厭的角色。我總在想我何以為了一個“優秀學員”的稱號做令我的心落淚的事。后來我想明白了,其實每一個來此的同學都背著學校與家庭的包袱,耳畔總能想起那句“好好表現”的叮囑。其實,我們何時不都背著這樣的包袱?我們總是整體分之一,我們做不到與所生活的環境脫節。
在夏令營同學發言里,我又聽到了那句“這是一個浮躁的社會”的話。這是我聽到過的最浮躁的話了。正所謂“欲潔何曾潔”,我們其實都不干凈,做潔癖想清高還不如拋開這句話,在風雨中奔跑,在泥潭里打滾,至少是“維摩詰”。我想只要為心留一寸安寧的干凈地方就實屬不易了。
我記得《色情男女》里的一句話:“我以前做人很可笑。”其實我以前做人也很可笑,可笑到讓現在的我啞然失笑。我以前總以為公道自在我心,刻薄自傲,現在才明白:道可道非常道,天道地道人道劍道,一道二道三道四道,東道南道西道北道,左道右道前路后路,都是胡說八道。
好有意思,我說我去哲學夏令營這事,竟扯出這么多無關的話,可是這些都關乎哲學。然而可嘆的是,任何人都可以說哲學已死,卻不能像尼采那樣在判語下定后開創自己的哲學,這就是鳳凰涅槃與飛蛾撲火的區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