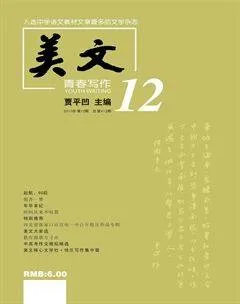在荷蘭吃了一個風車

何杰,南開大學漢語言文化學院教授。世界漢語教學學會、中國語言學會會員。1996年至1998年赴拉脫維亞大學講學、任教。同年于波羅的海語言中心講學。1999年應邀赴德國漢諾威參加世界漢語教學研討。2008年參加第九屆國際漢語教學研討會。2009年論文入選美國布萊恩大學語言學會議。2010年應哥倫比亞大學邀請赴美交流學術。
長期從事對外漢語教學及語言學研究。出版語言學專著《現代漢語量詞研究(增編版)》等三部;出版教材、詞典多部。發表及入選國內外頂級學術會議論文三十余篇。
1972年開始發表小說。1982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論文和文學作品均有獲獎。出版散文集《藍眼睛黑眼睛——我和我的洋弟子們》。
入選《世界優秀專家人才名典》《中國語言學人名大辭典》《中國專家人名詞典》等。
1998年獲評天津市級優秀教師。2006年榮獲全國十佳知識女性。
小“皮肚”和風車哥哥
我小時就愛看書。那時的童話書好像也不少。我特別喜歡看一本叫《皮杜和風車哥哥》的童話。“皮肚”(皮杜)名字好記,風車形象鮮明。
風車哥哥給我的印象更是深刻。他是那么英武,俠義。“皮肚”是個小可憐。當風魔鬼要來抓他時,風車哥哥把“皮肚”藏在了他的大風葉后。然后掛上戰甲,轉動起他的風葉胳臂英勇奮戰,趕走了風魔鬼,救下了小“皮肚”。至今記得,小“皮肚”站在風車哥哥巨大的風葉胳臂上,和云朵小姑娘一起玩耍的圖畫樣子。小“皮肚”是個牛皮大王,膽小,卻敢吹大牛。他見到小云朵就吹開了牛:
小云朵問:“昨天,怎么刮起了那么大的風?”
“皮肚”說:“嗨,那是我生氣了,出了口粗氣。”
正在逃跑的風魔鬼一聽,忍不住笑了。誰知一笑,笑出個屁。一下把吹牛的“皮肚”吹下了風車,吹到了沼澤地里。“皮肚”大喊救命,灌了一肚子水。風車哥哥趕緊伸出風葉長胳臂把牛皮大王撈上來。小“皮肚”一邊吐著水,一邊繼續吹牛:
“哈,大哥,要不是你把我撈上來,我就把那里的水都喝干了。”
風車哥哥笑了,說:“那好吧,我再把你放回去。”
小“皮肚”忙說:“不去!不去!那么點水,不夠我喝。”
從那,不知怎么地,小“皮肚”再也不吹牛了。風車哥哥是那么高興,托著小“皮肚”和小云朵一塊玩耍。
說真話,我記得最清楚的是:那時,我那么想也到風車的長胳臂上去,在藍天和小“皮肚”和小云朵一塊玩。
兒時,風車就把去看看它的渴望吹進我的心里。現在,我終于站在了風車的故鄉,像走進了童話……
風車的童話
我看到了風車。真切、生動。
在荷蘭,無論從哪個角度觀賞荷蘭的風景,你一定能看到地平線上豎起的風車。風車在那寬廣地平線上,和天上漂泊的云朵,地上的湖泊都帶給人無數的夢幻和想象。
一望無際的綠野上,一座座古老的風車高高站立。他們像一個家族的兄弟姐妹廝守著,彼此愛惜地相視。色澤鮮艷的風車葉,像伸長了的胳臂地轉動著,只是發出的語音永遠是不改變的“吱呀!吱呀!”是啊,他們有傾訴不盡的勞苦。風車下,溪流卻沒有時間聽風車的絮叨,竟是跳起來,頂著水花,閃著亮光忙著去磨坊赴約。他們得打工呦。
曲折的小道鋪著蜿蜒的彩帶。溪水潺潺,涓涓流淌,把晶瑩安裝在大地上。小橋扭來扭去,你拉著我拉著你,在綠野上架著通道。小木屋靜靜地藏在綠蔭里。陽光慷慨地把眼前的一切都鍍上了金色的亮光。
一片詩意。詩意藏著人們的勞績和歡樂。
不是像童話,而是就在美麗的童話中。風車葉上好像還站著小“皮肚”和小云朵。
兒時傻傻的童話像一壇陳年的老酒,歷久彌香……
我情不自禁地贊美:“多好的居住環境。真羨慕呀,純凈的田園風光。”
我的旅友有個德國同行,我叫他老德。老德撇著嘴說:
“嗬,別總是‘鼴鼠出門——見什么都稀罕。”老朋友老德總開玩笑,說我是出洞的鼴鼠。沒辦法。
“荷蘭風車最早是從我們德國引進的。可惜德國在大工業發展時期,移情別戀,愛上了蒸汽機,忘了他的老情人。結果鬧得萊茵河都污染了,荷蘭卻躲過了一劫。”
我說:“人家荷蘭把風車發展到了極致。”
“他們有條件。”每當我贊美荷蘭,老德一律不屑。
是啊,上帝總是公允的。上帝沒給他們土地,卻給了他們造大地的風。荷蘭正處在從北海長驅直入的大西洋季風帶里。
我說:“不管怎么樣,人家風車的使用真是太巧妙了。一舉多得。”
風車的功勛
荷蘭風車最早只是用來磨面粉,碾谷物,后來磨香料,榨油……人們不但建起了風車的磨坊,還建起了鋸木廠和造紙廠。后來我到美國,知道美國獨立宣言的羊皮紙就是荷蘭用風車做動力制造的。
風車是上帝給荷蘭人的補償。聽說,在歷史上,全荷蘭的風車有一萬二千多架,現在還保存了一千多架。 在埃爾斯豪特村,我看到了這個世界最大的風車群。每一個風車都用悠然的姿態,鑲在藍天之上,和那白白的云朵組成一幅優雅、古樸的畫面。
真的就在童話里。
我還走進一個很大的風車塔樓,有幾層樓高。風翼長達20米。進塔房就像進古堡一樣,中間是木梯,分幾層。有睡覺、吃飯的地方。生活用具一應齊全。布置溫馨、簡樸。有的家族在風車塔房里已生活了二百多年。更吸引人是那些穿著17世紀衣服的大人孩子。他們在風車下展示著他們祖輩淳樸的民風:
農婦頭上戴著紅三角巾,穿著帶條的大裙子,腳上穿著大木鞋。帶腿的南瓜一樣,做著永遠飄香的奶酪。(在國外見了奶酪就想吐,回國卻特別想吃奶酪。可惜沒有叫我想吐的味了也不香了。)我最看不夠的是一個表演的孩子。他穿著短坎肩,學著大漢的樣子晃著膀子,眼卻盯著一個游人手上的蛋塔,眼珠都不轉了。我想他和他的祖輩一樣,都得為生計辛苦。令人欣慰的是,時至今日,荷蘭人祖輩的家業,又以另一種形式養育著他們的子孫。
看來想啃老,怎么啃的都有。
荷蘭的“老”是苦命的。上帝把他們放在北海邊,又放在沼澤地里。而聰明的荷蘭“老”們卻用風車排水造地,變滄海為桑田。免于他們大部的土地沉淪于水下。在荷蘭的經濟發展中,風車功不可沒。至今風車煥發著人們沒有意想到的優勢。現代化的風力電站,已出現在地平線上。風車創造著最清潔的動力傳奇。我真希望我的國人來看看受些啟發。
荷蘭人感念風車給他們的恩惠,他們每年5月的一天(第二個星期六)為“風車日”。
這一天,全國都懸掛國旗、鮮花彩燈。裝飾一新的風車一塊轉動,舉國歡慶。為了叫人永遠記住風車飛轉的歲月。
我記得我的一個荷蘭學生就寫過一篇作文《風車日——我最難忘的一天》:
“……
那天大家都要吃一種黑燕麥做的面包。面包是用從風車磨房拿回來的新鮮面粉做的。
那種面粉發的面包特別大。
我的屁股那天也發得特別大——叫我爸差點打成了面包。因為那天,大家高興,我也高興。
那時,我還沒上學。我最愿意玩的游戲就是到處跑,最想去的地方就是風車葉上。心想坐在那上面一定最美啦。在那,也一定能抓一塊云彩。
那天,大人們做吃做喝,忙成一個疙瘩時,我就決心到風車葉上一游。只可惜,要不是多管閑事的鄰居大媽多嘴,我就真的撕下一塊云彩了。大人們卻說,要不是大人們發現早,要不是停了風車,把我抱下來,我就沒胳臂,沒腿了。不過那天,不管媽媽怎么護著我,爸爸還是給我來了一次‘發面包’。爸爸打完我的屁股還說:
‘哼,這次給你個兩半的面包,下次就叫你看不出縫來!’
在歐洲流傳著一句話:‘上帝創造了人類,荷蘭的風車創造了陸地。’
我說:‘我爸爸創造了肉的發面包。風車日真難忘。’因為至今,我一坐下,就能記起屁股真像面包一樣,發起來是什么滋味……”
想起學生寫的這段趣事我還想笑。沒想到,現在我也站到了風車下。那天,看著這特別漂亮、特別神氣的風車,心癢癢地又生出了兒時的夢。真的,心想,要是真能上去,屁股被打得沒了縫也值得了。只可惜,風車“呼呼”轉動著,只叫你站在安全線外看。
遺憾,我沒趕上風車日。那天看得更認真,竟然發現有的風車掛著小紅旗,有的不掛。一問才知道 ,哪家有喜事,哪家就掛小紅旗。而且還知道了,那么大的風車竟是一個家族的。
沒出國時,去看敦煌,過了蘭州,一路大漠,看見許多風車。國內的風車苗條。高高的身材,清秀的風葉點綴在一馬平川的沙漠上,生動,充滿了生氣。只可惜太少了。真想我們國內也像荷蘭,到處能看到風車,而不是油田井架。
在荷蘭就想買一個風車帶回去!特別想給我的家鄉帶回一個風車。
帶回一個風車真不易
為了買風車(當然是藝術品啦。買不起大的,買小的。)我決心逛商場。嚯,一去,我們這些“老外”都有點劉姥姥進大觀園了。
荷蘭人鬼點子真多。
有創意的商業點子,可以叫顧客赴湯蹈火。沒想到,我也獲得了一次這樣的恩賜。
那是去一個展覽館。展覽廳不大,出了展廳同一樓層便是商場。本來是看展覽,卻又可以逛商場。那商場正在展銷,不需要再買門票!
玻璃窗內,色彩斑斕,各種商品好像都在搔首弄姿地以各種姿態召喚著你:“快來看呀!”
可惜還沒等我去看,只聽“咚”的一聲,和我同來的小Q ,本來走在我前面2米,此時,只見他“噔噔噔”一個大屁股墩又礅回了2米。我和老愛什么也顧不得看了,忙看他的頭。
小Q喊著:“腦袋沒事,眼鏡!”
我們忙把眼鏡給他找來。是啊,在國外換個眼鏡得多少錢呀。幸好眼鏡沒壞。不過,小Q起來更像小Q了。
小Q是中國留學生,小個,站直了也像團團著。(小Q,我給他的雅號)小Q團著身子一會兒摸腦袋,一會兒摸眼鏡,大罵了一通。我們就下樓了。
世界上有人的記性“好”到居然下一層樓,就什么都忘了。
下樓,一扭頭,呀!又是商品大廳,里面又是琳瑯滿目,又是各種商品好像都在召喚著你:“快來看呀!快來買呀!”更不可抗拒的是,一個醒目的大牌子,我敢說,誰看了,都走不動了。
“4荷蘭盾,你拿走!”
才合1美元呀!什么呀?這么便宜?
我快步上前。接著就是和小Q一樣,“咚”的一聲,這回“噔噔噔”礅回2米的不是小Q,而是我。我暈乎了好一陣子,之后,我們又大罵了一通:你說,這商家光知道招攬生意,卻不想想把門開好。有把門開在兩邊的嗎?中間卻是通頂立地的大玻璃窗!
后來我們才知道,從歷史上,荷蘭人造房子就是小門大窗子。那因為他們憑著門的大小納稅。人們為了少掏錢,寧肯從窗戶吊物品進屋也不把門開大。難怪荷蘭人的房子頂上,都有伸出的一個鐵鉤。
錢,這玩意真怪。現在不這樣納稅了,但人們的思維還是慣性的。其實,想想,何止是慣性?人家會做買賣。
展室和商場連著,那大窗子里的東西真吸引人啊!商品都只有一件,而且你買完,老板立即喊:
“這個樣子的,沒有啦!”
多勾心啊!荷蘭人真會招攬顧客!
在荷蘭,你只要走進商店,就不可能不買東西。特別是工藝品商店充滿了幽默感。那里全然就是一個小型藝術展覽館。光小船、木鞋就不下幾十種。
展示水國荷蘭特色的木屐精致多彩,多種多樣:有園藝型、新婚型、滑雪馬靴型……特別新婚型的木屐精雕細琢。據說,荷蘭婚禮上,新郎新娘父母各給新人送一只木鞋。兩只鞋上分別刻上新郎新娘的名字。婚禮過后,這雙木鞋便要永遠珍藏在他們的臥房。象征走到一起,一生相伴。了解這一風俗,許多情侶都買。遺憾,老板不會刻漢字,否則我和老愛也一定買一雙。
我的一個老外朋友卻非要買一雙,而且還一定要小鞋:
“我買小的,我愿意穿小鞋。我愿意穿小鞋。”
等我告訴了他們漢語“穿小鞋”的比喻義,老外說:“買了也不穿。”大家一通“哈哈”。
不同民族,語言的比喻義不同。這種文化誤解也就成了我們的笑料。那天我們真是笑料不斷。
在荷蘭,我還認識了一個大概是尼泊爾人(我最愛交朋友了)。他說他可不買木鞋。他們古時候,有一種叫“木站鞋”。人穿上就站在那不動了。我忙搶著說,那我買一雙。穿上也好歇歇腳。出來,整天跑,累死了。誰知,我的老外朋友們一塊大笑起來。
原來那種鞋是一種刑罰。在一塊板挖兩個洞,叫受罰的人站到木板里,兩只腳不能動。那是用來懲罰傳老婆舌頭和偷情的人。
你說,我還要買一雙?真倒霉。聽說我們西藏,過去也有。
我們又一通“哈哈”。跨文化交際,因文化背景不同總有歧義,歧解。
木鞋不買了,買小船吧。
小船造型也頗富想象力,有的是搖籃,掰開的花生殼、仰面朝天的小熊肚皮。無論什么都可見人家思路活躍。有個煙碟干脆是個小孩蹶起了屁股,妙趣橫生。連他們的國鳥琵鷺(嘴像琵琶的白鳥)也都人格化了:抻脖瞪眼表示驚訝的、跳倫巴舞的、下跪求婚的、穿著大木鞋的……最嚴肅的人看了也不能不笑。
我終于看到我最想買的風車。
小風車更是構思獨到,好像是用樹葉、草棍兒編扎起來。古樸、逼真。這些小風車、小船、木鞋、國鳥的成本寥寥可數,成品價格卻叫你瞠目。然而凡是來這里的人都買。說實在的,需要買的真多。人家國家特點鮮明:只是國花:郁金香不好帶; 國鳥:琵鷺不能帶;鉆石(國石)帶不起,也怕丟。 只有木鞋、小帆船、小風車好帶,都昭示著這水上之國的特色。
我咬了咬牙買了一個風車。想帶回國,擺在客廳,昭示:到荷蘭一游!
走走,覺得不對勁,細看,呀!風車是巧克力!同行旅友皆大歡喜。我們大家高高興興地把風車分吃了。一個小風車40荷蘭盾,等于10美金(那時匯率1比8多),相當80多元人民幣啊!
藝術無價呀!
真沒想到,就這樣了卻了我兒時的風車夢。 長見識,高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