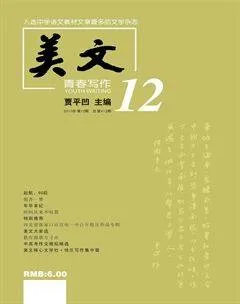因時制宜似嘉猷 明日黃花已空談

張大文:1991年被評為全國模范教師并被授予國家級“人民教師”獎章。1992年被評為上海市特級教師。現為復旦大學附中特級教師,華東師范大學、華中師范大學兼職教授。已發表文學作品1000萬字左右。
中國歷史上最后一次殿試,于1904年(清光緒三十年)5月21日在保和殿舉行。光緒皇帝制策以察吏、治軍、理財、勵士四個方面為問。劉春霖認為,無論是任官治兵之要,還是裕財正俗之方,都要以因時制宜為立論的大前提而分別論述之。于是,他指出:在澄清吏治方面,必須從重視守令開始,一方面長官勤求民隱,則屬吏清慎自持,另一方面加意培訓,擴其見聞,使守令委之以任而不惑,責之以事而不迷,使上下之情相通,萬政之興可待;在擴軍備戰方面,既用生動的比喻反論證國家之有軍隊猶如血肉既具之人身必有氣力以貫注,才足以發揮其精神,以生存于萬類競爭之世,又在批駁不以兵制為急務者的基礎上,強調天下之事日趨于變時,務必變換戰術,改進裝備,才能并立于群雄之間;至于理財方面,明確指出在利源外溢之今日,節流不如開源之尤要,而開源之道,在振興實業——講求農事,繁榮工藝,擴充商務,使野無曠土,市無游民,精華日呈,利權可挽;最后在勵士正俗方面,由于“今日浮蕩之士未窺西學,已先有毀裂名教之心,故欲正人心、端士習,必以明倫為先。欲明倫理,必以尊經為首。此即國粹保存之義”,所以力主以六經為治國之大道,以正視聽。

在因時制宜的前提下,上述四點分論,最后被概括為“皆保世之閎規,救時之要務”。加上皇上勤學修身,那么“我國家億萬年”得道之首要條件便以此為根基了。
——顯然,這樣一份殿試答卷,就文字論文字,有的言之成理,付諸實踐,必有成效;有的雖然提不出具體的步驟、方法,只能抽象地泛泛而談,但是方向對頭,自圓其說;有的能超越策問局限,提出創見,并輔之以切實可行的措施;有的雖然脫離社會實際,但是觀點明確,代表一方之言。
然而,這篇文章由于脫離中日甲午戰爭與馬關條約以來的國際形勢與國內實際,所以對作為立論的大前提的“因時制宜”的“時”缺乏深刻的認識,因而給“制宜”帶來先天的嚴重不足。這種不足,對于劉春霖這樣一介書生,有的是不能要求過高、橫加責問的。例如,在治軍方面,我們不能要求他總攬全局,高瞻遠矚,提出什么戰略方針,他能夠一反“乃世之論者,動是古而非今,輒謂人民歲輸數千萬之資財,以養此坐食驕惰之兵,固不如古者寓兵于農之善”的謬論,主張“皇上整軍經武,士卒以知學為先”,“然后可并立于群雄之間,所謂氣力充而精神煥矣”,就已經很不錯了。
然而,在論述到勵士正俗一節時,劉春霖卻跟時潮大唱反調了。經歷甲午慘敗、庚子巨變,世紀之交的新學啟蒙運動發端于救亡圖存之時勢,存在于朝廷興學育才之決心,發展到匯流成河,沖擊著舊社會、舊制度的堤壩。《新民叢報》1902年一則《召見翰林》的報道中,記敘了光緒皇帝、慈禧太后勉勵諸翰林當讀中西有用之書,中西之學,必求其通的情景,太后甚至教導眾人“今后切不可泥古不化,總以通達時變為第一要義”。這樣,一個嶄新、崇西的時代便形成了。據梁啟超《西學書目表》所記,1896年市面上可讀之西學書籍,總共不過三百余種,而據顧光燮《譯書經眼錄》所記,1904年翻譯出版的西學書籍已有五百三十三余種。可以說,新學、西學以啟蒙為旗幟,標志了一個時代的特色。但是,劉春霖卻認為“今日浮蕩之士未窺西學,已先有毀裂名教之心”,于是提出欲正人心,必以明倫為先,必以尊經為首。顯然已站在文化保守主義的立場上了。
所以,這樣一篇文章,看似因時制宜地獻上嘉猷,實際上是明日黃花地變成一紙空文。憑借它而考取狀元,從一個側面說明科舉制度已是強弩之末,不能不走出歷史舞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