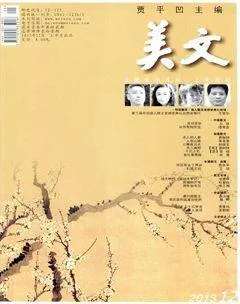用生命書寫

李三槐
1941年3月生于陜西省周至縣。1964年從西北政法大學哲學系畢業。國學學者,中國思想史、中國新聞史學者。先后任陜西省社會科學院科研處處長、《人文雜志》總編等職。
為摯友榮慶校閱《從新聞黑洞跳進又跳出》這部248萬多字的四卷本著作,感觸奔涌。歸結起來,這部書是他用自我生命書寫出來的華彩結晶。
我甘心情愿為他的書當“助產士”
我從任《人文雜志》編輯的20世紀70年代起,就編發過榮慶的文稿——《秦馬小史》《秦國四貴及其覆亡》《張載卒年卒因考》《酈道元遇難地陰盤小考》《王老九的詩歌風格及其流派》《王陸一和他的〈戰區巡察報告撮陳〉》等。知道他在民間文學、民俗學、地方志與國共兩黨史料的征集上用力甚勤。當時曾有中共陜西省委書記、陜西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主任陳元方先生想調他到省上做方志研究;新聞學家、陜西省社會科學院院長何微先生想調他到省社科院做黨史研究;教育家、陜西省教育廳副廳長權劍琴與左嘉猷兩先生想調他到省廳做教育學研究等動議。最終,榮慶進了《中國新聞社》,走上了對外新聞記者崗位,但始終沒有減弱對文學、史學、民俗學研究的興趣。70年代初,他就對我披露心跡:“想寫一部揭示民族秘史的長篇小說《繡嶺》。”我幾次三番勸他:“你從事學術研究可能取得的成就會更大。”
榮慶此生曾兩度遭受了常人不易挺直腰桿生存的艱難困苦:一次因抵制“窮過渡”,受頂頭上司打擊報復;一次在作記者后因寫“內參”揭露某些地方官員的不正之風,受內外上下糾結打壓。逆境之中,他還有文學夢、學術夢么?
2008年,68歲的他與旅澳學者劉婷博士合著的開啟性邊緣學科專著《新聞民俗學》(兩卷本、83萬字、中國文聯出版社出版)殺青后,我受其囑托,做了該書的編審與校閱工作。
讀著書稿,我吃了一驚,深為他不墜初志和獻身人文科學的執著與毅力所感動,也心甘情愿為之效力。記得榮慶在《新聞民俗學》導論里說:“本書在學術上要處理的癥結是,構建新聞民俗學學科體系中國際視野與中國特色之間的矛盾。”這條紅線貫穿于這部專著始終,顯示了一個學人高遠的生命寄托。
在《新聞民俗學》校改、付梓的同時,榮慶又像一匹馳騁疆場的奮蹄老馬,要對自己的“筆墨人生做個交待”——從歷年撰寫的三千余篇文稿中,挑選四百多篇,結集成冊,擬交作家出版社印行,并再次囑托我做《從新聞黑洞跳進又跳出》一書編審與校閱工作。由于這部學術性、文學性兼容的著作涉及學科廣泛、學術議題復雜,加之我做編輯養成的“吹毛求疵”習慣,弄得作者將不少篇章推倒重寫,大刪大改,個別文章乃至“割愛”舍去,竟然延遲預定出版周期數年而在所不惜。他對我的“咬文嚼字”與某些不留情面的質疑不但不惱,還鼓勵說:“我在西安再也找不到像你這么愛挑剔、能挑剔的好編輯了!”與前次不同的是,他要我寫篇序文。我逐卷逐篇逐段逐句讀了這么一個四卷本大部頭著作,深深地感覺到,這部文集,是作者為文化振興而吶喊的文本,是一位學人生命在筆端流淌的記錄。
生命是什么?古今中外的學人眾說紛紜。生物學認為,生命是蛋白質與基因存在的一種形式。物理學家普里高津認為,生命是一個耗散結構,任何生命都要與外界環境不斷地交換物質和能量。哲學家說,生命是一個由物質和能量構成的對立統一體。“萬物各得其所,生命壽長,終其年而不夭傷”。(《戰國策·秦策三》)“人之所寶,莫寶于生命。”(《北史·源賀傳》)榮慶與我是同代人,經歷了中國20世紀40年代迄今的所有社會變遷。他敬畏生命,珍愛生命,堅持不懈地記錄自我生命存在于社會的軌跡、感悟、心聲,輯而為《從新聞黑洞跳進又跳出》。
將《從新聞黑洞跳進又跳出》作為整部書的題目。所謂“新聞洞”,借自美國未來學家約翰·奈斯比特有關報紙“是一個在有一定之規的封閉系統中的強迫性選擇”。“新聞洞能自然而然的反映社會注意事項的輕重緩急”。作者在《中國新聞社》《報刊之友》《陜西旅游》《企業信息報》《香港商報》《今傳媒》等媒體當記者期間發表的3000余篇作品,都是經過媒體在“封閉系統中的強迫性選擇”,及時傳播了中外受眾急需的新聞信息。在編選本文集時,從中打撈出來一部分,做第二次“封閉系統中的強迫性選擇”——擇其較有史料價值、學術價值、鑒賞價值而選錄入書。
榮慶用“新聞黑洞”作為書名,意在何處?
“黑洞”——由一個只允許外部物質和輻射進入而不允許物質和輻射從中逃離的邊界即視界(event horizon)所規定的時空區域。“黑洞”是超級致密天體,它的體積趨向于零而密度無窮大。由于具有強大的吸引力,物體只要進入“黑洞”一定距離的范圍內即“黑洞”的引力場內,就會被吸收掉,連光線也不例外。“黑洞”吸進物質時會發射出X射線。引力場會使時空彎曲。當恒星的體積很大時,它的引力場對時空幾乎沒有什么影響,從恒星表面上某一點發的光可以朝任何方向沿直線射出。而恒星的半徑越小,它對周圍的時空彎曲作用就越大,朝某些角度發出的光就將沿彎曲空間返回恒星表面。等恒星的半徑小到一特定值(天文學稱“史瓦西半徑”)時,連垂直于其表面發射的光也可捕獲,此時恒星就變成了所謂“黑洞”——像宇宙中的“無底洞”,任何物質一旦掉進去,“似乎”再也不能逃出。天文科學家猜想,“黑洞”跟白矮星和中子星一樣,很可能也是由恒星演化而來的。“黑洞”特異于別的天體,具有人們無法直接觀察到它的“隱身術”。
榮慶提出“新聞黑洞”,指新聞作品易碎、易逝,猶如天體“黑洞”所具有的“隱身術”。
而“從新聞黑洞跳進又跳出”指什么呢?我曾想過很久,也與他討論過。
根據廣義相對論,空間會在引力場作用下彎曲,好像光仍沿任意兩點間最短距離傳播,但走的已非直線,而被強大的引力拉得偏離直線方向。而在“黑洞”周圍,空間變形成為“曲線”。這樣,即使是被“黑洞”擋著的恒星發出的光雖有一部分落入“黑洞”中消失,可另一部分光線會通過彎曲的空間、繞過“黑洞”而到達地球。這樣,地球人類仍可觀察到“黑洞”背面的星空,就像“黑洞”不存在一樣。進而言之,有些恒星不僅朝著地球發出的光能直接到達地球,它朝其他方向發射的光也可能被其附近的“黑洞”強大引力折射而到達地球。如此說來,地球人類不僅能看到該顆恒星的“臉”,同時還能看到其“側面”乃至“后背”。顯而易見,榮慶的“新聞黑洞”提法,借天文學“黑洞”打比方,對一部分落入“黑洞”中消失的作品如“川”(河)似的永遠“逝者如斯夫”,而讓另一部分如“光線會通過彎曲的空間、繞過‘黑洞’”而到達地球”的作品,供人們繼續觀察其“臉”、其“側面”乃至“后背”。作品結集了,提供了讀者閱讀的方便,而如何“觀察”、思辨,又當另論了。
從“新聞洞”而“新聞黑洞”,進而“從新聞黑洞跳進又跳出”,這種將形象思維、意象思維、邏輯思維聯結貫通做學問的方式,已成為榮慶讀書與寫作的經驗、習慣。我說他在“用生命書寫”,除了指他實實在在寫自我生存體驗外,也指他的作品里流露著的這種思維方式。
為這么一部四卷本巨著作序,從何說起呢?想來想去,不如將幾年來的看稿札記,約略集納,作為導讀,給讀者提供一些閱讀方便,就叫《用生命書寫——看稿絮語》吧!
《報壇擷英》卷校閱札記
新聞記者是新聞事件的記錄者、觀察者。只有實錄事實、洞察真偽,運用背景揭示事件本質,才能使新聞在轉化為歷史的過程中少一些迷茫與偽裝。新聞從業人員能做到此點者,可稱為報壇英才也。榮慶以此自勉,也以此結交同行。
榮慶將司馬遷譽為記者之師,特別推崇司馬遷紀事“不虛美、不隱惡”,“善敘事”,做“良史”的“實錄”精神。在他看來,記者猶如活躍的氧元素,活潑而善“化”;又如戲臺上的“八角身子”,生旦凈末丑哪個缺了補哪個,是全掛兒把式;還像六國販駱駝的,七十二行、三教九流之人,哪個都能搭上話。而對事實則必須準確、真實,返璞歸真地呈現人物、事件及其環境變遷的本來面目;力避隨意抑揚、愛憎任由己出。《一個老紅軍的落葉歸根》,是寫中國人人皆知的革命前輩習仲勛的。作者沒有溢美之詞,而是從富平迤山習仲勛陵園的觀感說起,再介紹民眾劇團與《梁秋燕》的誕生、毛澤東對習仲勛曾經的器重、精心策劃與保護李先念等回延安、冒風險保護西安城墻、“文革”在大街上之所見與長篇小說《劉志丹》事件本末、在金家巷第二次見到習仲勛等,環環相扣地寫出了這位老紅軍與人民之間的血肉聯系——每則傳奇故事都蘊藏了民心。《難忘喲,那一場“雄雌之風”》,是中國當代社會轉折期的一個縮影,也是作者人生轉折點的一份真實記錄。《國殤》《黃帝陵詩文背后》《克林頓訪陜追記》《風雪旅韓日記》《報道西北大開發戰略的回眸》與《3·16車禍內情》《西安火車站爆炸案始末》《西安蘆蕩巷姚宅存世秘聞》《西安半坡遺址損壞嚴重》《漢長安城遺址遭嚴重破壞》《黑河啊黑河,救命的水》《驪山母親啊,我為您“討”來七字批語》《為秦兵馬俑受損呼吁》等,流露了他記者生涯中意氣風發、無所畏懼的為民請命、勇于擔當的作風。
榮慶還試圖打破同行是冤家的陋習,為諸多記者、編輯樹碑立傳。記者的文章常有振聾發聵、一紙風行之效,但記者為人、為學及其生存狀態,卻是“燈下黑”,很少為社會所了解。作者從清末女杰秋瑾、辛亥革命與報業元老于右任、民國報壇宗師張季鸞、為老百姓辦《老百姓》報的李敷仁、當代新聞學界旗手何微與甘惜分的卓越貢獻與高尚人生,到作者同時代的新華社記者王兆麟,中央電臺記者賀俊文、甘肅日報社記者武揚、嶺南報人張躍虎,陜西日報社記者杜耀峰、楊玉坤、吉虹,寶雞日報社記者寧麗君、劉斌,陜西省報刊審讀員薛耀晗、賈保民、張羽、王宗義,新加坡聯合早報記者邱程光,德國王安娜與美國史沫特萊、海倫·斯諾,出身名門、自學成才的李鎧博士等的從業腳步,“說故事”似地活靈活現、娓娓道來。讀了他寫這些人的“列傳”,便會明了“記者”是什么樣的人。他將同行作為“類的樣本”來探究,以其是否忠實地記錄歷史為標準加以衡量。“賣石灰見不得賣面的”慣常社會現象,在他筆下成了“惺惺相惜”、同行相親。
當記者不僅需要精通新聞知識和所采訪行業的專門知識,成為某領域的專家,并需經過長期的學術積累轉化為具有一定權威性的專欄作家、雜家、文化學者。閱讀本卷作品,可以看出榮慶在這方面的進取與努力。他撰寫的《王老九的詩歌風格及流派》《王老九之死》《賀丙丁和他的詩歌》《農民詩的對話》《黃土文化獨特人性的破譯與解密——評長篇小說〈陜西楞娃〉》《散評〈半閣城〉》《〈金城關〉及其他》《跟進老舍還原消失的那個北京——略說〈滿樹榆錢兒〉》《夢,在那并不遙遠的地方——與網友話文學》《聽平凹說三毛》《幾多李廣——“電視李廣”出奇死》《電視連續劇不是連環畫》等篇,涉及詩歌、小說、散文、游記、隨筆與電視劇諸多創作與欣賞的“時興”文學話題,集中反映了作者對中國當代文學的深刻思考。就我所知,他的文學批評起步于20世紀70年代,但并未將之作為主攻方向,故而文學評論時有時無、時斷時續。讀者由上述作品可以看到,作者對中外名著如饑似渴地吸納與咀嚼,時出創見。在文學批評園地,他是最早、最系統研究農民詩人王老九的詩風及其流派的學者。在《農民詩的對話》里,他依據當代市場化、城鎮化、國際化進程中文藝思潮的多元,從學術高度為農民詩做了深入淺出的定義,開創性地為農民詩提出了五條標準;在《農民詩和農民詩的歷史分期》里,將新中國成立迄今的農民詩劃分為三個時期評估,并對中國城市化中的農民詩走向做出預測,填補了我國農民詩歌研究領域的空白。同時,還從理論與實踐的結合上簡論了中國現代詩近百年的得失及當下的困境與出路,雖為一家之言,但也鞭辟入里,發人深思。
作者對《陜西楞娃》《半閣城》《金城關》《滿樹榆錢兒》四部長篇小說的評論,直擊節點,縱橫比較,以赤誠坦蕩的語言和灑脫睿智的文筆展現了文學評論上的開闊視野。他認為小說是運用語言形象地虛構故事、塑造人物以反映社會現實和揭示人性的文學體裁,并對當代小說創作粗制濫造的問題提出了五條糾正、引導的建議。他就文學批評界有學者將小說重故事情節泛化為“罪”的現象指出,這與中國小說史的文本成果不相符,也與中國人的閱讀習慣相悖離。主張作家用坐冷板凳和癡迷藝術的心態,創作本民族“史詩”式的小說,不必因了追求“功名利祿”和市場效應去制造“短命作品”或“文化垃圾”。榮慶有的放矢地強調了文學作品的語言問題。在他看來,文學是語言的藝術。小說藝術成就的高低,首推語言。語言不僅是作家與讀者交流思想感情的工具,還是構建小說“樓宇”的基因。上述四部新出版的小說,作家對本民族的語言都懷有深深的敬畏心。他斷言,中國21世紀不朽的文學作品,將出在甘坐冷板凳的“文學宗教圣徒”手里,歸根結底,取決于小說家語言藝術水平的高下。
本卷及其他卷還散嵌了作者寫的幾十首古體詩及民歌體詩。這種編排方式不比將詩收集在一起易讀,但卻保留了其詩最初發表的原貌,易于讀者連同散文、隨筆文本與題記一塊兒領悟詩的背景及其真諦。他說:“詩是諸種文學題材中最凝練、最講律動的藝術表達形式。”又說:“不管古體詩詞、山歌民謠還是自由詩(新詩),都追求空靈、抒情、節奏鏗鏘、韻律優美。”本書雖然選錄他的詩作較少,但都大氣磅礴,清新歡快,意境深沉,宛如行云流水而時出漣漪,體現了作者在真誠與浪漫兼容里跋涉的創作境界。
“振葉以尋根,觀瀾以索源”。榮慶主張文學創作應形象思維、邏輯思維、意向思維三種思維模式兼容。他認為,《周易》用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把復雜的宇宙人生圖景展示為一種可觀之象,便是中國傳統的意象性思維。而當代時尚的“快餐文學”,與“文以載道”相悖,患了“意向思維貧乏癥”。
《人世鏡像》卷校閱札記
每個人的一生,不管其社會地位與出身、歸宿如何,都是所處時代的縮影。其生其死、其榮辱貴賤,對當世后世都是一面鏡子。《人世鏡像》卷里所收篇章,涉及大人物,也有小人物;有精英,也有落魄者;有當代人,也有辭世者。讀者閱他人事跡,照他人影像,剖他人心跡,同時也照自我影像,剖自我心跡。花花世事“走馬燈”,讀來會饒有興味。
作者采寫《毛澤東水晶棺的由來》和高端人物王震、蕭克、李瑞環、王光英、杜義德、鄭斯林等的特稿與報道,從平凡的視角出發,將引語、對話、敘事、背景、白描與形體語言相結合,撥開了他們身上神秘的“光環”。讀者從親切、質樸的字里行間,當會明事悟理。《蝸牛風波》《邱會作談十六年囚徒生活》《吳桂賢暢談往事》《再訪吳桂賢》《姚連蔚“失蹤”與近況》等,通過采訪當事人,揭開了“文化大革命”風云人物如毛澤東主席夫人江青,14歲當紅軍后來成為林彪集團骨干、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軍委副總參謀長、總后勤部部長的邱會作將軍,由紡織女工而出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國務院副總理的吳桂賢,由工人“造反派頭目”而出任中共中央候補委員、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的姚連蔚的一些奇聞逸事及其政治淪落的境遇。這些篇章曾為中外媒體廣泛轉載,如今已成為研究“文革史”不可或缺的珍貴資料。
《“東陵大盜”和他的兒子》,寫盜掘清東陵的孫殿英將軍獨生子孫天義教授暢談乃父及自我人生。《一片秦聲渾不斷——臺北秦腔實驗劇團西安尋根》《臺灣國策顧問向中共獻策——趙耀東西安考察追蹤》《江南遇害始末》《渝生尋母、認父(柏楊)記》《萬里碧空孤帆遠——張學良公館開館側記》《蔣介石題黃帝陵碑的重刻》《丘逢甲謁黃帝陵》等,故事感人,充滿了臺灣海峽兩岸信息阻隔時期難割難舍的同胞情誼。《西安衛星測控中心訪問記》《“三十而立”,志在明天——記航空航天部第四研究院》《中國飛機城巡禮》《瞻顧西北天橋》《絲路第一關》《訪吳瑞》《數學奇才王國俊》《中國電子科學家的搖籃》《“神箭”之母——訪中國空軍導彈學院》《走訪西藏民族學院》等,是榮慶最早揭開其人其事神秘面紗的作品。由于材料翔實客觀,不少為當事人口述親歷,作者運用高屋建瓴、縱橫交錯結構,生動簡明、深入淺出解析,將諸多高難度的題材,用剝繭抽絲、直達樞奧而又靈動風趣的方式呈現給讀者。如今讀來,還令人擊掌稱奇。
本卷所收為書法家、畫家、高僧、高道、教師、醫生、導演、戲劇與影視演員、體育明星、海外華人華僑寫的特稿,重在解析各人的生活環境、人生經歷、鮮為人知的內心世界及其過人的毅力,將“追星族”要追的“秘聞”,還原為切切實實、明明白白的人物原生態。作者用事實告訴人們,名人都是由無名而來的。每個為民族復興而奮爭的人,都可以轉化為有作為有成就的人。
《人世鏡像》卷末尾收的16篇隨筆、雜文和《驪山記勝》附錄諸篇小品,與前面的人物特稿、專訪的題材、文風截然不同,夾敘夾議、嬉笑怒罵而酣暢淋漓。劉勰《雕龍·雜文》云:“詳夫漢來雜文,名號多品:或典誥誓問,或覽略篇章,或曲操弄引,或吟諷謠詠,總括其名,并歸雜文之區。”經五四運動魯迅、瞿秋白、李大釗、陳獨秀、劉半農等人經營,雜文已成長為直接而迅速地反映社會事變或社會傾向的一種文藝性論文。我深知榮慶文筆犀利詼諧,在特定政治環境下長時間不愿意在雜文園地里耕耘。本卷所選錄的《樗祭》《耍猴獵猴雜說》《耗子鬧夜》《說扎勢》《說酒》《人老了》等文,在調侃中針砭時弊,鞭撻丑惡,求索真理。《屬龍說龍》《解讀壁虎》《西安應復名長安》《口號與網上口號》《白居易吟居宅》諸篇,在充滿知識趣味的字里行間曲折冷峭,入木三分,諷喻辛辣。
《天地走筆》卷校閱札記
唐代李復言《續玄怪錄》云:“吾已得煉形之術也,其術自無形成而煉成三尺之形,則上天入地,乘云駕鶴,千變萬化,無不可也。”《天地走筆》卷所說“天地”者,并非探究仙玄者流“上天入地”之幻術,而所收盡為游記、散文、隨筆,均是作者游歷祖國山河和境外名勝之實錄、觀感。
榮慶曾對網友說:“史籍是活的故事流逝之后留下的符號,后人要令它復活,就需要考辨、發掘,并用新的視角表達。我嘗試將紀實性、學術性、文學性糅合起來,不知道社會效果到底如何?”對散文創作,他有一系列獨到的見解,如說:“人物紀事的散文難寫,弄不好會如小小說或小說。兩者的區分,只在小說有故事情節縱向貫穿并由矛盾沖突演進。而人物刻畫與細節、心理、對話描寫,還有形體語言,與散文并無區別。人物紀事的散文也常以第一人稱抒情,較小說的情感顯露,也濃烈。”“散文貴在抒情,貴在刻畫人物細節中抒情。藝術的真實在細節,因而在細節中抒情者,乃情真意切。”他在評點大巖屋《野猴走親戚》時說:“用童話解析人類回歸自然保護地球生態的課題,動了腦筋。現在很多童話作者腹中空虛,離孩子又遠,寫的童話‘人話’太少,一個勁搬日韓歐美的外國貨,什么奧特曼、變形金剛之類,有什么故事性、文學性、科學性呢?令人生厭!”
他的散文理論,貫徹在自己的創作實踐中。
本卷選錄榮慶的游記散文最多,這可能與他當記者時將旅行作為新聞報道方式的職業習慣有關。盡管離開了一線采訪崗位,他每有出游消閑機會,總會在記“行”、記“動”中,描繪所見佳境、所聞異事、所吐快語、所出奇思妙想。由于學識功底厚實,思維敏捷,文筆靈動散漫,故所寫散文游記不同于記者,多了學術深度;不同于學者,多了流光溢彩的韻致;不同于作家,多了現場感與理性的沉思。
榮慶年逾古稀赴澳大利亞探親中創作的《金合歡國里且徜徉》《黑天鵝啊,“命定”的精靈》《攬得澳洲月,帶回古長安》《格里芬湖畔那座山,那座大廈》《我與考拉合影》《悉尼歌劇院的遐想》《大洋路看洋》等,將異域風情、文史掌故、山河瀚海、蟲鳥花卉攬于筆端,時而拈來與祖國物事比較,收放開闔自如。即使寫香港、澳門的《九龍城寨的最后一瞥》《大嶼山禮佛》《香港賞燈》《“試向番僧問,誰能識此關?”》《澳門蓮,常相憶》《海灣攪勝》等,一景一物亦隨其身行目視而呈現異趣橫生的動態美。寫境外的篇章雖然不多,但在字里行間洋溢了對故土、祖國的眷戀和對中華文化的摯愛。
榮慶寫大西北的游記題材甚多。從新疆的吐魯番、天山、喀納斯湖,甘肅的敦煌、陽關、永登、石馬坪、麥積山、南郭寺,到寧夏的西夏王陵、中衛,內蒙古的成陵,大漠草原、數千年史跡與英豪業績,在他筆下,發前人之所未發,溫古而出新知,抒個人之感慨與情思,一切都變“活”了。寫江南的篇章并不多,《張家界走筆》《年逾古稀登武當》《西湖覓戲》《千島湖觀日出》等,卻面對前人一寫再寫的套路,作者另辟蹊徑,如在西湖尋找千百年戲曲故事的脈絡遺跡,在千島湖觀賞噴薄而出的朝陽,故能出奇制勝。
作者是秦地人,書寫三秦游記多乃情理中事。這同工作間隙與友人、節假日與家人出行方便有關。他勤奮,踏進名山佳境,決不空歸。所到之處,總會將人們耳熟能詳的景象、物事來個“冷不丁”的自考、自問、自答。由于寫時不落俗套,心得不同凡響,學識宏博,文筆優美,讓人讀來忍不住神情一振。《紫柏山問道》《拜將壇上讀韓信》《金絲大峽谷暢行曲》《仙娥湖泛舟》等陜南游記,《統萬城,一部沙埋一千六百年的大書》《鎮北臺上望長城》《白云觀看大河》《紅堿淖乘舟記》《貂蟬與米脂婆姨》《闖王行宮游》等陜北游記,著眼于情境交融中的地理人文史跡考證、鉤沉,文散旨遠,言淺意深,別具一格。寫秦嶺與關中的《在河之洲》《龍門朝圣》《華山紅豆》《西上太白峰》《秋風習習儻駱道》《玉山行》《驅車五丈原》《周家大院觀光記》《尋訪楊虎城故居》《磻溪釣魚臺的隱秘》《龍門洞探微》《回望鄭國渠首》《關山草原:一本厚重的史冊》等人們所熟知的名勝地,作者采用陌生化的手法,即從游人熟視無睹中尋找其不熟悉的視點,在開掘中出新出彩出奇,形成“故地故景出新章,異情異趣費思量”的文本。
本卷選錄榮慶寫景狀物的純散文《我家的蟹爪蓮》《塞柳》《紫荊》《銀杏啊,銀杏》《藤》《雪中牡丹》等,篇目雖少,但用托物寄情的象征手法,自然而不牽強,巧妙而不澀枯,深沉而富情趣,顯示了學識、歷練及人格力量的厚積薄發。他寫的敘事散文《吾母最愛牡丹花》《碑》《洋洋》《看泰戲》《我的書齋》《買書》《圓夢馬球場》《想見母親》等,在灑脫輕松的筆調里,描繪故事細節,勾勒生活畫面,順勢抒發母子情、父子情、母女情、爺孫情、民族情、家國情,寫得那么深入肺腑,動人心魄。
榮慶平日不茍言笑、學人式沉思冷峻的外表與狂放不羈、作家式激情澎湃的內心,在散文里和諧統一了。
《驪山記勝》卷校閱札記
本卷原以《驪山的天籟地籟人籟》為名,取自《莊子·齊物論》子綦曰:“女(汝)聞人籟而未聞地籟,女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后人常以天籟指詩歌不事雕琢,得自然之趣。作者借“驪山的天籟地籟人籟”包含了故鄉的時空,兼及對驪山史事、人物、景致、逸聞探本溯源,務求歸真之旨。印刷前夕易卷名曰《驪山記勝》,則較為平實易懂。
本卷將作者有關驪山的散文、隨筆、札記輯錄在一起,讀來不乏人文科學的深沉思忖與美學享受。
《從驪山到天水追索中國八千年文明》《驪山溫泉利用史揭秘》《周武王征商簋》《驪山烽火戲諸侯與西周滅亡》《驪山秦東陵考及報道》《銅人與銅人原》《秦始皇陵地宮》《秦始皇地下陳兵軍幕》《秦俑修復掠影》《秦始皇銅立車的清理與修復》《秦兵馬俑一號坑復掘寫真》《重回人間閱春色——秦始皇兵馬俑坑全貌前瞻》《驪山魚池灣》等篇,直接取材于田野考古。但榮慶并未囿于勘測、發掘資料,而是將現場觀察、考古文物、前人成果、文獻記載與自我學識參詳比較,連類求同,鑒別索異,做力所能及的探究與考釋,發現他人未揭、未明、未道之秘。即使考古新聞,也不是有聞必錄,人云亦云,而是著力于探求歷史的真實面貌。這類文章大多依據最新的考古發掘資料,論證充分,學術含量高,見解獨到,又文筆曉暢,鮮活耐讀。例如,一些外國學者對“中國五千年文明史”尚且提出質疑,為什么作者竟然從家鄉驪山開始,“追索中國八千年文明”?這是異端邪說、虛幻浮靡之論么?讀罷文章,你就會盡掃心頭云翳而豁然開朗。又如學界對依據神話傳說論定中國人使用地熱水始自秦皇、漢武尚且猶豫難決,為什么作者敢于說新石器時代的中國原始先民就使用溫泉了?讀了《驪山溫泉利用史揭秘》你也會心中了然而踏實。
狀寫天籟地籟人籟的原始本真,是人文學者的科學探索過程,需要求真的立場與嚴謹的治學態度,來不得半點虛偽與文過飾非。榮慶對自己或他人過去所寫文章中的誤判、誤書或存疑問題,實事求是,勇敢面對,決不自欺欺人。本卷所收《酈道元及其遇害地陰盤驛亭再考》一文,是他自己糾正自己幾十年前發表在綜合性學術刊物《人文雜志》上關于此事考據失誤的專文。雖然那個失誤似乎已被學術界接受、并被國內一流酈學家在其專著中引用,但作者還是采取了“做一個本色的不摻假的學人”的態度,寫了這篇“再考”的自糾文章。
驪山的歷史文化名山地位,使一系列發生在這里的重大事件進入了權威的歷史教科書和學術著作。作者在撰寫本卷的一些篇章時,遇到了與某些前人、名著、權威學者觀點相沖撞或相悖逆的問題。他沒有回避與偷巧,而是以科學態度與無畏精神,著文直陳己見。如《驪戎國與“驪姬之亂”》一文,他提出與顧頡剛先生的不同看法;《杜甫與新豐杜甫溝》一文,他提出與郭沫若先生的不同看法;《“秦置麗邑”考辨》一文,他提出與林劍鳴先生的不同看法;《秦都櫟陽》一文,他與當代國內一些著名學者爭論;《扁鵲與驪山扁鵲墓》一文公開否定了河北、河南、山東、山西等省方志的記載;《驪山秦始皇坑儒谷》及答《少年文史報》讀者問,力主秦始皇兩次坑儒說;《他的名字與辛亥革命連在一起》一文,力主郭希仁是愛國而開放的陜西辛亥革命元勛、“近代大儒”,不能如《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陜西大事記》那樣定性為“反動”人物等。不管最終爭論結果如何,其堅持唯物史觀,堅守學者本色,追求真理,不盲目迷信權威的文人風骨,令人感佩。
秦始皇兵馬俑是誰發現的?西漢灞橋紙的發現是真的嗎?誰在保護西安明城墻上功不可沒?諸如此類議題,因功利與權位的緣由,曾先后在媒體觸發過激烈爭論。作者在《驪山尋寶者》《他與洛陽鏟相伴終生》《多好的武老,多好的長者》等篇章里,以大量事實作深入的科學考辨,得出了合乎實際的結論。《雄哉,伯雄!》與《尋找撬動地球的支點——魏效榮印象》等散文,在和盤托出人物個性中解析了兩位驪山籍學者攻取世界難題的執著。《驪宮葬梅妃及〈梅妃傳〉略考》一文,依據相關史籍,考證梅妃其人,提出自己的創見。《“驪宮禍胎”表里》《唐梨園弟子在驪山的故事》,幽默風趣,蘊藏思辨,別具文風。《驪山虎斑石與兵諫亭》一文,對西安事變這一改變中國歷史軌跡的重大事件中各當事人居功諉過的歧說,作者逐一鑒別比較,發表了客觀真實的獨到見解。他說,這就是人籟,有了人籟,才可能揭示地籟、天籟。
KiNEbsZbSl6U1gl57N1qxOgHEwyvsiAa7I62DWdAAnw=讀《驪山記勝》卷,深感作者在繪景記事中,運用詩文、典籍、文物考古、地望勘驗、人物對接印證等綜合分析、辯證思考的方式,堅持當本色學人,寫本色文章的標準,書寫了與驪山相關的女媧氏、周武王、周幽王與褒姒、秦孝公與商鞅、驪姬、扁鵲、秦始皇、呂不韋、李斯、趙高、秦二世、邵平、漢高祖、項羽、馮衍、班婕妤、楊沛、賈洪、酈道元、唐太宗、李靖、張儉、馬周、韋嗣立、唐玄宗與楊貴妃、梅妃、僧一行、李白、杜甫、王維、王昌齡、儲光羲、杜牧、李商隱、王建、段秀實、張載、蘇軾、趙統、康熙、魯迅、胡景翼、馮玉祥、張學良、楊虎城、蔣介石等人物的作為。用這種科學態度寫出的散文、隨筆、游記、小品,形式活潑,內容真實,學識博雅,耐人尋味。從一定意義上說,《驪山記勝》卷也是一部絢麗多彩的地方性歷史地理著作。它彌補了史志文獻的缺失,足可以作為一方鄉土教材和旅游指南之用。
一個人的生命有限,其對社會貢獻的大小,并不能以官位高低、金錢多寡、處境順逆決定。劉榮慶的兩卷本《新聞民俗學》四卷本《從新聞黑洞跳進又跳出》,還有手頭正在修改、編輯的《中國古代戲劇史述略》《長安美術通史》《報人說報》三部著作,集中反映了一個學人的“中國心”“民族情”。他外表瘦削卻在艱困的生存中奮力書寫。事物相反相成。老子云:“上善若水……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此乃柔德也;故柔之勝剛,弱之勝強堅。”要征服、摧垮、磨滅這樣似乎羸弱得不堪一擊的生命,其實是很難很難的。這就是我與榮慶相識相交40余年體察之所得,也是我看稿之后想表明的心語。是為序。
附劉榮慶先生《題記》:
周至李君三槐,本余摯友,乃陜西省社會科學院退休學人。此序乃其連續不輟三個春夏秋冬披閱拙稿之札記也。弟妹劉佩蘭扶病鼓勵夫君為友無私效勞。《新聞民俗學》《從新聞黑洞跳進又跳出》兩書300余萬言里,也滲透了三槐、佩蘭伉儷的心血。感恩無以為報,賦詩以銘:莫道人情如紙薄,天賜摯友誰勝我?兩度困厄君扶勉,三尺書稿汝披閱。自古序文多應景,罕見心語娓娓說。人生但逢一知己,敞開胸襟共切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