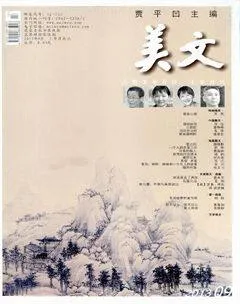誰染霜林醉

諸榮會
江蘇溧水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某出版社副編審。有作品發表并入選《中國散文60年》等選本。出版散文集等十數種。曾獲“紫金山文學獎”等多種獎項。
一
“南京徐悲鴻故居”位于該市傅厚崗6號。我工作的辦公地離那兒只一箭之遙,每天上下班我都要從它門前走過,每次走過時我幾乎總會不自覺地看上它一眼——有時候目光只在它日漸銹蝕的大門上一掃而過;有時候目光又會越過圍墻看到里面那兩棵高大的白楊,還有那幢西式的小樓,以及它屋頂上立在瓦行間的瓦菲;有時遇大門偶爾開著,我會稍稍放慢腳步,讓目光穿過大門,看見不大的庭園里有碧草、綠樹、紅花——每當此時,我又會常禁不住想,這樣一個略顯陰冷的小院內,如果能增加幾株紅楓,確實會生色許多、溫馨許多。
我之所以會這樣想,是因為徐悲鴻曾將此住處名之“無楓堂”,且這小院內又的確曾種植過紅楓。
1932年下半年,徐悲鴻這處住處落成后,他的一位學生為老師送上了一份別致的禮物:她讓父親從老家安慶捎來十多株紅楓樹苗種在老師的庭院里。這些樹苗第二年春天都成活了,且長得都很好,這讓徐悲鴻非常高興,他想象著一到秋后,每天早上推開窗戶,便都是一派“停車坐愛楓林晚”的詩情畫意了。
可是沒想到,第二年夏的一天,徐悲鴻去上海為張大千祝壽,再回到家里時他傻了眼:院中的所有楓樹都被連根鏟除得一棵不留。
不用問,那一定是夫人蔣碧薇命人干的。蔣碧薇之所以這么干,是因為她要將一個在她看來十足的愛情陰謀徹底粉碎,并將之斬草除根。
后世的許多人只知道徐悲鴻這位中國現代美術史上的繪畫大師、現代美術教育的奠基人先后有過兩位妻子蔣碧薇和廖靜文,前者給了他一生中最初的愛,后者用自己的愛陪伴著徐悲鴻走到了人生的盡頭;并不太清楚在徐悲鴻的生命歷程中還曾有過另一段愛情,也不知道這段愛情的女主角是誰。
1964年10月,蔣碧薇以被遺棄者和被傷害者的身份出版了她的《蔣碧薇回憶錄》,1984年6月,廖靜文以承接者與忠貞者的身份在大陸也出版了她的《徐悲鴻一生——我的回憶》,在這兩部回憶錄中,兩個前后成為徐悲鴻妻子的女人,都不約而同地回避了另一個女人,她們在各自的書中連她真實的姓名也不愿給她留下,幾處非涉及她不可的情節中,她的名字只是“孫韻君”和“女學生”等。然而,這位“女學生”絕不是一個在徐悲鴻生命歷程和藝術歷程中可有可無的角色,雖然她并不曾與徐悲鴻結過婚,但是對他的影響恐怕并不比與他結過婚的她們小,與此同時,她們的人生實際上也因為這個女人而發生了很大的改變。
二
徐悲鴻看到自家院里的景象驚呆了,他懷疑自己是不是走錯門了,眼前這個院子是自家的院子嗎?只見松、竹、梅,桃、李、杏等觀賞植物一應俱全,地面還植上了草坪,草坪上還撐起了兩把巨型遮陽傘,傘下放有圓桌和藤椅……原來的一切都被連根鏟除了,連一點影子也沒了。徐悲鴻立在那兒半天沒說出一句話來,妻子蔣碧薇則滿臉堆笑地迎上去說:“大家都說我們公館和院落風格不大協調,我一看也是,就沒有和你商量,把它做了小的變動。因怕耽誤你的創作,所以讓園林工人抓了點緊,趁你不在家的幾天,把它突擊完成了。不少朋友來看了,都說有法蘭西浪漫色彩,也確實,每每走在其中,我都有回到法國巴黎的感覺。”說話語氣、神態,充滿了虔誠,讓旁人聽來似乎對老公充滿了愛意,且絕對唯命是從。然而徐悲鴻望著眼前這個與自己相濡以沫十幾年的女人,似乎不認識似的,他絕沒想到她竟有著如此的心計、如此的手段,同時他幾乎看到了這個人內心原來有著一顆狠毒的心。徐悲鴻無言以對,憤怒無比,可又無可奈何,最終一閃身繞過了迎面的妻子,默默走上樓去,走進自己的畫室。
等到徐悲鴻默默地上樓去了,蔣碧薇露出了一絲不易覺察的薇笑,她知道自己又一次勝利了。他們夫妻間十多年來,每次發生爭執,最后都是以徐悲鴻的沉默而告終,這一次似乎也是一樣。
然而,蔣碧薇哪里知道,這一次并非如此簡單,愛情的種子一旦生根發芽,哪是她如此簡單粗暴之舉便可以斬草除根的嗎?有時甚至會適得其反!
走進畫室的徐悲鴻,先是默默呆坐了一番,然后展紙濡墨,揮毫寫下了三個大字“無楓堂”,然后除落下了自己的名款、鈐上了自己的名印外,又鈐上了一枚他早已刻好卻一直不曾公開用過的閑章,印文為“大慈大悲”,并從此以后將自己住處的齋號名之曰“無楓堂”。
千萬不要以為徐悲鴻此舉只是為那慘死的十多棵楓樹苗而內心悲摧、祈天禱地,實際上他這是以一種特殊的方式,向尚是自己妻子的蔣碧薇,也向這個世界,表達著自己從今以后的一種態度和決心,即,將一直深埋于心的那段戀情不再埋藏,且從此為之矢志不渝。原來徐悲鴻這枚閑章中的“悲”和“慈”二字,各取自于他自己名字中的一字和他當時深愛上的一個女人的名字中的一字——這個女人叫孫多慈。
從此以后,這兩枚“無楓堂”和“大慈大悲”閑章常常被徐悲鴻公然鈐在自己的畫作上,由此見證了中國現代美術史上的一場曠世之戀。
三
其實,直到“楓樹事件”發生,徐悲鴻與孫多慈之間的感情雖然已超越了一般的師生之情,但是對于他們雙方來說,也都多茫然而矛盾。當然,因為各自人生閱歷的深淺大為不同,其茫然和矛盾的程度還是各有著很大差別的。徐悲鴻雖然對于這份感情也時常茫然失措,但是他自己心里很清楚的是,這種茫然失措正是在面對一份不該產生的愛情所生出的無奈所致,所以他的心中矛盾更大;而孫多慈更多的只是茫然她更多的時候只是將一直給予她種種關心和愛護的徐悲鴻當作是一位大哥哥,甚至是一位如父親般的長輩。在得知徐悲鴻喬遷之喜的消息后,孫多慈想去送一份賀禮,但送什么好呢?她曾找自己的好友、同為中央大學同學的李家應和吳健雄商量:“先生要搬新居,我這個做學生的,總得要表示表示吧?可送什么好呢?一般的東西,先生看不上。太招搖太顯眼了,讓師母知道了,又會不容忍。你腦子靈活,幫我給拿個主意吧!”
沒想到她倆反而首先要孫多慈說說她與徐悲鴻到底算是什么關系。孫多慈面對好友老老實實地說:“我們之間的關系,絕沒有外界傳的那么渾濁,但也絕不是一潭清水。說實在的,我自己也很矛盾,說有‘愛’,不確切,說沒有‘愛’,也是一句假話。”由此我們足可看出,直到此時孫多慈或許也并沒能分清楚遇到的和自己心里升起的這份感情到底是一種什么樣的感情,到底是不是就是愛情?
李家應與吳健雄說,既是這樣的關系,她倆都覺得這禮很難送。她們幫著想了半天也沒想出個送什么才覺合適的,最終還是孫多慈自己說“我倒是有個謀劃,自知也還算是個絕點子,但不知……”
她倆自然急忙問是什么,孫多慈于是認真地說:“我盤算著,先生公館有這么大的院子,送他一些楓樹苗,讓他栽在院子里,如何?”
孫多慈的話讓李家應目瞪口呆了半天,說:“真有你的呵,簡直太絕了!既特別又有新意。每到秋霜季節,徐大師或憑窗凝思,或庭院踱步,只要一看見這滿樹紅葉,馬上就想到了你。而且樹會一年年長大,一年年長高,你這禮物也會一年年增值。甚至到你們,不,是我們都老了,甚至都不在人世了,你對徐悲鴻的這份心思,仍會留在這個世上!更重要的師母即便知道樹苗是別人送的禮物,也絕不會想到是你這個小丫頭,她一定只會猜想是某個老頭。”
收到孫多慈的這份“大禮”,徐悲鴻當然很高興,但是他立即想到的也只是“停車坐愛楓林晚”的詩句,而非“曉來誰染霜林醉”的意境,為此他還與孫多慈開玩笑地說:“你送我這禮物,是不是想讓我再去買一輛車,一輛四個輪子的能滿大街跑的車?”
其實,這兩個小女人,雖然都是中央大學的高材生,甚至吳健雄日后竟成了名滿天下的物理學家,但是此時她們都低估了只是家庭婦女的蔣碧薇,甚至徐悲鴻也低估了。其實像她這樣的女人,用張愛玲的話來說,她們絕對比多數知識女性和職業女性厲害,因為“她們日日以婚姻為她們的事業,豈能不厲害!”蔣碧薇很快就知道了楓樹的來歷——那是一場愛情的陰謀,她一定要粉碎它!但是她在等待,等待一個合適的時機,再選擇一種合適的方式。
蔣碧薇終于等到了一個合適的機會,也選擇了一個她自以為合適的方式,又一次取得了一場愛的保衛戰的完勝。像這樣的完勝算起來這已經是她一年多時間里連續取得的第四場了。

四
蔣碧薇贏得的第一場勝利,自然是在一回到家時與徐悲鴻的初戰中。
1930年12月初的一天,遠在宜興老家的蔣碧薇突然接到一封徐悲鴻的信,信中徐悲鴻說:“碧薇,你快點回南京吧!你要是再不回來,我恐怕要愛上別人了!”
看到這樣的話,蔣碧薇說實話也并沒太放在心上,也沒有立即趕回南京,而更多的只是將此當作是夫妻間的一個小小玩笑而已,但想想還是決定再過一個星期后就回家。一個星期后,徐悲鴻收到蔣碧薇從宜興發來的電報,說第二天便到家。此時徐悲鴻突然間似乎又有點后悔讓妻子這么快就回來,更后悔自己在信上寫的那句話,因為他知道蔣碧薇回來一定會因為這句話而興師問罪的,他對于妻子的個性太了解,知道她不是個省油的燈,于是他在當天寫給好友舒新城的信中又說:“太太明日入都,從此天下多事。”
那么徐悲鴻既已知道蔣碧薇的為人,可為什么還要不打自招呢?
其實徐悲鴻當時在信上寫的這句話可謂是實話實說,因為他已明顯地感覺到自己已有“戀愛傾向”,而他以為這都只是因為妻子不在家而產生的一種想入非非,所以他想讓妻早點回來,這樣自己的那份想入非非便可自然結束了。徐悲鴻如此矛盾的舉動正是他此時矛盾心態的反應。
今天我們站在一個旁觀者的角度來看待徐悲鴻此舉動和心理,至少可以看出兩點:一是他的“戀愛傾向”的產生,并非是主觀上因為嫌棄妻子蔣碧薇所至,也并非是想背著妻子搞“婚外情”;二是他也想盡快妥善結束自己這種不該產生的“戀愛傾向”,更不想發展下去,至少是主觀上不想。如果不是那樣,他根本就沒有必要向妻子“不打自招”,更不會主動將她叫回家來給自己“添亂”。那么我們不妨一廂情愿地設想一下,如果蔣碧薇回家后,能順著徐悲鴻所希望的那樣做,或許事情的發展未必不會真有一個他所希望的結果。徐悲鴻在給蔣碧薇寫信時一定相信妻子會順著他的希望“幫助”他的,道理很簡單:任何一個做妻子一定都是希望如此的。
是的,蔣碧薇當然也希望如此,希望徐悲鴻不要沾上外面任何的花花草草,已經沾上了也要盡快一刀兩斷、連根鏟除,且刻不容緩。
首先是立即審問徐悲鴻:“說,怎么回事?怎么我一不在家,你這感情就出問題了?”徐悲鴻自知理虧,支支吾吾道:“你也別太著急,聽我慢慢向你解釋,好嗎?”
并沒等徐悲鴻解釋一句,蔣碧薇又聲淚俱下:“我是一個普普通通的女人,是一個只需要家庭生活穩定的女人!悲鴻,難道這么一點小小要求,你都不能答應我嗎?”此時徐悲鴻更是陷入了自責,非常真誠地說:“我既然能向你承認感情出軌,就說明我對這件事已有悔意!”
蔣碧薇邊哭邊打斷了他的話說:“自從當年……”一聽此言,徐悲鴻無話可說。是的,他能說什么呢?這是他們夫妻間感情的起點,也是他們夫妻風雨同舟、相濡以沫十七年最牢固的基礎。
那時候徐悲鴻只是一個從宜興來到上海灘,一面靠為一些雜志社畫畫插圖謀生、一面刻苦求學的青年,他的這種精神得到時為復旦大學教授也是宜興同鄉前輩蔣梅笙的賞識,為此徐悲鴻常去蔣府,一來二去便認識了蔣梅笙的千金蔣棠珍。漸漸地,這個早已許配無錫大戶查家公子的蔣小姐,竟對徐悲鴻生出好感,并于1916年改名蔣碧薇,隨徐悲鴻私奔去了日本,后又于1919年去了法國巴黎,害得蔣梅笙一張老臉無處放,只好對外宣稱女兒暴病身亡了,并還裝模作樣為她辦了一場喪事,在棺材里放了幾塊石頭抬出去埋了才算完事。不過也有人據此推斷,這一切都是蔣家父女合演的一出雙簧——蔣梅笙其實也看中了徐悲鴻,但由于已將女兒許配查家在先,因此平時就曾常當著蔣碧薇的面感嘆,“我要再有一個女兒就好了”,蔣碧薇這才“心領神會”。不過實情究竟如如何,今天我們已難以搞清楚了,但我們清楚的是,從此以后,蔣碧薇的確與徐悲鴻在海外度過了一段艱難的生活,直到1927年回國。那時他們生活非常艱苦,但感情卻十分融洽。據說有一次,蔣碧薇在巴黎的一家商場里看中了一件風衣,試穿后也覺得非常滿意,店里的老板和店員都說漂亮,慫恿她買下,并說可以優惠,但蔣碧薇最終還是因為囊中羞澀而戀戀不舍地脫下了。可是哪知道她離開商場后心里又放不下,事后她竟又多次去那家商場去看那件風衣。徐悲鴻知道此事后心里非常難過,因為他知道,蔣碧薇怎么說在家也算是個闊小姐,竟然跟隨著自己過這樣的生活。但是他那時能做的唯有刻苦學習、努力繪畫。不久,他終于有一幅畫賣了一個不錯的價錢,拿到錢后徐悲鴻立即去那家商場買下了那件風衣。當蔣碧薇穿上這件風衣時,她眼淚撲漱漱直掉,但是心中卻充滿了喜悅。蔣碧薇與徐悲鴻便是如此相濡以沫走過了十七年,其間感情有多深,想來夫妻雙方都是不用提而非常明白的。且對于徐悲鴻來說,他多少還懷有一種對蔣碧薇的歉疚。
或許是蔣碧薇也正是因為明知這一點,所以每當夫妻發生爭執,她總以此為殺手锏來攻擊徐悲鴻軟肋。徐悲鴻自然也是每次都無言以對。 徐悲鴻再次無語。蔣碧薇卻不依不饒:“我最恨的,就是你現在這樣!一到關鍵時刻,就緘口不語。你不說話就是看我不起,看我不起你就會移情別戀……”
“碧薇,你一定要相信我,這事剛剛才開始,我會好好地把握它,不會任它自由發展的。”徐悲鴻的態度仍十分誠懇。
“我不是那種胡攪蠻纏的女人,我也理解我不在南京的這段時間,你作為男人,內心必然產生的空虛。但你必須告訴我,這個女人是誰,你和她是如何開始的,現在已經進行到哪個階段了……”
然而徐悲鴻怎么能輕易說出那個女人呢,更何況她在他看來還只是個孩子,他要對她負責,即使僅僅是老師他也有保護她的責任。
但是盡管如此,這一場初戰,應該說是以蔣碧薇的勝利而告終的。雖然徐悲鴻最終并沒肯“交待”那個“第三者”的名字,但是這在蔣碧薇看來是小菜一碟的事情,并無關緊要,重要的是她要在下一步掌握住其“罪證”。

五
不久,蔣碧薇果然利用一個機會,有意無意間便又贏得了第二次戰役的勝利,那是在1931年春的一天。
那天,在徐悲鴻任教的中央大學門口,蔣碧薇無意間碰到了徐悲鴻的老朋友盛成和宜黃大師,他們正應約去徐悲鴻畫室看畫,招呼間,宜黃大師邀蔣一同前往,這本是其一種禮貌和客套,但是蔣碧薇就此心生一計,來了個順桿而上,真的隨他們一同前去了。
遠遠在畫室門口等著的徐悲鴻一見蔣碧薇也一同走來,不禁心里暗暗叫苦,但一切已為時已晚。
一進畫室,蔣碧薇便儼然如偵探一般四下里搜尋起來,弄得不明就里的宜黃大師好生奇怪,而徐悲鴻更是十分尷尬。好在她搜了半天也沒搜出什么在她看來有價值的“罪證”,最后就剩下畫架上兩幅用布蒙著的畫沒看了,于是她呼的一聲,將布掀開——“呵!”在場的人幾乎都同時情不自禁地發出了驚嘆聲,整個畫室也仿佛一瞬間增加了光亮,畫面上一輪明月當空,明亮而溫馨的月色下,古老的城頭之上,畫家自己席地而坐,不遠處一位少女雙手抱立,似正享受著大自然美好的月光,又似在享受畫家深情的目光,畫的一角有徐悲鴻親題的畫名:臺城月夜。

盛成和宜黃大師被畫面所描繪出的那種意境,那份深情給深深地震撼了;而蔣碧薇更是被驚呆了,不過她并不是因為這畫的藝術效果,更因為她這一瞬間有了豐富的聯想,只見她頓時臉色蒼白,雙腿發軟,要不是盛成當時眼疾手快輕輕從一旁扶了她一把,說不定她當場就癱倒在地了。好在這也就一瞬間,她就似乎恢復了常態。然而又裝著若無其事地說:“這畫既已畫好了,怎么不帶回家呵?”說著便不由分說,叫了兩個學生幫忙,將它連同一張《孫多慈像》的素描一起,用一些舊報紙七手八腳包了起來。
“罪證”既已到手,蔣碧薇自然選擇立馬離開了,以免夜長夢多。由于《臺城月夜》是畫在一張很大的三夾板上的,既不能折疊也不能卷,她于是就讓兩個幫助包扎的學生也幫她拿回家去,臨走時還對盛成和宜黃大師說:“你們看你們看,看細一點,記著要給我們悲鴻多提提意見哦!”完全是一種得勝還朝的風度。
徐悲鴻雖然心里恨得癢癢,但由于在學校,在大庭廣眾之下,在朋友面前,在學生面前,他只能裝傻,不能阻止,最終也只是對盛成無奈地問了一句:“是不是一只準備咬人的母老虎呵?”
《臺城月夜》在蔣碧薇看來是徐悲鴻背叛自己的最好的“罪證”,因為他將畫中人畫得那種美好,一個畫家,只有當他深愛著畫中人時,他才會捕捉她最美的姿態、神情,將她畫成世上最美的美人。的確,蔣碧薇對此太清楚了,也太有切身體會了,想當年,徐悲鴻那幅最初轟動歐洲的油畫代表作《簫聲》便正是以蔣碧薇為模特畫成的,但是每一個認識蔣碧薇本人的人都覺得,畫上的蔣碧薇比現實的蔣碧薇不知要美多少,但是它又怎么看都是蔣碧薇而不是別人。
罪證既已到手,她當然還要讓它公開示眾。于是蔣碧薇就將《臺城月夜》放在了家里的客廳里,但并不掛在墻上,而是將它靠墻立在地上。我們不妨設想一下,徐悲鴻在家里每天看著自己的這個“罪證”,心里將是什么滋味呵?!然而蔣碧薇要的就是你這種心里不是滋味!要的就是你低頭認罪!要的就是你無臉見人!她每天都在品嘗著自己的勝利,自己的得意,自己的驕傲,但是她絕沒想到,正是在這一過程中,徐悲鴻的心在日日哭泣,也日日變冷,更日日離她而去。而這原本又是蔣碧薇所并不希望的,她這一切舉動的所有目的,說實話原本是希望徐悲鴻不要離開自己。就這樣,蔣碧薇在自己設定的一個怪圈中不能自拔。
關于《臺城月夜》的結局,蔣碧薇晚年在她的回憶錄中這樣寫道:
至于那幅《臺城夜月》,是畫在一塊三夾板上的,徐先生既不能將它藏起,整天擱在那里,自己看看也覺得有點刺眼。一天,徐先生要為劉大悲先生的老太爺畫像,他自動地將那畫刮去,畫上了劉老太爺。一件藝術杰作就這樣從人間永遠地消失了。
蔣碧薇當然希望永遠消失的并不只是畫,因此,不久她又發動了第三次戰役。
那是1931年7月,國立中央大學藝術專修科招考放榜,學校教學大樓外的報廊里,徐悲鴻將考生試卷和分數同時當眾公布出來了。這在南京,在中國,都是極罕見的激進做法,自然引得爭先恐后的觀者云集。蔣碧薇竟然也擠在看榜的人群中,這不由得讓人覺得奇怪,她關心誰呢?
她真有關心的人,那不是別人,就是孫多慈。當她看到孫多慈的名字高高排在第一名,以95分的高分無人能及時,她帶頭高聲地說:“這個結果我早就預料到了,是你的得意門生嘛,看你面子,看你感情,自然要多給幾分的。”此言一出,榜前的人群一下子如同炸開了鍋,一時議論紛紛。明明是按作品水平判出的結果,一時卻變成有舞弊嫌疑的不正常事情了。徐悲鴻終于憤怒了,他再也顧不得在大庭廣眾之下了,針鋒相對地對蔣碧薇說:“知道你是要說這話的,所以公布成績時,連試卷也一起貼出去了。她的水平如何,她可以得多少分,試卷說話。”
蔣碧薇也不甘示弱,說:“誰不知道你這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呵!錄取孫多慈才是你最終的目的。好啊,你的心愿達到了,你們可以更光明正大地在一起了!”
話既已說得如此白了,徐悲鴻也顧不得“家丑不可外揚”的古訓了,高聲說:“告訴你蔣碧薇,不要把話說得這么難聽。如果我徐悲鴻想離婚,想拆散這個家庭,早就橫下心與你分手了。之所以還和你保持夫妻關系,是因為在我的腦海里,還從沒有想過要和誰結婚,所以也不存在要和誰離婚!”
……
就這樣,那年夏天,孫多慈第一次與徐悲鴻、蔣碧薇名字一起出現在了南京各個小報的花邊新聞中。當然這并不是蔣碧薇的目的,她的目的是中大不要錄取孫多慈,但最終結果自然不會以她的意志為轉移,1931年9月,孫多慈還是以圖畫第一名的成績,被南京中央大學藝術專修科錄取了。所以說蔣碧薇發動的這一次戰役沒有取得完勝,但在她看來還是不乏戰果的,至少是她將徐悲鴻與孫多慈背后的“丑”事暴露到了光天化日之下了,看他們以后還敢再不好自為之!
可是令蔣碧薇沒有想到的是,徐悲鴻卻正式向她提出了離婚。
說良心話,蔣碧薇種種行為的目的并不是為了離婚,因此當徐悲鴻在上面,當著朋友將“離婚”兩個字在桌面上第一次說出來時,蔣碧薇先是愣了一下,然后竟然說:“悲鴻,你說什么?你再說一遍!”
徐悲鴻又高聲地說了一遍:“我們離婚吧!”這一次蔣碧薇聽得真真切切。回到南京后,她又接到了徐悲鴻的信:
我觀察你,近來惟以使我憂煩苦惱為樂,所以我不能再忍受。吾人之結合,全憑于愛,今愛已無存,相處亦已不可能。此后我按月寄你兩百金,直到萬金為止。兩兒由你撫養,總之你亦在外十年,應可自立謀生。
每字每句,似都是深思熟熟后才落筆的,絕不像是玩笑,戲言。
六
其實,徐悲鴻此時也沒有完全做好離婚的準備,事實上不久后,他在吳稚暉等人的勸說下便又放棄了離婚的行動。這看起來當然都是因為徐悲鴻給了一次吳稚暉“面子”,是的,吳推暉的“面子”不能不給,因為她是“世界文化名人”,是令人敬重的長者,又是出手幫了自己大忙的人(傅厚崗的那塊宅地便是他看到徐家與鄰居實在太擠而出了三千大洋幫助徐悲鴻買下的),但說到底只是徐悲鴻自己借坡下驢而已,真正做主的還是徐悲鴻本人。吳稚暉在勸說信里這樣責問徐悲鴻:“尊夫人儀態萬方,先生尚復何求?……倘覺感情無法控制,則避之不見可乎?”徐悲鴻無法回答,但無法回答的原因或許是吳稚暉又一次的“憶苦思甜”讓他又想起了自己與蔣碧薇過去的那些相濡以沫的日日夜夜,也難以忘懷于昔日的那份濃濃的感情,當然也不想就此輕易放棄這段感情。
然而,當年生活那么艱難,夫妻反而能相濡以沫,現在一切都好了,為什么不能好好過下去呢?
是的,相對于十幾年前,生活是好了,但是徐悲鴻與蔣碧薇人都變了。
當年買一件普通的風衣對于徐悲鴻來說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但也就是一件普通的風衣就能讓蔣碧薇激動得熱淚漣漣。可是現在呢?徐悲鴻可以置地建別墅,蔣碧薇自然再不會因為一件衣物之類激動了,相反她覺得今天所有的一切都是她應該得到的報答,甚至徐悲鴻這個人連同他的才華都應該由她來支配——她本來就是個強勢的小姐!
蔣碧薇的強勢在回國后不久就表現了出來。
眾所周知,徐悲鴻不但是一個畫家,更是一個理想主義的美術教育家,他在美術教育上有兩個偉大的理想:一是努力實現中西方美術的融合,二是努力開展美術教育的普及。1928年春,田漢、歐陽予倩等成立南國社,剛回國不久的徐悲鴻便以極大的熱情加入其中,此時他雄心勃勃,于這年的春節,創辦了南國藝術學院,徐悲鴻任繪畫部主任。但南國藝術學院的教學基本是義務教學的性質,這讓蔣碧薇一直反對,她覺得徐悲鴻這是浪費自己的才華,這讓徐悲鴻很是反感。這年4月中旬,徐悲鴻又受聘南京中央大學。蔣碧薇竟然以此為借口,背著徐悲鴻去南國藝術學院幫著徐悲鴻辭去了那兒的教職,并擅自雇了一輛車,將徐悲鴻在南國藝術學院內的畫具全部搬回了家。這讓徐悲鴻萬分尷尬,外人以為這都真是徐悲鴻授意的,并由此說徐悲鴻不愿做大眾義務教育的工作,只認錢。
由此生活中一例,已可見出兩人在價值觀和處事風格上的差異。當然這樣的差異并不足以使他們的分手,更不能成為他們分手的理由。
無論是當時還是后世,一些人都將徐孫之戀當著一發攻擊徐悲鴻人品的炮彈,覺得他這樣不僅僅是花花公子的行為,還是一種陳世美的行徑,因為他“遺棄”蔣碧薇這個糟糠之妻,實際上是過河拆橋,是忘恩負義。孫多慈的父親孫傳瑗得知女兒與徐悲鴻之間的緋聞后,第一反應便是如此認為,也正是為此,他一直不能認可徐悲鴻的人品,直到后來徐悲鴻已與蔣碧薇離婚后仍堅決反對女兒與徐悲鴻戀愛,寧可讓她嫁給同樣大孫多慈近二十歲的許紹棣。而作為徐悲鴻忘年交的吳稚暉,在那封給徐悲鴻的勸誡信中曾現身說法:“弟家中亦有黃臉婆,頗亦自足,使弟今日一摩登,明日一摩登,侍候年輕少女,吾不為也。”此話實際上也是指責徐悲鴻喜新厭舊。
至于蔣碧薇,她這樣想更是自然而然,她不但將其中的原因,而且更將其所有責任都歸結為孫多慈這個第三者的介入,歸結為徐悲鴻要做“陳世美”。
然而真的是如此簡單嗎?
或許徐悲鴻此時也在心里這樣問過自己無數遍,所以他要試一試。于是他放棄了離婚,攜上蔣碧薇去歐洲巡回畫展,且一去一年多——或許他正是想借此機會與蔣碧薇一起舊地重游,以對當年“艱苦奮斗”的重溫來重回夫妻昔日,同時他也想借此能夠忘掉“第三者”孫多慈。而留在南京的孫多慈,也試著去結識男朋友。
七
因為年齡、身份和地位的原因,在徐孫之戀全過程中,孫多慈應該說都一直處于被動中,她從來都沒有主動去“勾引”過作為老師的徐悲鴻,盡管蔣碧薇一次次地指責她,說是她勾引了自己的老公。
孫多慈走進徐悲鴻的生活實在充滿了偶然。
孫多慈的父親孫傳瑗原與當年的五省聯軍司令孫傳芳五百年前是一家,且還同輩分,孫傳芳便讓他做了自己的機要秘書,并對他十分信任,所以也曾一度位高權重。孫家在老家壽州,甚至在安徽也算是一名門大戶。后來孫傳瑗雖然投身文化教育事業,但因受各種關系的牽連,于1930年春天被蔣介石逮捕關押南京老虎橋監獄。這一年正是孫多慈高中畢業的那一年,她為此很受影響,以至成績一向很好的她高考落榜。暑假時她郁郁寡歡地從安慶來南京探視獄中的父親。
這里需要補充介紹一下老虎橋監獄、中央大學、國立美術陳列館和臺城在南京的位置,或許孫多慈與徐悲鴻后來能夠走到一起,都是因為它們之間靠得很近的緣故。當年的中央大學校園就是今天的東南大學,該校的大門幾乎是斜對面就是老虎橋監獄,老虎橋監獄向南百米就是長江路,當年的國立美術陳列館即今天的江蘇省美術館就在長江路上,至于臺城幾乎就在中央大學的后門口外。
那天,孫多慈探視父親時也得知了一個好消息:因為多方疏通,父親很快便能出獄了。這讓一直心情郁悶的孫多慈多少心情好了不少,于是走出監獄時使得平時很喜歡畫畫的她想到去不遠的美術陳列館看看。而此時徐悲鴻畫展正在那兒舉行,她一下子被徐悲鴻一幅幅大氣磅礴的杰作深深震撼了,也使得原本立志當作家只將畫畫作為業余愛好的她立志成為一名畫家。正好父親好友宗白華又是徐悲鴻的好友,于是在宗白華的介紹下,高考落榜生孫多慈成了中央大學徐悲鴻教授班上的一名旁聽生。這樣一名旁聽生,自然繪畫基礎是班上最差的一個;再加上徐悲鴻得知她又中文系落榜才“無奈”轉學美術的,這自然讓視美術為天下第一神圣事業的徐悲鴻很不以為然;即使是外貌上,孫多慈也不像是后世許多人猜測的和想象的那樣,一定是傾國傾城,讓徐悲鴻一見傾心,相反,她只是中人之上。總之孫多慈最初并沒引起徐慈鴻太多好感,甚至連太多的關注也不曾有。
然而僅僅過了幾個月,孫多慈這名本來水平在班上屬倒數的旁聽生,竟然以進步的神速讓徐悲鴻刮目相看,于是就有了在課堂上徐悲鴻對孫多慈的表揚,又就有了課后的幫助和鼓勵,又有了一同去校園后面不遠處的臺城寫生。
正是在古老的臺城之上,面對著眼前的荒城衰草、寒水煙柳,不但讓孫多慈觸景生情,對人生的無常、世態的炎涼大發感慨,而且流著眼淚向老師徐悲鴻講述了自己復雜的家庭背景與多舛的命運。徐悲鴻從來不曾想到這個十八歲的少女,竟有著如此令人感慨的人生,他被震驚了!他不自覺地將這孩子攬在懷中說:“不要難過,你以后無論遇到什么困難,在這個世界上一定會有一個人會保護你的,他就是我徐悲鴻!”并且在她額頭上輕輕一吻。不久后,徐悲鴻除了完成了素描《孫多慈像》,更完成了巨幅油畫《臺城月夜》。
應該說至此,徐悲鴻與孫多慈之間的關系雖然超出了一般的師生關系,但也并非如蔣碧薇等許多人想象的那樣已到了“師生戀”的程度。回過頭去看,恰恰是蔣碧薇的一次次欲將兩人分開的努力,適得其反地反而將他們本來只是一種隱私不停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而無法回避,事實上這也將他們越推越近,以至于真的使一場曠世的師生戀成為了事實。
1934年8月,徐悲鴻與蔣碧薇回到國內。經過了一年多的努力,徐悲鴻與孫多慈發現并不能將對方忘記;蔣碧薇也失望了,也累了,正好在巴黎時舊日追求者張道藩又找上門來,而此時的張道潘是國民政府的文化部長,又是蔣介石面前的紅人,與徐悲鴻比較起來前途更加無量,蔣碧薇于是毫不猶豫地投入了張道藩的懷抱。但是她臨走前并沒忘了向徐悲鴻開出條件,要他賠給自己的“青春損失費”:徐悲鴻自己的畫100幅、古代名畫40幅,外加現金100萬元。徐悲鴻照單全付,而且還多加了一幅,那是蔣碧薇最喜歡那張《琴課》——徐悲鴻是因為理虧,還是因為不忘當年的情分,還是二者兼而有之,只有徐悲鴻自己知道。
正是靠著徐悲鴻賠付的這筆財產,蔣碧薇無論是在大陸還是后來去臺灣后,日子都一直過得很滋潤,而徐悲鴻卻并不如意。據廖靜文《徐悲鴻一生》所載,為了盡早湊足蔣碧薇的那些畫和錢,徐悲鴻一度沒日沒夜地工作,以至積勞成疾,落下病根。因此在她看來,對于徐悲鴻58歲的英年早逝,蔣碧薇是負有一定責任的。
然而蔣碧薇決不這樣認為,她覺得所有的一切都是她應得的,甚至她覺得還不夠,以至于她在晚年出版的《蔣碧薇回憶錄》中時見抱怨之詞,以至于連她的親生女兒徐靜雯也讀不下去,并為此而很是不滿:
廖靜文寫的是基本符合父親形象的。蔣碧薇寫的就不顧事實真相,大罵父親,極不道德。我感到憤慨的是,她花了我父親一輩子的錢,臨分手時,父親還給她一百幅畫和一百萬元錢。這里面包括我和哥哥的撫養費,其實我和哥哥花了不到十分之一。母親就是靠這筆錢在臺灣度過余生的。可她罵了父親一輩子,真不知父親前生欠她什么!
然而,徐靜雯或許并不知道,她的母親直到死,臥室里還放著她父親徐悲鴻的那幅《琴課》,而張道藩的畫只放在客廳里。

其實蔣碧薇也是愛徐悲鴻的,這種愛或許至死都不曾改變,正是因為愛,她才對徐悲鴻“嚴格要求”,才不允許他有任何過錯,才不允許他有任何出軌,無論是肉體還是精神;一旦徐悲鴻稍有閃失,無論你如何認錯,如何悔改,都一律嚴懲不貸;同時也因為愛,她每日都如臨大敵般地防犯著,隨時準備戰斗,事實也如此。總之,她不知道設身處地地去理解,不知道給對方空間,不知道給別人臺階……所以,她的所有防犯、維護和戰斗,最終往往都事與愿違、適得其反。這樣一來,愛最終都變成了恨,并難以釋懷,以至愛恨情仇連她自己也說不清了。
八
1953年9月26日,在美國紐約的一個藝術研討會上,會議中途,組會者突然宣布休會,并要求與會者為藝術大師徐悲鴻默哀3分鐘。于是參會人員全體肅立,會場鴉雀無聲。突然后排發出嗵地一聲,一個女人應聲暈倒在地。此人就是孫多慈。
此時孫多慈已離開徐悲鴻17年了,離她與徐悲鴻之間作出的那個“十年之約”,已過去了七年。
徐悲鴻與蔣碧薇分道揚鑣后自以為可以光明正大地與孫多慈在一起了,哪知道卻遭到了孫多慈父親孫傳瑗的極力反對,原因如前文所述,孫傳瑗不能認可徐悲鴻的人品。
1935年夏,孫多慈中央大學畢業,孫傳瑗隨即將孫多慈接回老家安慶,徐悲鴻多次前往安慶,并作過多方努力,但都沒能打開孫傳瑗這把鎖,以至于徐悲鴻無奈地說孫傳瑗“面貌似為吾前身之冤仇”。70多年過去后,孫多慈的表妹陸漢民還清楚地記得當年徐悲鴻來安慶與表姐孫多慈最后一次見面的情景。那次徐悲鴻托同是中央大學畢業的李家應去孫家通報,希望能讓孫多慈與他見上一面。可孫傳瑗一聽便將手上的筷子一扔,桌子一拍說:“絕不許進門!”最后在孫多慈母親的一再勸說下,并在孫多慈保證這是“最后一次”后,他才答應讓孫多慈去安慶當時的菱湖公園與徐悲鴻見面,并且還讓陸漢民跟著去“監視”。陸漢民看到,二人見面后幾乎沒有說話,只是抱頭痛哭。臨別時,徐悲鴻對陸漢民說:“小妹,你要記住,你的表姐永遠是最美麗的!”
表面上看起來,孫多慈的退出,只是因為她父親的反對,其實也并非如此簡單,更多的原因是此時的孫多慈對于自己的愛情、生活和人生,都多了許多理性的思考,她需要等待。許多年后,孫多慈在自己《孫多慈素描集》一書的“述學”中曾這樣寫道:
然后知吾父為吾講“動心忍性”之有因也。非此者,吾幾于不能自持。雖然中間“幾欲至疑孟子性善這章”。但最終還是從中受到啟發——悵然以悲,毅然以起,誓欲于虛偽、偏私、殘酷、險詐、猜忌、刻薄之中,求善求真求美。儻使風雨雷霆,供我馳驅,大海波濤,為我激蕩;宇宙之大,人情之變,融冶之洪爐也,將欲避其烈焰,突火而出,反身而觀,此至繁極賾不可思議之造物,令入我筆端,出我腕底,強使吾藝狀其博大,狀其雄奇,狀其沉郁,狀其壯麗,狀其高超,狀其秀曼。吾之意志,于以堅強;吾浩然之氣,至大至剛,與天地無終極,隨文運以旋轉者,蓋古往今來懷宏愿者之所以事事,終不以吾之小而抉棄也。人固可言其不知量,但吾所以答吾賢父母良師友殷切之期望者,固無他道,抑自定其為生涯者也。
其實那年安慶菱湖公園里并不是徐悲鴻與孫多慈的最后一次見面。1936年夏,孫多慈還特定從安慶來到南京一次,并與徐悲鴻訂下了一個“十年之約”:十年之內,他們互不通信,雙方各自奮斗,一切全憑天意,用孫多慈的話說就是“用十年的時間,你也有個了斷,我也有個結果”。
然而,哪里等得到十年啊?僅僅一年沒過,孫多慈便在父親的安排下嫁給了當時的浙江省教育廳廳長許紹棣。然而1938年8月,孫多慈又給徐悲鴻寫來一信,信中竟有這樣的話:“我后悔當日因為父母的反對,沒有勇氣和你結婚,但是我相信今生今世總會再看到我的悲鴻。”
然而孫多慈終究沒能再見到徐悲鴻。徐悲鴻1944年終于又遇到了另一位紅顏知己廖靜文,不久與她結婚,與她一起度過了人生最后八年的幸福時光。從此以后,孫多慈便成了只是夾在蔣碧薇與廖靜文之間一個不太引人關注的角色,甚至在蔣碧薇和廖靜文帶有傳記性質的回憶錄中,她們也不約而同地回避她——蔣碧薇是因為恨她而不愿意提她,因為在其看來,沒有她這個“小三”,或許徐悲鴻就不會與自己離婚;而廖靜文不愿意提她,是因為不愿意人們對她了解多了后會覺得自己原本只是她的替代。再加上孫多慈1948年又去了臺灣,任教于臺灣藝術學院,后任該院院長,從此再沒回過大陸,回過故鄉。就這樣,人們似乎便漸漸將她遺忘了,忘記了美術大師徐悲鴻的人生中曾有過如此重要的一個女人——從另兩個女人不約而同對她的態度即可反見出這一點。
然而任憑人們將她忘了,但是她怎么也忘不了徐悲鴻,也忘記不了過去的一切。雖然回不了大陸,但是她只是一有機會她便去美國,去見早年的老同學和好朋友吳健雄,并每次定去另一位畫家王少陵家,只因為他家里有一幅徐悲鴻當年寫給她的條幅,每一次孫多慈都要在這個條幅前默立許久,黯然神傷而又泣涕漣漣。條幅上的四句詩為:
急雨狂風勢不禁,放舟棄棹遷亭陰。
剝蓮認識中心苦,獨自沉沉味苦心。
1953年9月26日孫多慈在會場上當眾暈厥后醒來,當場宣布了她一個令人震驚決定:她將為徐悲鴻戴3年大孝,以表達對自己恩師的無限緬懷與尊敬,也表達對他們之間長達10年感情的無限追悔與追思。
1975年1月,一代才女孫多慈病逝于美國,終年63歲。
1988年,孫多慈的好友,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美國物理學會會長吳健雄,為參加東南大學校慶而回到南京,她除了參加一系列有關活動外,還來到了離校園不遠的傅厚崗6號的徐悲鴻故居,向陪同她的徐悲鴻女兒徐靜斐說出了孫多慈晚年為徐悲鴻所做的這一切。見故居前的幾棵大樹,她也說起當年孫多慈曾經送給徐悲鴻的那十棵楓樹苗,不禁唏噓,“樹亦如此,人何以堪”啊!也許當年孫多慈送那份楓樹苗的“大禮”時,所想到的詩句確實是最終被蔣碧薇猜破的那句,“曉來誰染霜林醉”,但是她卻忽視了此下句為:“總是離人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