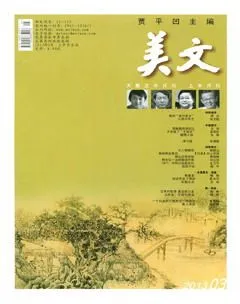轉在弘一法師圍墻外面
最早無意中走進弘一法師的精神世界,是在上世紀八十年代,電影《城南舊事》有一首插曲《送別》,記憶深刻。
長亭外,古道邊,芳草碧連天。晚風拂柳笛聲殘,夕陽山外山。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觚濁酒盡余歡,今宵別夢寒。
曲子舒緩婉轉,歌詞優美蘊藉,很有些宋代婉約詞的味道。那時還不知道詞作者是誰,也沒聽說過弘一法師的名字。后來讀書多了,方知,這首著名的歌詞竟出自一位大和尚之手——當然,那時弘一法師還未出家,他的名字還是李叔同。
弘一法師的一生極盡傳奇色彩,他的前半生與后半生反差之大完全判若兩人,令人深思其中不盡的人生況味。胡宅梵云:“綜觀大師之生平,十齡全學圣賢;十二歲至二十,頗類放誕不羈之狂士;二十至三十,力學風流儒雅之文人;三十以后,始漸復其初性焉。”此說不完全準確,但大體仿佛。
弘一法師出生于天津一個富足的鹽商之家。他的父親李世珍是富翁,也是清朝進士,68歲生下他,過了4年就撇他而去。雖然缺少父愛,但他并不缺乏錦衣玉食的生活,家資巨厚足以維持他悠游卒歲的少爺公子哥的習性。少年的李叔同到上海后,同一干文人往來酬酢,走馬章臺,廝磨金粉,秦樓楚館消遣,風塵場中寄情,還留下纏綿旖旎的風流詩詞。到日本留學期間,花錢大方,衣著考究,“高帽子,硬領、硬袖、燕尾服、史的克(即stick,手杖)、尖頭皮鞋,加之長身、高鼻,沒有腳的眼鏡架在鼻梁上,竟活像一個西洋人。”(豐子愷)為演話劇,他制一套戲服花一百多元,對一般普通留日學生來講,一百元相當于半年的生活費用。在日本,他還娶了一個日本妻子(在天津老家有妻俞氏,育三子),在家中雇有保姆,過著上層有錢人的生活。
弘一法師藝術興趣廣泛,善書畫,工詩詞,喜金石,能篆刻,在中國現代戲劇、油畫、音樂等多個方面,他都可謂開創者和先驅。晚弘一一歲的魯迅很喜歡法師書法,從日本朋友內山完造那里間接獲得“弘一上人”的一紙字,日記中用了一個“乞得”字樣,其恭敬態度由此可見。在日本期間,李叔同與歐陽玉倩等人成立了中國第一個話劇團“春柳社”,演出話劇《茶花女》《黑奴吁天錄》《熱淚》等,在《茶花女》中,李叔同扮演“茶花女”瑪格麗特,盈盈細腰,手可掬握,令人驚嘆莫名。回國之后在浙江第一師范任教,他教授的主要是音樂鋼琴課和美術課,這在當時都是開時代之先河的。著名文藝家豐子愷、曹聚仁、劉質平等都是他培養出來的高足。杭州西湖的湖光山色對李叔同的藝術氣息的熏染也非同小可,他經常在西湖中流連泛舟,在給一友的信中做了如此描述:山色如娥,花光如頰,溫風如酒,波紋如綾,才一舉手,不覺目酣神醉。山容水態,何異當年袁石公游湖風味!
李叔同年輕的時候,“異常的孤僻”,脾氣很各。歐陽玉倩記述了留日時期的一件事。一次,李叔同與歐陽約好八點鐘見面,歐陽住所距那里較遠,趕電車耽擱了些時間,到了后,遞上名片,不多時,李叔同開了樓窗,對歐陽說:“我們約的八點鐘,你過了五分鐘,我現在沒工夫了,下次再約吧。”歐陽知道李叔同的脾氣,只好掉頭走去。浙江師范的同事、一生好友夏丏尊回憶了一件事,學生宿舍丟了東西,作為舍監,夏丏尊十分苦惱,李叔同出主意,勸其貼布告以自殺逼小偷自首,但如果小偷不為所動,那只好真自殺“以死殉教育”,夏丏尊認為這招太狠,沒有接受。
李叔同年輕時候寫過一些慷慨壯麗、雄奇豪放的詩詞,如《滿江紅·民國肇造》:“皎皎昆侖,山頂月,有人長嘯。看囊底,寶刀如雪,恩仇多少?雙手裂開鼷鼠膽,寸金鑄出民權腦。算此生不負是男兒,頭顱好!荊軻墓,咸陽道;聶政死,尸骸暴。盡大江東去,余情還繞,魂魄化成精衛鳥,血花濺作紅心草。看從今,一擔好山河,英雄造!”這首詞填于1912年,距李叔同1918年出家僅有6年。
1918年,38歲的李叔同到杭州虎跑寺出家,一個月后在靈隱寺正式剃度。至1942年62歲圓寂,他的一生庶幾被平分成僧俗兩個世界,他也奇跡般創造了兩個高峰:現代中國文藝先驅李叔同和律宗一代宗師弘一大師。這,的確是一件令人不可思議的事情。
1918年,發生了什么事情?讓曾經的風流才子、曾經的公子少爺、曾經的豪放文人毅然斷然決然皈依佛門?我試圖在國內大背景和弘一法師的個人經歷中尋得一點蛛絲馬跡,但苦苦思索不可得,只好相信大師自己的自述,他有一篇《我在西湖出家的經過》,講述了出家的過程。這個過程是漸變的,不是突變的。究其故,大抵有如下幾個:1、深受馬一浮的影響。馬一浮,浙江紹興人,曾留學美日,飽讀詩書,學貫中西,是民國時期著名的國學大師,同時又是佛學家,自號“馬一佛”,他早年在上海與李叔同相識,在杭州交往頻繁,李叔同視其為精神導師。在佛學上,“漸有所悟”,遂“世味日淡,職務多荒”。2、“斷食”的因緣。1916年,李叔同在日本一本雜志上看到一篇關于“斷食”的文章,說“斷食”是身心“更新”的修養方法,自古宗教上的偉人如釋迦、耶穌都曾斷過食。因李叔同身體一直不好,患神經衰弱,肺結核,還咯血,所以,在這年年底,他跑到清幽之地虎跑寺斷食17天,虎跑寺后來成為他出家的地方,他自己也把此次斷食視作他出家的近因。1917年下半年,李叔同開始吃素,房間里有了佛經、佛像,天天燒香,過年他也沒回家,而是跑到虎跑寺過年。3、夏丏尊的“敦促”。夏丏尊與李叔同是一生的知交,友誼超乎尋常。1918年春節過后,李叔同皈依三寶,以演音為名,以弘一為號,原本打算以居士身份修行,寄住虎跑寺,暑假后辭去教職。夏丏尊見老友如此,心中寂寥,十分苦悶,有一天,對李叔同說:“這樣做居士究竟不徹底。索性做了和尚,倒爽快!”這原本是心中難過的性情之言,卻促使李叔同下了最后的決心。幾年后,在一個場合,李叔同指著夏丏尊對大家說:“我的出家,大半由于這位夏居士的助緣,此恩永不能忘!”
俗世中的人們往往私心揣度,遁入空門的出家人,肯定是在現實中遭遇重大變故或打擊,遂產生幻滅感,絕望感,看破紅塵,剃度出家,著名如賈寶玉者即如是。這樣的人確也所在多有,但不盡然,有些人完全是機緣巧合,一切隨緣,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有人把李叔同出家的原因歸于世事板蕩,時局混亂,中國知識分子在苦悶中尋求不到出路,精神頹唐,于是,醉心于青燈黃卷;有人歸于江南寺廟眾多,佛教氣息濃郁,儒家的修身與佛教的修行合二為一;……這些都是外在的情由,對于李叔同來說,絢爛之極歸于平淡,煙雨江南,歌榭樓臺,紅粉佳人,妻孥家人,都化作了“空”。當了和尚,對別人是“出家”,對他是“回家”,找到了最終的靈魂停泊地。李叔同的父親李世珍晚年信佛,曾撰一聯:“今日方知心是佛,前身安見我非僧。”這話應在兒子李叔同身上,其間似有微妙的因緣。
我在想,作為一個文人,而且曾是一個放誕不羈的文人,李叔同為什么不選擇禪宗,而選擇律宗?一般來講,禪宗講究頓悟,更適合文人修行,飯來即食,覺來即眠,自由度高,而且參禪、談禪也是件有趣的雅事。而李叔同選擇了戒律非常嚴格的律宗,說白了,就是選擇做苦行僧。律宗是佛教的一個派別,以研習和傳持戒律而得名,對僧人生活要求持戒嚴謹,不得稍有違越,因而修習甚難。他之所以選擇律宗,是因為,在他看來,近世所以佛門不昌,僧人不嚴格遵守戒律是一個重要原因。他認為,僧人的道德品行,應該在一般人之上,如果僅與一般人相當,甚至不如俗家人等,社會就難免對佛教徒的鄙視。因此,弘一法師精心研習,持戒甚嚴。他一直保持過午不食的戒律,俗界朋友請他吃飯也非常尊重他這個習慣。穿不過三衣,即使嚴冬也是如此,所以冬天他的手上經常生有凍瘡。
弘一法師有一張照片,穿著一身破舊的袈裟,頭上戴著帽子,眼神悲憫、慈祥,給我心靈以強烈的撞擊,有一種欲哭流淚的感覺,悲憫情懷油然而生。如果仔細看法師的照片,你會發現,他的衣服幾乎都很破舊。一次,他在南普陀寺給青年佛教徒做演講,第一條就是惜福,以他自己的衣著為例,一雙僧鞋穿了十五年還要穿,一把雨傘用了十三年還要用,一條毛巾用了五年還舍不得扔。在他過五十壽辰時,他的學生劉質平在他的房間細細數過他蚊帳上布縫紙糊的洞共有200多個。夏丏尊曾約弘一到白馬湖小住幾日,期間弘一的生活境界,讓這位老友慨嘆不已,“在他,世間竟沒有不好的東西,一切都好,小旅館好,統艙好,掛褡好,粉破的席子好,破舊的毛巾好,白菜好,菜菔好,咸苦的蔬菜好,跑路好,什么都有味,什么都了不得。”安泰、靜默、謙和,隨遇而安,構成了弘一一貫的生活態度。弘一不僅生活至簡至樸,而且對聲名地位更是淡如云煙,甚至視為累贅,對達官貴人避而遠之。一次去青島講律,青島市長晚間求見,弘一小聲叮囑他人說:“就說我已睡覺了。”第二天上午市長又來,弘一只寫了一張紙條送出去,還是不見。但弘一卻有一顆悲憫的菩薩心腸,他每次坐椅子都要將椅子顛一顛,唯恐上面有蟲子,不小心將蟲子壓死。為了宣講戒殺護生的教義,他與學生豐子愷合作——豐子愷繪畫,弘一撰文——出版了《護生畫集》,1929年上海開明書店出版。他經常去開元慈兒院、溫陵養老院、晉江平民救濟院等這樣的慈善機構,給他們說法,安慰他們孤苦的心靈。
弘一精研律宗,著述甚豐,代表作有《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記》《南山律在家備覽(略編)》等。研習律宗,苦持苦修,使他成為一位純粹的和尚,一位真正的僧人,一位德高道深僧俗兩界均高山仰止的大師。他被佛門弟子奉為律宗第十一代世祖。現代女子奇才張愛玲,一向清高自許,目下無塵,卻對弘一法師如此恭肅:“不要認為我是個高傲的人,我從來不是的,至少,在弘一法師寺院轉圍墻外面,我是如此的謙卑。”
1942年春天,郭沫若寫信請求弘一法書,弘一寫《寒山詩》相贈,詩云:“我心似明月,碧潭澄皎潔。無物堪比倫,教我如何說!”上款題“沫若居士澄覽”,郭沫若收到后復信致謝,稱弘一法師為“澄覽大師”。此詩寫作距法師圓寂還有幾個月時間,可以看做法師對自己一生的自我評價,明月皎潔,碧潭無塵,澄澈如許,光照后人。
1942年10月10日,弘一法師圓寂前三天,寫下人生最后四個字:“悲欣交集”,留下偈語般的人生總結,令人玩味不盡。葉圣陶對此解釋為:“悲見有情,欣證禪悅。”為眾生苦海無邊而悲,為修者回頭有岸而悅,有大慈悲,有大歡喜,“悲欣交集”,一切的人生滋味盡在其中了。10月31日,夏丏尊收到弘一法師的一封掛號信,里面是弘一法師的遺書,是兩則著名的偈語:
君子之交,其淡如水。執象而求,咫尺千里。
問余何適,廓爾亡言。華枝春滿,天心月圓。
何意?不可說,說不得。葉圣陶說:“此境勝美,亦質亦玄。”善哉。此時,只覺得有春風拂過,淡云梳過,清水滌過,花香熏過,明月照過,內心澄澈如一泓碧潭,無痕無塵。
豐子愷在弘一法師圓寂幾年后,在廈門佛學會做過一次《我與弘一法師》的講演,他把人生比喻成三層樓:“一是物質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靈魂生活。物質生活就是衣食,精神生活就是學術文藝,靈魂生活就是宗教。”“我們的弘一法師,是一層一層走上去的。弘一法師的‘人生欲’非常之強!他的做人,一定要做得徹底,他早年對母盡孝對妻子盡愛,安住在第一層中。中年專心研究藝術,發揮多方面的天才,便是遷居在二層樓了。強大的‘人生欲’不能使他滿足于二層樓,于是爬上三層樓,做和尚,修凈土,研戒律,這是當然的事,毫不足怪的。”在所有的人中,沒有誰比豐子愷更懂得他的老師了,他的這番話,是對弘一法師一生最好的詮釋。
劉江濱
1964年生,供職于燕趙都市報,高級編輯。河北作家協會理事,河北省散文藝術委員會副主任。著有隨筆集《書窗書影》,曾獲河北省第八屆文藝振興獎、第二屆中國報人散文獎等。散文《男人孟軻》被收入人民教育出版社版九年級語文教材,《理念的燈火》被編入中學語文試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