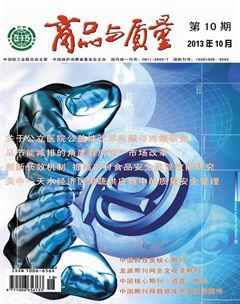論王陽明“致良知”學說及其價值
高原
【摘 要】本文探討了明代哲學家王陽明的“致良知”學說。全文共分四大部分,文章首先從“良知”這個范疇入手,考察了良知思想的歷史淵源。緊接著指出王陽明對孟子良知思想的繼承,在繼承前輩學者思想的基礎上,王陽明對“良知”范疇作了本體論改造,把“良知”和程朱理學所謂的“天理”等同起來。“致良知”學說是王陽明對儒家內圣外王成德立功之教的進一步發展,充分反映了陽明的人道情懷和救世精神,它不僅關注個體自我生命的道德實踐,而且更要推及于整個人類社會的精神實踐。
【關鍵詞】王陽明;良知;致良知;道德
一、“良知”說
要理解王陽明的“致良知”學說,首先有必要考察一下“良知”這個范疇。
(一)良知思想探微
“良知”這個范疇最早見于《孟子》,是孟子“性善論”的重要組成部分。孟子在《盡心上》中說:“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愛其親者,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也就是說,良知是指人的不依賴于環境、教育而自然具有的道德意識與道德情感。“不學”表示其先驗性,“不慮”表示其直覺性,“良”即兼此二者而言。[2]孟子的良知說是他性善論的核心。良知也就是人人生來都具有的一種善性。那良知具體表現在什么地方呢?孟子把良知的內涵具體化為“四心”。他在《告子上》中說:“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
(二)王陽明所理解的良知
王陽明在《傳習錄上》中說:“心自然會知,見父自然知孝,見兄自然知弟,見孺子入井自然知惻隱,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3]“自然”表示不承認良知是外在的東西的內化結果,而把良知看作是主體本有的內在的特征。可見王陽明繼承了孟子的良知說。
陽明作為一個關心時代、洞察社會民心的哲學家,他不可能只是單單繼承闡釋思孟學派的思想,在闡釋的過程中,王陽明更有自己的見地。
孟子論證性善的時候,不僅提出良知,而且提出“四端”,認為“四心”是“四德”的開端。而王陽明明確指出,“見孺子入井自然知惻隱,此便是良知,這就比孟子更明確地把良知與四端結合起來了。而且在良知和心的關系上,陽明認為:“良知者,心之本體,心之本體,即前所謂恒照者也。心之本體,無起無不起,雖妄念之發,而良知未嘗不在。”良知是心的本體,是心的“虛靈明覺”的狀態。本身不動的良知,在具體的道德實踐活動的過程之中體現為“理”,王陽明說,“吾心之良知,即所謂天理也。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王陽明的“天理”仍然是仁、義、禮、智等一套道德原則和規范,良知具有道德本源的性質。
王陽明明確指出良知是判斷是非的標準,是每個人先驗的是非準則。他在《全書》三中對陳九川說:“爾那一點良知,是爾自家底準則。爾意念著處,他是便知是,非便知非,更瞞他一些不得。”[4]在陽明看來,良知是人的內在的道德判斷與道德評價的體系,是一種判斷善惡的標準。就本體來說,良知是善,是人們心中最真切的一個準則,它以寂然不動的狀態對是非善惡做出直覺判斷。陽明還說“夫良知者即所謂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待學而有,不待慮而得者也”由此可見王陽明非常強調良知的內在性。
王陽明也強調良知的普遍性,認為良知對于每個人都是相同的,他說:“自圣人以至凡人,自一人之心以達四海之遠,自千古之前以至于萬代以后,無有不同,是良知也者,是所謂天下之大本也。”又說:“是非之心,知也,人皆有之。子無患其無知,惟患不肯知耳。”[5]因此,人并不需要到外部去尋找善惡是非的準則,這個準則是每個人所固有的完全相同的。
在王陽明的思想中,對于良知的規定體現著其思想的主體性精神:良知的先驗性和普遍性說明人人心中有一個至善的本體,它的自然發用表現為善的行為的展開,所以,行為的價值依據從外轉向了內。道德實踐和修養活動是良知作用和價值的具體體現,“致良知”成了必然要求。
二、“致良知”說的意義
(一)“致良知”說是儒家人性論的一大發展
中國經歷了漫長的封建社會,封建意識、封建倫理道德觀念根深蒂固,而等級觀念尤甚。孔子一方面強調人需要學習,承認自己不是“生而知之”者,提倡“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一方面又把人分成四種人。第一種是天生的圣人、賢者、上等人,其余都是學而后知的人,是愚者、下等人。孟子把上等人稱為勞心者,下等人稱為勞力者,他們的社會地位也就因而定了下來:“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這種長期形成的等級觀念壓抑自我意識覺醒。
王陽明先生所說的圣人則是泛指所有的人。不管是誰,只要按良知辦事,去人欲,存天理,就可以成為圣人,充分體現了王陽明先生對人的尊重,對張揚人性的渴望。王陽明高舉張揚人性的大旗,他的致良知學說無疑是對幾千年來的落后意識的挑戰,是在呼喚人性解放。他從不同角度來論述人心的功能,目的在于使人人都明白自己的存在價值,在社會實踐中發揮自己的智慧和才能,其意義已遠遠超過了一種嶄新的哲學理論的創建,而是意識形態領域里一次重大革命。尤其值得推崇的是王陽明先生非常注重踐履,反對空談,這就把理論研究和實踐緊密地聯系起來了,致良知學說乃至整個心學都有了生生不息的生命力。儒學的本質特征是實踐理性,尤其是經孟子發展、闡釋的儒學,其根本目的就是使人的道德修養漸趨完備,因此能否落實到踐履層面是衡量一個學人水平的標準。儒家的各種經典的目的在于教育、指導、說服人去這樣做,所以,也可以這樣去理解,經典、言說是手段,修德、實踐是目的。不過,在實際操作層面上,讀書解經卻成了成圣的主要甚至是唯一的手段了,實踐本身倒被放到次要方面。王學的立足點與出發點,就是王陽明終身痛切批判的“徒騰口說”的學風。陽明學最大的動機就是要糾正這種流于形式而不注重實踐的學風。
(二)“致良知”說對當代的實踐意義
王陽明致良知學說的提出有深刻的時代背景。我們現在也遇到了與王陽明時代相似的困惑。現時代是一個以知識過度膨脹而淹沒了價值理性的時代,以科技宰制世界,以強力統治世界的觀念以各種各樣滲透到各個方面,人的單向度的發展,忽視精神修養而引發的各種問題,正困擾著越來越多的人。
我們國家現在正處在一個社會轉型的重大時刻,大凡這種時候都存在著一個道德建設或重建的問題。馬克思主義認為社會道德不是孤立的、抽象的事物,它是有著一定的階級根源的體現特定階級利益的行為規范。這種規范很重要,它是社會生產生活得以順利進行和延續的有力保障。當社會存在發生一定的變化,經濟狀況有了發展,我們的道德觀念會隨之變化。然而這種變化是以新的經濟利益為導向而不自覺地體現出來的,其形態勢必表現為多層次性和不確定性。也就是說,不同的人有著不同的變化趨勢和適應度,然而作為社會道德的一般性而言,這種情況則可以被視為一種危機。進而引發的會是一系列的社會問題,可見我們能動地對我們的社會道德導向加以控制是應該的。這種控制導向的根據應該來自我們實踐的回饋,也就是那些社會上存在的不利于社會系統的各種問題。我們現在這個社會近些年來由于市場經濟的刺激,人們在追求經濟價值的同時很容易忽視道德理想的追求。在社會公共事務中則表現為責任心差。一方面熱衷空談道理,不去辦實事,吃不了苦;一方面表現為私欲太重,不給家國社會著想,不能從大局出發,往往惡變為貪污腐敗之徒。在這種情況下,光靠法制是不行的,而健全的良知是真正的法治能夠順利地良性運作的社會心理基礎。法的昌明要求社會活動主體形成與法治的精神實質相一致的、基于法律并以對法律的忠誠為核心的法治良知。法治的推行必須以個人、社會和國家、政府這些基本的社會活動主體具備起碼的良知為前提條件與人格保障。但是,呼喚人的良知,要求人的自律精神只是一方面,實質上這種呼喚還是乏力的,因為這無疑于是用外在的道德規則來要求內在道德的渴望,其本質還是外在的道德要求。
“致良知”的提出,不僅是王陽明本人思想的成熟形態,也是宋明時期心學思潮發展的高峰。“致良知”包含兩方面的含義:一方面是從“本體”到“發用”的擴充過程,另一方面是克除私欲,復歸良知本體的過程。前者側重道德實踐過程,后者側重于道德修養活動。“致良知”強調了“致”的工夫論和“良知”是本體論,“致良知”既突出了修身工夫的地位,又能在工夫中追溯本體存在。王陽明“致良知”的思想要點正在于:一、“致良知”就是良知本體的自我呈現。王陽明認為,每一個人都具有內在的良知,而良知的內容就是仁義禮智的天理,每一個人必須首先認識到這一點。二、“致良知”就是將自我發現擴充的良知貫徹到自己的行為實踐中去。王陽明認為,真正的“知”、“良知”都不是純觀念上的,而必須體現在行為實踐中,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所以他特別強調知行合一。王陽明的思想對當今仍有借鑒意義,尤其是他“致良知”的勇于實踐和道德自律的要求,引發個人對自身道德踐行和職責的深刻反思。
參考文獻:
[1]肖萐父、李錦全.中國哲學史(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312.
[2]陳來.有無之境—王陽明哲學的精神[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66.
[3]王陽明.王陽明全集傳習錄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39.
[4]王陽明. 王陽明全集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74.
[5]王陽明. 王陽明全集八書朱守諧卷[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141.
[6]王陽明. 王陽明全集年譜一卷三十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215.
[7]黃宗羲.姚江學案明儒學案卷十[M]. 北京:中華書局,1985.176.
[8]朱熹.格物補傳大學章句四書章句集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6.
[9]張學智.從人生境界到生態意識—王陽明“良知上自然的條理”論[J].天津社會科學.200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