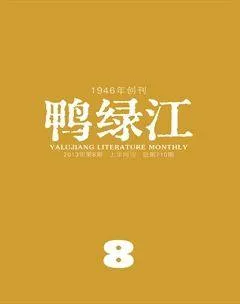李皓組詩(附:創作談)
李 皓,中國作家協會會員,1970年生于大連普蘭店,1989年入伍,1999年進入大連晚報社,2010年任大連《海燕》文學月刊社主編。1987年開始寫詩,曾獲“蓓蕾杯”全國中學生詩歌大獎賽一等獎、詩刊社“雷鋒杯”全國新詩大賽三等獎、“雷鋒——道德的豐碑”全國詩歌大賽二等獎等獎項。曾在《解放軍報》《解放軍文藝》《詩神》等報刊發表散文、詩歌作品,多篇作品入選多種年選。
回父母家吃飯
我的父母住在鄉下,如果開車
回一趟父母家,需要個把小時的
車程。個把小時,父親總共
來過三遍電話
第一遍電話打進來的時候,車子
剛經過開發區。我們一家三口正在
爭論日新月異的被新區合并了的
開發區還叫不叫開發區,父親說
你們開的什么車,真慢!
第二遍電話打進來的時候,我正在
打量著車窗外的玉米、大豆、高粱
還有翻滾著金黃色稻浪的水稻
女兒不屑一顧我對莊稼的認知
父親在電話那頭說,哦!快了
父親打來第三遍電話的時候
我望見由遠及近的收費站一陣竊喜
這個節日高速公路免費通行
讓隨著油表一起下沉的心,有些許
扭曲的安慰。爸,馬上到家
在小鎮電業家屬樓樓下停車的時候
爸爸準時出現在一門洞的出口
像提前有預感似的。爸爸嘟噥著
怎么這么晚才回來?你媽早把
飯菜準備好了,有的都涼了
其實飯菜根本沒涼,那一桌飯菜
把母親忙得夠嗆。父親對于快與慢
涼與熱的定義,總是讓人匪夷所思
但我始終堅信他有他的道理
就像一群大雁從我們頭上飛過
根本不需要,任何借口和理由
母親很享受我們的風卷殘云
個把小時,我們就把父母家搞得
杯盤狼藉。一個個抹著油膩的嘴巴
我說媽,今天的飯菜咸淡正好
母親說,好吃,你們就再多吃點兒
個把小時,我們吃得很快
沒怎么喝酒,只嘮了點兒家常
然后拍拍屁股就準備走人,驅車
個把小時,回到沒有父親母親的
城里,沒有莊稼撩人的城里
父親母親沒有計較這個把小時
兒子足足走了大半個年頭
他們知道,兒子很忙碌飯局很多
以至于大半個年頭沒回鄉下
回來,也就待上個把小時
下樓時我們執意不讓父母下樓
父母在門里,我們在門外
父親說回去的路上慢點兒開車
我說爸,你別擔心也就個把小時
轉過身去我就覺得芒刺在背
高速公路上的車都是風馳電掣
但我清醒地知道,自己尚不及一根
干枯的稻草更有力量。我咀嚼著
殘留在嘴邊的飯粒,我的淚水
都已掉進酒杯
父母健在,明鏡高堂
個把小時回父母家吃一頓飯
吃多吃少、吃快吃慢都不重要
只是守候與駐留的時間要慢下來
慢得我們從不曾認為自己的父母
正在慢慢變老
創可貼
必須有傷口,一個不大不小的傷口
一個創可貼恰好覆蓋的傷口
這樣就有了借口,一個恰如其分的借口
一個堂而皇之的借口
買藥,買幾貼謂之創可貼的膏藥
為你刮骨療傷,解去心頭之痛
我絲毫不想掩飾對你的欽慕
打認識之日起,我就把你視為己有
據說也有人宣示過對你的主權
但我不在乎,我有我的霸道
是我的就是我的,我是個男人
對于心愛的女人,我是天然的保護傘
即使有秋夜的冷雨,將傷口浸泡得
四周泛白,創可貼欲蓋彌彰
好吧愛人,對于你的傷口
我永遠都是一味守候千年的藥
女兒的電話
女兒打來電話,報了一聲平安
我的心,才在平靜中安頓下來
女兒拎著的兩個包裹像兩枚石子
一枚擊中秋水,一枚擊中了我的心
千重浪花在為父的胸中掀起波瀾
每一朵都叫惦念,每一朵都叫牽掛
能讓秋水復歸于平靜的,只需要
一個電話,大聲報一個平安
親情的漣漪在秋風中蕩漾開去
誰也無法阻止兒女一天天長大
我看見窗前的銀杏葉在悄悄泛黃
我想象豐收的田野顆粒歸倉
我看見拎著包裹的女兒,平靜地
走向輕軌車站潮水般的人海
石子的回聲,在輕軌經過的地方
把叮嚀和囑托鋪張得越來越遠
這個秋天,我的心開始在一棵樹
會說話的枝頭上抖動,或者等待
燒水
一根木柴噙住了火苗
火苗從一根木柴爬上另一根木柴
兩根木柴就開始用火苗
相互取暖
只有一根木柴進入另一根
木柴的時候,爐中的火
才會燒得更旺。焚毀乃至融化
才是生活的高潮
壺蓋發出的愜意的聲響
一定是燒熱的水在呼喊
那些不曾被燒過的水
冷靜中蘊含著無法預想的狂熱
附:
創作談
——詩歌與命運
我是一個用詩歌這種體裁寫作的人,而不是嚴格意義上的詩人。我對詩人這個稱呼有著近乎偏執的理解,絕不是發表了一些詩歌作品或者出版了幾本詩集,就可以稱其為詩人。
竊以為,真正意義上的詩人,就應該是那種像詩一樣生活著的人:他敏感、激情、豪放,不與一切世俗為伍;他蔑視金錢、權力,重情重義,仗義執言,不向權貴低頭,不為五斗米折腰;他純凈如一汪秋水,純粹如一縷清風;他表面平靜如水,內心波瀾壯闊;他吃的是草,擠出的是奶——他平凡如草,但仙風道骨,他從平常事物中間找出閃光的語辭,向人類提供源源不斷的精神食糧……我可能這輩子只能作為一個寫詩的人存在于蕓蕓眾生,對于“詩人”的桂冠,我只能永遠心存敬畏。好在,我一直在路上;對于詩歌,我從未遠離。
如果我不愛上詩歌寫作,或許我人生的旅途會平順許多。但是,人生的詭譎,叫作鬼使神差也好,叫作陰差陽錯也好,使得我的命運發生了很大改變。很多東西個中滋味,實在是無法言說。
1988年春,我的處女作《男生宿舍》在“蓓蕾杯”全國中學生詩歌大獎賽中獲得一等獎。1989年3月,我報名參軍。接兵團副團長李艷國得知我的情況后,爽快地簽了字:考慮此人的才能,予以接收,決不退兵!這段簽字至今還保存在我的檔案里。1989年底,我被分配到沈空機關。
沈空機關是個人才濟濟的地方,我耳熟能詳的大概就是政治部創作組著名軍旅詩人李松濤了,又是通過姜鳳清老師的推薦介紹,我成了李松濤的弟子。認識了松濤老師,可以說就認識了半個中國詩壇。
1991年9月,我考入位于江蘇徐州的空軍勤務學院航空油料系。然而,由于一位詩友創辦的詩社出了一點麻煩,我牽扯其中,當一名空軍軍官的夢想,隨著那陣冷風而消散了。我只能無言以對。愛和愛好,同樣都是需要付出代價的。
1994年我進入普蘭店經濟開發區管委會做秘書工作,其間,我娶妻、生女,生活談不上清苦,但絕不富有。精神生活倒是寬綽得多,寫作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
我最終能在大連晚報社落腳,也與詩歌創作有關。倏忽間,我在晚報工作了十個年頭。十年,我寫了大概不到十首詩。我時常在無人的夜里懷念起詩意的軍旅,就無法不想起李松濤,我一度那么執著地想模仿他的人生,但是啊,人生是不可以復制的,我只能聽從命運的召喚:我學得了他的語言,卻學不到他的深邃;我學得了他的靈性,卻學不到他的睿智;我學得了他的憂患,卻學不到他的風骨——四十歲的李松濤已經聲名遠播,而四十歲的我才剛剛開始。
或許詩歌帶給人的除了心靈的撫慰之外,還能夠改變人的性格。我一直在琢磨自己性格中的率性、天真、不圓滑、不設防、喜怒形于色等等,是不是詩歌帶給我的,還是我天生就有著詩人一樣的悲劇性格?它與詩人的靈性是相克相生的嗎?
2010年12月,我被任命為大連《海燕》文學月刊主編。我重又端起寫詩的筆,不為別的,只為了記錄下命運那無法捉摸的點點滴滴,僅此而已。
附:李皓詩歌評論
“我在”詩情與生命意志的兩全
蘆葦岸
在詩人的寫作動機中,往往難有類似定律一樣的確定性,但作為藝術門類之一域,詩歌的作用或許真如奧克塔維奧·帕斯所言的為人類提供了“相互辨認”的可能,這種“隱蔽的整體的形象”在很多場景下確實讓詩人著迷。比如我要論述的李皓的詩歌。李皓顯然在不停地被詩意推動著前行,哪怕亦步亦趨。這種無悔的執著姿態,具有旗幟般的隱喻功能——被蕓蕓眾生辨認,亦有笛卡兒的“我思故我在”的冷靜與激情。作為一個浸淫詩歌數十年的北方漢子,這種“我在”的詩意情懷甚至帶有內視的色彩。通讀他的詩歌,能強烈地感觸他那打開自我的堅定態度,以及對生命意志的持衡之心。
李皓的詩歌創作始于20世紀80年代的中學時期,成年后,豐厚的閱歷和生活的寬度鑄就了他更為靈動、細膩、多情的詩心,他的文學之路越發沉穩、深遠。細讀他的作品,對照他的生活軌跡,不難發現他是一個內心力道異常堅毅的人,他的詩歌道出了他對生活的敬畏,對世道人心的問診,對山川大地的膜拜,對自然物理的親近,對親情大愛的恒常頌贊。
一、沉靜的生活疼痛與故鄉情結的詩意融會
常年輾轉各地使得李皓背負的心靈痛楚日日深重,解讀人生的異數更通透,加之詩人本身敏銳細微的洞察力,對日常生活細節賦予哲學與美學的反復思辨,成就了他詩作最明顯的個性標簽,尤其比照閱讀了幾組他不同時期的詩,更是驚喜他傳遞的聲音的純粹、豐盈。
對于詩人而言,經歷繁雜會改寫詩歌悲喜的格局,事實是不少人沉溺生活的洪流中,往往一蹶不振,沉疴不起,無法完成心靈的自救,但也有人踏平坎坷成大道,視其為孕育詩歌的肥沃土壤,這種游刃有余的人氣場超強,能在光怪陸離中獨守一份安寧,只留清氣滿乾坤。從這個意義層面考量,李皓是過硬的,他的詩心成全了他的堅韌。游走在城市各地,他的詩隱透著對生活沉靜的痛,又因為他擅長以細膩度量生活,所以能自覺放下身架,褪去清高的外衣,以謙恭的視覺投影和心智過濾對待所目擊的一切。但又區別于普通的寫實主義,不是零星地再現生活圖景,他擅長以“插科打諢”的旁觀者方式,理性探視生活和人性的不同面,配之以特有的性靈觸覺揭示事物(現象)的內在本質,甚至以互為悖謬或矛盾的心態反轉將內心的沉淀激活,進而勾連人生百味。這種由表及里的敘寫思維所形成的巨大反差能引發閱讀共鳴,并促使讀者進入冷靜的思考。
在《我得坐車去一趟普蘭店》里,多重敘述性意象構成生活里各種矛盾心情的沖突。“在東北師大讀研時,我是遼寧人/在鞍山沈陽當兵時,我是大連人/在大連做記者時,我是普蘭店人/在普蘭店工作時我是磨盤鄉人。”全詩在不間斷的矛盾轉換中透出蕪雜人生的詩性真實,產生了一種冷靜的硬度,似乎在作者的內心,再光鮮的身份后也總拖著卑微的影子。此詩讓我不由想起雷平陽的那首悲憫的《親人》,率真、務實,李皓也一樣,在極力讓詩歌剔除雜質,直接道出心跡,體現的是作者的謙卑與擔當,當然更是對“詩人”身份的再確認,以及對自我靈魂的清晰辨認與體察。
而就詩的語言來說,他將赤裸裸的犀利的批判巧妙化為冷幽默式的自嘲。正如楊克所言,“一個詩人盡可以以丑角的面孔出現,但這種幽默滑稽的方式所傳達的是平民的智慧和力量,而不應只展現人格的猥瑣”。這一點李皓做到了,他對生活形態的書寫也明顯有別于傳統主流意識形態,透過許多自我嘲弄,反射出現實生活的陰郁,和勾畫出一部分人人格的卑劣。那些自以為是上等人的下等人,打腫臉充當起來的“假胖子”,整日鉆營溜須拍馬的諂媚嘴臉才是他真正想唾棄,不愿同流合污的原因。所以在他的詩中,反語和調侃形成的巨大思維聯想是一大亮點。“詩是人格創造的表現”(郭沫若語),李皓勤勉為詩,一切盡在五味雜陳的痛中。
二、人性真實與日常詩化的提純
在消費時代的當下,物質文化對人文精神的沖擊不可小覷。李皓擯棄世人皆醉我獨醒的“圣人”姿態,在描摹日常生活的詩歌中努力構建“包容開放,靈動大氣”的詩風,將批判、理解與融入合為一體,旨在傳達良知,啟示真理。而要將鮮活的人性鑿刻在日常生活的年輪里談何容易?李皓在鍛造語言內在的氣度和智慧上花了不少力氣。
“父母健在,明鏡高堂/個把小時回父母家吃一頓飯/吃多吃少,吃快吃慢都不重要/只是守候與駐留的時間要慢下來/慢得我們從不曾認為自己的父母/正在慢慢變老。”在《回父母家吃飯》一詩中,父親的三次催促傳遞了日漸年邁的雙親渴望子女回家團圓的樸素愿望。“母親很享受我們的風卷殘云……”他的父母從不會計較半年的守候、幾天的準備、一整天的滿心期待換來的只是半小時的天倫。為人父母給予兒女的牽掛總是這么細膩綿長,這份人性的真實借幾個時間詞的對比著實讓人備感溫暖。而人性的繁復猶如鉆石的多個切面。
在描寫男女情感時,李皓又成功轉身化為一張熾熱而溫柔的“創可貼”。在《創可貼》中,他更熱衷獨辟蹊徑,通過捕捉事物表面的差異來揭示其本質的一致。“我絲毫不想掩飾對你的傾慕/打認識之日起,我就把你視為己有/據說也有人宣誓過對你的主權/但我不在乎,我有我的霸道/……/好吧愛人,對于你的傷口/我永遠是一味守候千年的藥。”這種愛與哲思通融的打開是無限的,這個“藥”的意象,堪比舒婷筆下的“木棉”,十分經典。
一張不起眼兒的創可貼卻能在情傷時掩飾虛弱和難堪。這樣的類比取象令人耳目一新,在描繪愛情的詩歌中我們習慣了花好月圓、花前月下,寄寓相思的紅豆與鳥雀。他卻將一張創可貼和一個男人對女人熾熱執著的愛黏連在一塊兒。這陌生化的搭配讓詩歌豁然開朗,詩意沛然。親情或是愛情,人性的真實投射到生活的激流里就是一個個光怪陸離的斑駁的影子,時而模糊,時而真切。
讀李皓的這部分詩歌,腦海里總浮現出明代散文家歸有光的神韻。“生命中會有多少變故,搬家/何嘗不是一場別離。當平日疏忽得/幾乎認為不存在的大包小裹/重新塞滿又一個空間,那放不下的/豈止是一只飯碗,兩雙筷子?”(《搬家》)日常瑣事的碎片一旦被詩歌照亮,就會生成無限的感動,也會為生活多了這樣的人文深情而備感美好。寫出名詩《假如生活欺騙了你》的普希金說過要“用詩歌喚起人們善良的感情”,李皓覺得這份情懷在物欲橫流的今天是多么寶貴,因詩而見李皓也有著別林斯基評價普希金的“天性”——他的內心有著許多赤子似的和善、溫良和柔順的成分,感情中永遠有一些特別高貴的、溫和的、柔情的、馥郁的、優雅的東西。
“我看見拎著包裹的女兒,平靜地/走向輕軌車站潮水般的人海//石子的回聲,在輕軌經過的地方/把叮嚀和囑托鋪張得越來越遠//這個秋天,我的心開始在一棵樹/會說話的枝頭上抖動,或者等待。”(《女兒的電話》)平白舒緩的敘述,娓娓道來,親切動人,“我的心開始在一棵樹”這樣的沖動,已經隨著閱讀的深入移植到了每一個父親的靈魂深處。這份“等待”是李皓提純日常詩意的一個典型案例,占了他詩歌的很大比重,不贅言。
三、生命幽微的異境呈現與醇厚的心靈映照
大城市的喧囂并未沖淡李皓對詩歌的熱情,反倒促使他理性思量,砥礪生命幽微的意境,這期間,他寫下大量批判現實主義的詩篇。更值得欣喜的是,他在冷靜觀察社會萬象后能清醒地正視社會沿革的產物——對欲望的癡迷。所以,他的文字一以貫之地將丑陋的人性幻化成波瀾不驚的調侃式幽默,劍指人心的黑色風暴,達到驚人的效果。
有的時候,堅硬的文字也有柔軟一面。出于知識分子的人道主義同情,關注底層自然成為他詩歌內容的另一組成部分。《落葉》中的作者將卑微的小人物意象化為凋零的枯葉。“人生一世,你的舞蹈,不比一枚落葉更加輕盈/把喘息留在枝頭/把嘆息伸進泥土……”在生活這個沉重的命題前,人只能是一張落葉,無可避免地經歷萌芽、繁茂、枯萎直至凋零的自然循環。小人物注定有小人物的卑微。即便落葉終需歸根也不必沮喪,迎著花開的季節,努力綻放,自由地吮吸生活給予我們的一切美好,成就自己斑斕的春天,也不枉白白走一遭!在看似蕭瑟的文字里卻又包含對生命的竭誠的贊美,大有枯木逢春的驚喜與感動!
“其實這個秋天,早已/深入我的內心,我的每一寸/肌膚。你卻視而不見//含淚的紅,是我中年的傷/這一季/鳥兒已飛過。”(《蘋果獨語》)但凡文字折射出的鏡像,均是因為有一雙善于發現并且有思辨性的眼睛。李皓在生命與文字中潛心打造精神殿堂,在生活與心靈的激蕩中探索人性的微妙;又憑借對生活細膩虔誠的關注,在一個個詩意的鏡頭里任由思維的浪潮肆虐沖撞,然后將一切激情凝聚成富有張力的文字,呈現出或熱情、或謙卑、或醇釅、或知性的詩意景觀。超拔的精神正行走與在潛心修為的詩情表明,李皓是一個與時代脈絡一起搏動的詩人,并因此而找到了自己的另一個更為真實的身份!
蘆葦岸,1989年開始公開發表作品,迄今已在《人民文學》《詩刊》《詩林》等數十家文學刊物發表詩歌、小說、散文、評論近百萬字。1999年12月出版詩集《藍色氛圍》。有作品入選《星星詩刊甲申風暴大展》《70后詩歌檔案》《浙江詩典》等選本,多次獲獎。
責任編輯 林 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