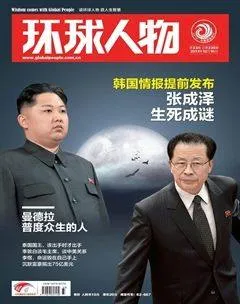學者潘毅,為農民工打工


人物簡介
潘毅,1970年出生在汕頭。1992年本科畢業于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1994年碩士畢業于香港大學社會科學系,1998年獲得倫敦大學人類學博士學位。現為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教授,著有《中國女工》、《大工地》、《我在富士康》、《煤礦工人調研報告》等書。
12月3日,一個晴朗的下午,環球人物雜志記者見到了潘毅——這位社會學家瘦小卻透著一股堅毅的力量,T恤衫、不施粉黛,似乎隨時準備出發。潘毅這次到廣州是參加“中國職業安全健康回顧與展望研討會暨致麗火災二十周年紀念會議”。1993年11月19日深圳致麗工廠發生大火,導致87名工人喪生。這一或許早被人忘卻的事件,不但催生了《勞動法》,也讓潘毅從此將個人的關注點對準了底層工人。20年里,女工、建筑工人、塵肺病、富士康、煤礦工人……相繼出現在她的視線。在做調查的過程中,她睡農家的泥土地、像礦工一樣灰頭土臉,和建筑工人一起吃兩元錢的盒飯。
與其他學者不同,潘毅調研的目的不是出成果,而是改變現實。作為香港理工大學教授,她沒招過一個香港學生,她的學生都來自內地。因為對學生,她有一個苛刻的要求:不允許他們畢業后待在高校,而是去當基層干部、辦民間公益組織。這種死磕的精神、接地氣的生活,讓潘毅成了學術界一朵“奇葩”。
不知道這本書寫給誰看
21歲的曉明躺在病床上,除了一張臉,全身被嚴重燒傷。她看上去十分虛弱,一雙明亮而純真的眼睛卻非常平靜。病房外,她的父親焦慮地來回走著。1993年致麗大火后,當時正在香港中文大學讀歷史的潘毅跟隨社團前去探望被燒傷的工人,曉明是其中之一,她剛從湖北農村老家出來打工不久。
如今說起20年前病房里的那一幕,潘毅依舊感到震撼。“我之后做的研究,我對民工生存狀況的關注,其實都離不開我早期去探訪曉明留下來的記憶。”
1995年,潘毅以工人的身份,到深圳一家工廠打工,花了一年多時間與打工妹同吃同住,跟著她們探親訪友、回鄉過年,也看著她們苦苦掙扎。打工妹也愿意接納這個普通話說得不標準但很誠懇的朋友,當她們遇到人生困惑時,她會是最好的聽眾;當她們思念親人時,她會陪著她們一起沉默;她們也不介意與她分享日記。
在完成調研后,潘毅做了兩件事:一是在深圳成立“女工服務中心”,即現在“女工關懷”的前身;二是寫了一本書,《中國女工》。2005年,該書獲得有“社會學奧斯卡”之稱的米爾斯獎最佳書籍獎,潘毅也成為該獎項1964年成立以來第一位獲獎的亞洲學者。
如今不管是學界還是公眾,提到潘毅,通常就會提到這本成名作。但在她本人看來,這本書極不成功,因為“不知道寫給誰看,女工們根本看不懂”。所以這本1997年就完成的書被她束之高閣,直到需要參評學校終身聘用資格時才拿出來發表。“現在我的目標很清晰,所有書都是寫給大眾看的,我希望農民工都能看懂我的書。”
他們的聲音很少有人聽到
9歲時,潘毅跟隨父母從汕頭搬到香港。那個時候,汕頭與香港是兩個不同的世界,這種地域轉換帶來的心理沖擊,讓小小的她體會到一種興奮和不適,“就像女工們初次進城”。大學時,她選擇讀歷史,就是想從歷史的角度去理解現實。但很快她發現這并不能讓她更好地認識社會,于是,讀碩士時她改選了社會學,并開始了一系列民工調查。
從第一本研究女工問題的《中國女工》到考察建筑工生存境遇的《大工地》,從研究大型企業集團勞工狀況的《我在富士康》,到今年遠赴東北雙鴨山所做的《煤礦工人調研報告》,潘毅告訴記者,她沒有刻意挑選研究對象,只是緊跟當下的熱點問題。“2008年興辦奧運,我開始把目光投向了修建鳥巢等各種場館的建筑工人。2010年,富士康爆發‘九連跳’,我就想去看看那里工人們的生存狀態到底是怎樣的。”
潘毅最常用的調查方式是跟工人一起工作,直接卻有效。“大部分工人可能永遠也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不明白社會研究意味著什么,他們把我想象成一個專門寫打工者真實生活的小說家。”潘毅告訴記者:“工人們一直處在失語的境地,盡管他們要的不多,但他們的聲音很少有人聽到。我有一種使命感,把他們真實的生存狀態記錄下來。”
正是這份悲憫之心,讓潘毅異乎尋常地執著。就像如今,富士康的新聞熱度已經過去了,她和學生們仍活躍在富士康工廠周圍:調查、監督,為工人提供服務、做培訓。“自從涉足農民工的研究,這個群體的問題就一直纏繞著我,我無法停下來。”潘毅如是說。
看到別人的痛苦卻離開,讓她很內疚
環球人物雜志:您從事打工者研究20年了。和20年前比,現在打工者的境遇有什么變化?
潘毅:現在積累了更多問題。上世紀90年代工人一個月拿200多元,和公務員差不太多。20年后,他們賺的錢只夠城市基本生活。而且,由于城市和農村的生活水平進一步拉大,雖然表面上看新生代農民工的工資多了,生活條件也提高了,可是他們內心累積的不滿和焦慮也在增加。正是因為期望與現實落差更大了,所以才會出現很多極端現象,比如富士康的跳樓事件。
好的一點是,現在工人的權利意識比原來提高了。比如說女工吧,早期的女工遭到性騷擾都不敢講。肚子被搞大了,回家還被父母打。但現在不一樣,很多女工會公開講述自己的遭遇,這是一個巨大的進步。
環球人物雜志:經濟收入可能只是衡量打工者境遇的指標之一,您認為他們面臨的主要困境是什么?
潘毅:最主要的是農民工無法留在城市,可是又沒法回農村了。隨著農村土地的流失,即便他們回到農村也失去了謀生手段。很多我們研究的情形就是,農民工本來想回鄉發展,但是收入太低、沒有保障,只能跑回城市生活,可目前城市的發展模式又不可能把他們長期留下來。今天農民工的問題比以往更加嚴峻,就是因為一代比一代更清楚,城市很難容納他們;而他們想要在城市生活的欲望又比上一代更加強烈。
環球人物雜志:有人認為這是發展中的必然。
潘毅:有不少學者甚至是官員們認為,現在的種種問題只是“陣痛”,是因為市場經濟還不成熟、監管不力,如果繼續開放市場,問題就解決了。然而,事實并非如此。
環球人物雜志:在您看來,該如何保障工人的權利?提供更好的福利?
潘毅:第一步,在企業成立工會。今天我們選出的代表大多是企業家,工人缺乏真正能代表他們的人,缺乏話語平臺,沒有自我保護能力,而社會對他們的保護也很不夠。另外,國家應當制定政策、投入資源,讓農民工有可能在城市里長期生活。當然,現實情況是我們國家人口太多,國家沒有那么大的財力來實現國家層面的福利覆蓋,所以,把社會福利都壓在國家身上是不可能的。歐洲的社會福利國家已經大量欠債,這也告訴我們,這種模式是走不通的。我的建議是調整模式,用社會經濟的方式來搞企業,就像當年的“單位”來統籌福利,考慮醫療和教育等問題。
環球人物雜志:您的研究對象都是最普通的勞工,您也一直強調要改變現實,但作為學者是否有很大的局限性?
潘毅:我的個人生活比較簡單,除了看書和音樂,沒有其他追求。但就像你說的,有時我會感到很內疚,接受不了自己作為一個研究者,看到了別人的痛苦,卻只是完成自己的研究,然后離開。所以我現在做了一些努力,比如我現在的書或者研究的問題可能更接地氣了。同時,我也努力去培養一批學生,讓他們跟底層社會接觸、對話,去分析問題、解決問題。我想作為一名研究者,關鍵在于你會不會為這個群體尋找出路——光呈現現象,是不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