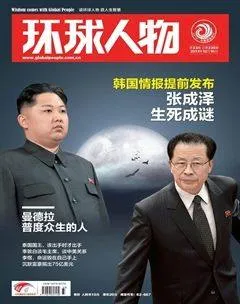充滿爭議的史景遷

費正清之后的西方漢學家里,史景遷頗有聲名。這不僅是因為他的個人魅力:典型的英國紳士,溫文爾雅,長相如肖恩·康納利,更因為他著作頗豐,10多部關于中國歷史的學術作品每每能以“講故事”的方式贏得讀者的心。不久前,史景遷的《大汗之國:西方人眼中的中國》簡體中文版面世。和他的其它著作一樣,此書具有可讀性,呈現了自13世紀起,700余年間有關中國的48種文本,旨在描述西方人“觀測”中國的觀念史。史景遷認為,西方人對中國的濃厚興趣,“明確道出了這個國家所散發的魅力。”
史景遷的英文名叫喬納森·斯賓塞,由于對司馬遷的景仰,他給自己起名“史景遷”。作為一名1936年出生在英格蘭、如今任職于耶魯大學的中國研究者,史景遷對我們這個東方古國有著近乎癡迷的熱愛。他在耶魯大學開設的中國近現代史是全校最叫座的課程之一,每次總有三四百人選課。同時,他對中國的觀照點也頗為獨特,他能埋首故紙堆找資料;也能從世界格局來看中國歷史。他能以地方志、文人筆記和小說作為材料,對清代初期山東農村一個婦人的生死做出立體描繪;也能以第一人稱為視角,將康熙皇帝日常的政治生活及心態進行復原。
不過,史景遷的學術研究也受到非議與質疑。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說法,就是認為他無法直接閱讀中文材料。從史景遷的學術經歷來看,此種說法并非實情。他求學期間曾學習中文,后來為提高中文水平專赴臺灣進修。他自己曾表示,中文材料比較難讀,不過這更多是指史料所蘊含的信息與意義,而非一般的閱讀障礙。
另一個有關他的學術非議就是他很少使用歷史學專業詞匯,這與美國漢學界的一貫風格迥異。事實上,這應該屬于史景遷個人的學術取向,而非欠缺專業素養。在耶魯大學求學期間,他師從芮瑪麗——費正清最青睞和倚重的學生之一。有這樣的名師,史景遷的素養不會差到哪里去。
還有人批評他的作品“作為歷史文章缺乏分析與論證”。據說,錢鍾書當年訪問耶魯時,曾在私下戲稱史景遷為“失敗的小說家”。美國匹茲堡大學教授許倬云也曾形容史景遷:給他一本電話簿,他可以從第一頁的人名開始編故事,編到最后一個人名。臺灣學者汪榮祖同樣認為史景遷的寫作技巧高超而史學修養不足。但在史景遷本人看來,正是因為中國史料本身有著明顯的敘事性,他才選擇了這種表述方式。
研究中國歷史半生,史景遷對中國近代史的開端時間有著與中國史學界不同的看法。他曾說:“我發現中國人編的課本有一個缺陷,當他們講述中國近代歷史的時候,總是從19世紀中國受的屈辱和侵略開始切入。而我認為,如果要更好地研究中國近代史,我們應該從17、18世紀的中國開始研究,因為當時的中國在世界上表現出一種更自信的姿態。”
史景遷的妻子金安平,是出生在臺灣的美籍華人,也是一名歷史學者。
史景遷的作品在中國如此走紅,和當前國內公共史學領域以趣味敘事為主的風格不無關系。讀者們習慣了文學性的講史風格,所以對史景遷的文筆極為欣賞,而閱讀了史景遷,他們又覺得自己接近了學術性的歷史作品,恐怕也會有一絲竊喜。史景遷隱藏在敘事中的學術思路與研究取向,幾乎被無視,作為一名歷史學者,這也算是一種明珠暗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