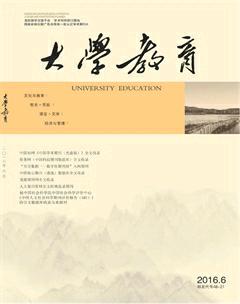大學教育
文化與教育
- 教育碩士開展案例學習的有效途徑與方法
- 數字內容管理微課程教學模式探索
- 英國電子信息類課程觀摩與思考
- 基于工程教育認證和評價體系的應用型人才培養
- 促使學生學習的教育理念
- 拔尖創新型人才培養模式的研究與實踐
- 光電類專業課程設計運行管理新模式的探索與實踐
- 新形勢下大學生創新實踐能力培養體系的構建
- 基于“知識共享”背景下的高校教師教學角色新定位
- “訂單式工學交替”人才培養中的教學組織與管理
- 用“問題化學習”模式改革教育碩士教學的行動研究
- 對地方工科院校本科生參與科研活動的思考
- 淺談如何成為一名合格的高校青年教師
- 獨立學院應用型人才培養模式研究
- 美國公立高校內部立法與權力分配機制研究
- 發現內化教學法在提高大學生創新實踐能力中的應用
- 高職實踐課程“翻轉課堂”教學模式的探索
- 翻轉課堂在Android程序設計課程教學中的運用
- 職業技術師范教育目標下的專升本課程體系構建之研究
- 初探新型高校就業工作體系的前瞻性
- 案例教學法在體育教學中的運用
- 地方高校應注重形成自身學科建設的特色
- 在高校創業教育課程中開展體驗式教學模式的探索
- 卓越計劃對過程裝備與控制工程專業教學的深遠影響
- 中國電子檔案袋研究熱點及發展趨勢
- 高校加強黨外代表人士隊伍建設的思考
哲史思政
語言文學
工農醫林
- 高等工程教育中學生工程素質培養的探討
- 具有火電特色的大氣污染控制工程課程改革探討
- 安全工程認識實習創新改革與實踐
- 道路橋梁與渡河工程(卓越工程師專業現狀與改革
- 應用型測控專業本科畢業設計模塊化運行機制研究
- 機械拆裝測繪實驗平臺的設計
- 土木工程名牌專業建設的實踐與成效
- 醫學專科生就業心理現狀調查
- 獸醫專業實踐教學與建議
- 機械電子工程專業學生應用和實踐平臺建設探索
- 應用Delphi法重構高職《基礎護理學》教材的研究
- 階梯式大學生電子設計能力培養過程的設計與實現
- 巧用課堂總結提高理論授課教學質量
- 形象教學法在機械制圖教學改革中的應用探討
- 創新人才培養模式,加強品牌專業內涵建設
- 測試技術課程內容的教學改革
- 應用型本科院校CAD/CAM技術課程的教學探索和改革
- 如何提高工科大學生圖學素養的探討
- 地方高校給排水專業教學模式改革的必要性與實踐成效
- 基于卓越工程師培養的工程圖學課程教學模式的探索與實踐
- 任務情景教學在《流體機械》教學中的實踐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