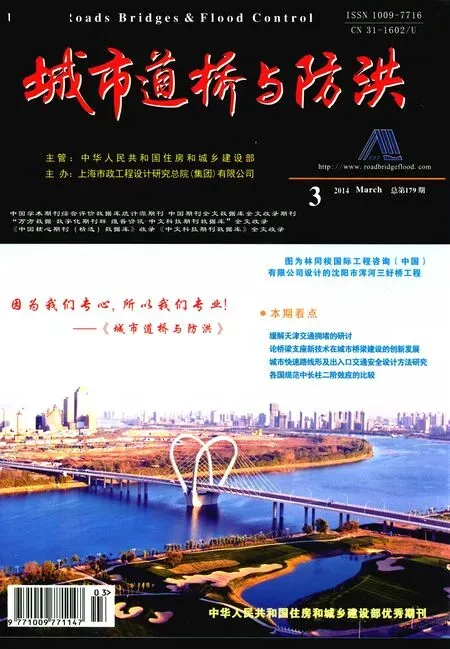高巨粒含量黏性填土的工程特性與承載力判別
陶華飛,彭功勛,李承海,劉良貴
(廣州市政工程設計研究院,廣東廣州 510060)
0 前言
填土一般分為雜填土、素填土、沖填土和壓實填土[1],在工程中非常常見。壓實填土指有目的地按一定標準控制材料成分、密度、含水量,分層壓實或夯實而成的填土,其土質均勻、工程性質好,一般視作一種特殊建筑基礎,如路基、壩基等。其余3種填土,其工程性質復雜而不均勻,或很軟弱,多數情況下都避免直接以其為持力層。本文所提的填土僅指這3種填土。在不得不以填土為持力層的情況下,一定要根據填土原土特性慎重采用堆填與處理方式,否則將對后期的工程建設帶來巨大的影響。
總體而言,不得不以填土為持力層的情況大致有兩種:一種是濱海或臨湖地區人工造地,一般采用吹填方式形成填土區,然后用堆載預壓、真空預壓[2]排水固結加攪拌樁[3]等處理方式處理,成為滿足承載力和變形要求的復合地基;另一種是低山丘陵地方的場地平整[4],部分挖方、部分填方,形成建筑用地,填方時要求逐層堆填、逐層壓實,使土層均勻、密實,達到建設用地承載力要求。這兩類填土處理過程比壓實填土要求低,處理相對粗放,堆填范圍和厚度一般也更大;不過,其堆填目的明確、組織有序、經一定深度的處理,工程性質可預知、可控制,類似于原狀土場地。
但是,對于一些不常見的、未經較深處理而堆填成的深厚填土地基,在不得不以其為持力層時,無論勘察、設計、施工還是檢測,都要慎之又慎。需全方位了解填土的性質,并注意克服常規工程形成的慣性思維模式,作出符合實際的判斷,才能制定出切實可行的勘察、設計、施工和檢測方案。在這幾個環節中,勘察作為初始數據的提供方,其判斷和結論至關重要,建設方一定要委托實力雄厚、經驗豐富的勘察單位進行勘察,才能確保工程的順利實施。設計、施工和檢測各方也需根據現場情況及時作出判斷和調整,以糾正勘察階段可能的失誤。
本文的工程實例深切說明了其重要性。
1 工程概況
1.1 場地概況
工程場地面積約40萬m2,位于丘陵邊緣,原地形高差七八十米,人工堆填平整后形成建筑場地。堆填的土以黏性土為主,多含粗粒、巨粒,厚度不一,最厚達60 m,平均厚度達25 m。填土堆填周期很短,在3個月內完成全部堆填工作,一個星期后即進場勘察。該場地擬建一批住宅樓、教學樓,以及一個運動場,設計要求地基承載力200 kPa。
1.2 勘察方案與結論
勘察采用了鉆探、標準貫入試驗、取土做常規土工試驗的常規工程勘察手段。現場共鉆探了370個鉆孔,全部鉆孔有填土揭露,其中約87%含有大量碎石及塊石,多數含20%~30%的碎石和塊石,部分高達50%以上。
除碎石、塊石含量超過50%的填土未做標準貫入試驗和采取土樣外,在其它填土中均進行了標準貫入試驗,采取了土樣。現場測試及室內土工實驗所獲參數的統計結果如表1所示。
根據表1,若按黏性土判斷,由標準貫入數據可得地基承載力特征值達310 kPa;由土工參數可得地基承載力特征值達260 kPa;由壓縮模量可得其為中等壓縮性土[5]。然而,由于其為填土,貿然由此得出承載力和壓縮性數據是不恰當的。勘察單位也注意到了這一點,勘察報告給出了如下結論和判斷。
(1)人工填土因含碎石標準貫入擊數偏大。
(2)人工填土土質松散,工程特性差,未經處理不宜作為場地天然地基持力層。

表1 填土層現場測試與土工實驗主要參數統計結果
(3)根據碎石含量由低到高,承載力特征值的建議值為 110 kPa(無碎石)、130 kPa(碎石 20%~30%)、140 kPa(碎石含量大于 50%)。
(4)根據碎石含量不同,壓縮模量Es1-2的建議值為 4.35 MPa(無碎石)和 4.1 MPa(碎石 20%~30%);碎石含量超過50%的填土則作為碎石土,沒提壓縮模量。
(5)填土土層厚度較大,若采用天然地基,應進行夯實地基處理。
1.3 設計與施工方案
設計根據規范和勘察報告的建議,采用了強夯地基處理方案,具體參數如下。
(1)目標:夯擊影響深度6~8 m,地基承載力目標200 kPa,沉降量小于40 mm。
(2)單擊夯擊能3 000 kN·m,夯擊次數10~15次,收錘標準為最后兩擊平均沉降量不大于50 mm。
(3)強夯兩遍,第一遍坑距4 m×4 m,第二遍在4個坑之間的中心點布坑。
(4)強夯完成至少24 h后,低能量滿夯兩遍,每遍2擊,夯擊能1 000 kN·m,夯印搭接1/4錘印。
在填方完成一個月多后,施工隊伍進場開展強夯作業。由于試夯影響進度,建設方取消了試夯,直接按設計方案對場地進行了強夯處理。因施工進度緩慢,加之雨季的影響,強夯地基處理前后耗時近四個多月。夯擊過程中,夯坑過深影響施工時,采用碎石回填。
1.4 檢測方案與結果
根據設計提出的檢測方案,建設方分別委托了兩家檢測單位進場分別開展標準貫入試驗檢測和平板荷載試驗檢測。
標準貫入試驗測試表明,標準貫入擊數比勘察階段顯著提高,在最深5 m左右、最淺不到2 m處,其標準貫入擊數就已超過50擊。其根據規范中關于黏性土承載力的判別表格,得出場地表層0.5 m土的最低承載力都達到300 kPa的結論。依此結論,場地土顯然是滿足設計要求的。
但是,平板荷載試驗卻得出了與其截然不同的結論。在最初用1 m2荷載板做的6個檢測點中,只有1個點滿足承載力要求,其余5個均不滿足要求,試驗得到的最小承載力特征值僅為100 kPa,是設計要求承載力的1/2。
為此,建設方又安排了第三家檢測單位進場做平板荷載試驗檢測。該單位用2 m2荷載板做了12個點的檢測。檢測結果表明,填土較薄位置的7個點承載力能滿足要求,但位于厚填土區的5個點仍不滿足要求,試驗得到的最小承載力特征值甚至才75 kPa。
2 高巨粒含量黏性填土的工程特性
為分析上述工程所出現問題的原因,無疑首先要掌握現場填土的工程特性。
2.1 壓縮性
從前文所述可知,現場約1 000萬m3的填土在短短3個月的時間內完成堆填,每天超過10萬m3的填方量根本來不及充分碾壓。因此,勘察報告對其土質狀況評價為“松散”應是合理的。
“松散”意味著大的孔隙比和高壓縮性。但是,在現場取土試樣及室內實驗人員做土工實驗時,囿于僅對“原狀土”做實驗的意識,人為地棄除了明顯的“擾動土”,從而使得土工試驗結果相對真實地反映了填土原土的工程特性,卻恰恰未反映出填土應有的工程特性。如表1所示,假如填土的孔隙比確實僅為0.75,也就是其孔隙度僅為43%,基本上接近一般土的平均孔隙度,對應于粉土或砂土,至少是中密以上的狀態,遠不是“松散”的狀態;而若其壓縮模量達到4.50,也說明其為中壓縮性土,就不會出現平板荷載試驗檢測出現的結果了。
由此表明,土工試驗的數據是假象。對于土質松散的填土,應當意識到其已經是擾動土的本質,在取土樣以及做土工實驗時,消除慣性的、先入為主的“原狀土”思維定式,尊重其當前性狀來做實驗,才能反映出土的實際性狀。
2.2 承載力
鑒于高巨粒含量的存在,通過標準貫入試驗判斷土的承載力是不恰當的[1,6]。
由于標準貫入器的結構特點,當遇到巨粒存在時,將把巨粒往深處擊入,并不斷擊到巨粒表面,使擊數畸高,反映不出土的整體力學特性。圓錐動力觸探試驗探頭則不同,其錐形結構可以把接觸到的巨粒擠到側面,從而達到測試目的。這正是規范說明前者僅適用于砂土、粉土和一般黏性土,重型或超重型動力觸探才適用于碎石土的原因所在。
該工程勘察報告中提到標貫擊數偏大,正是基于這一考慮。若不考慮巨粒的作用,如前文所述,場地填土在不做處理的情況下就已經有310 kPa的承載力特征值,比因假象而人為抬高了的土工參數法判別的承載力特征值還高出50 kPa。這顯然是與實際情況不符的。到檢測階段,由于強夯階段回填碎石的影響,其標貫擊數更是急劇增大,由之判別承載力無疑是不妥的。
2.3 沉降變形
從勘察報告的土工實驗仍可以得到的一個結論:用于作為填土的黏性土本身工程性質是很不錯的。實驗表明,其液性指數為0.35,是硬可塑的土[1],與編錄的描述也相符,按該工程的要求,其承載力是不成問題的;而考慮到其高巨粒含量的情況,承載力只能更高。因此,雖然做平板荷載試驗要求給出的是承載力是否足夠的結論,但場地的根本問題不是承載力問題,而是變形問題。
由于得不到填土實際的參數,事實上無法按規范計算出場地在設計荷載下的沉降量s。不過,根據平板荷載試驗數據,可以大致估算出s值。
以某點試驗數據為例。該點所做的2 m2圓形平板荷載試驗所得承載力特征值為120 kPa,測得沉降量為100 mm。該位置的填土層厚度約20 m,樓的平面尺寸為60 m×25 m。對于單層土,沉降計算公式[7-8]為:

2 m2圓形平板半徑r為0.8 m;假設平板荷載作用深度達到規范表格所能查到的最大值5 r,即4 m深,其平均附加應力系數=0.341;p0=120 kPa,s=100 mm。代入式(1)可得:ψS/ES=0.61MPa-1。
與此類似,可以通過平板荷載試驗測得的數據估算出其它位置的沉降量及樓面的不均勻沉降量。根據場地厚度情況及平板荷載試驗結果,并考慮到強夯的有效處理深度,在設計荷載下,現場最大沉降量預計將可達3 m以上,甚至達5 m以上。
3 工程失誤分析與補救措施
3.1 工程的失誤之處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正是因為缺乏對高巨粒含量黏性填土工程特性的深入了解,導致工程建設各個環節的些許失誤,最終造成難以挽回的損失。具體的失誤總結如下。
(1)場地平整方在委托填方時,沒對巨厚填土上進行建設的可能問題做出恰當的預判,導致沒有采取嚴謹科學的堆填程序進行堆填,使得填土呈松散狀,帶來后期建設的困難。這是問題之源,也是消除問題的最關鍵一環。該環節的失誤,使得后期的損失成為必然,區別僅僅在于損失的大小。
(2)勘察方雖然對填土的性質有所認識,但是認識不夠深入,采取的勘察手段不夠恰當,給出的建議也有偏差。
其認識不深反映在其所提的填土壓縮模量ES上,雖然對實驗值有所折減,但給出的4.1 MPa和4.35 MPa仍誤導了設計,使設計認為其為中等壓縮性土。根據2.3節所述,由平板荷載實驗可得ψS/ES=0.61MPa-1,ES最大也僅有 2.3 MPa,而且這還是經過強夯處理之后,亦即勘察階段應比2.3 MPa還要小許多。由此可見,勘察報告給出的ES值與實際情況相差甚遠。
關于其采取的勘察手段,恰如前文所述,場地不適宜采用標準貫入試驗做測試,可其恰恰采用了;取土樣及土工試驗也沒有根據填土的性質做出調整,而是依葫蘆畫瓢去做,所得數據是否有參考價值并未做出嚴謹的判斷。其以夯實地基處理作為天然地基的建議,則沒有考慮到強夯處理的有效深度與場地填土深度不匹配的問題,因為即便夯擊能高達6 000 kN·m,強夯處理深度也不過10 m[9],而現場填土平均厚度達25 m,不可能處理完全;報告也沒對處理后可能的不均勻沉降提出警示。
(3)設計方面對沉降控制的必要性有所認識,給出了控制條件,但是,對填土富含巨粒及其松散性均缺乏認識,具體表現在提出的檢測方案和施工方案中。在檢測方案中,安排用標準貫入試驗驗證承載力,如前所述,在勘察報告已說明填土含大量碎石及塊石的情況下是不當的;而其要求強夯施工時若夯坑過深則用碎石回填,卻沒考慮到這將使標準貫入試驗檢測更加不適用。在施工方案中,面對最厚超過60 m、平均厚度25 m的填土,采用夯擊能3 000 kN·m的強夯就期待解決問題,并且其處理要求也主要是要求達到200 kPa的承載力,并沒認識到現場地基主要不是承載力控制,而是沉降變形控制。
(4)施工延續了設計的認識,在其施工中沒意識到現場土的硬度和超常夯沉量之間的矛盾。從其強夯施工記錄可見,場地不同位置的夯沉量差異很大,在夯擊5次的情況下,最大的接近1.50 m,最小的只有0.4 m。同時,施工沒有按要求達到最后兩擊平均沉降量小于50 mm才停夯的要求,而是提前停止了夯擊。
(5)做標準貫入試驗的檢測方,在測試中發現明顯存在大量碎石的情況下,仍然用規范中黏性土的承載力判別表來判別承載力,既沒提出標準貫入試驗的不適用,也沒意識到判別方式的不適用。
3.2 補救措施建議
當然,問題既然已經發生,在分析原因之外,采取適當的措施亡羊補牢是至關重要的。
鑒于現場松散填土最厚超過60 m、平均厚度25 m的狀況,繼續使用強夯無疑并不合適。若設計方面仍未意識到現場的巖土問題不是由承載力控制,而是由沉降變形控制,僅僅加大夯擊能仍然堅持用強夯法處理地基,最終可能帶來后期更大的損失。因為,加大夯擊能處理后,平板荷載試驗結果可能合格了,但是,鑒于強夯處理有效深度最多10 m左右,更深的填土狀態仍然沒有改變,問題不是沒有了,而是被暫時掩蓋了。當在此檢測“合格”的地基上進行工程建設后,由于這些建筑物的荷載是大面積的,其附加應力將傳遞到比平板荷載更深的土體上,引起大范圍的沉降和不均勻沉降,最終導致建筑物的下沉、傾斜和開裂。
因此,最佳的措施是采取大面積堆載預壓處理,預壓荷載宜超過設計荷載一定量。由于其并非飽和土,不存在排水問題,從平板荷載試驗結果看,堆載一段時間使其完成主固結。堆載可分塊進行,堆載時要根據鉆探資料計算可能的不均勻沉降,再根據計算結果適當墊高土層厚的一側再堆載,使堆載體有初始的反傾,以免過大的不均勻沉降導致堆載體傾斜坍塌;在傾斜超過預期,存在坍塌危險時,要及時卸載調整后再繼續堆載。
在此基礎上,根據堆載過程的沉降分布規律,建筑物宜盡可能采取設置沉降縫等結構措施,以預防后期次固結產生的沉降和不均勻沉降。
4 結論
由本文的研究可得出以下認識。
(1)巖土問題千變萬化,沒有一定之規,一定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囿于慣性思維而生搬硬套可能導致難以挽回的損失。這是作為一名巖土工程師務必牢記的。
(2)高巨粒含量的黏性土實際上是混合土,其工程性質不同于一般的黏性土,作為勘察人員,必須明確提出,不能略而不談,否則將誤導參與建設的其它各方。
(3)對“原狀”填土也是擾動土必須有清醒的認識,在不得不以其為地基時,要有針對性的勘察方案和實驗方法,不能按常規針對原狀土的實驗方法來處理,參數建議也要更為慎重。
(4)認識問題要認識本質,認識的不同,決定了設計思路的不同。高巨粒含量的黏性填土的工程特性本質上不存在承載力問題,而是沉降變形問題;固結過程不存在排水的問題,只存在壓密和蠕變的問題。因此,當填土厚度太大,強夯不能達到消除變形的作用時,變換思路采取堆載處理就是自然的選擇;而由于場地填土為高巨粒含量的黏性土,而不是軟土,其堆載時間不需要太長即可完成主固結。同時,建筑物宜盡可能采取設置沉降縫等結構措施,以預防后期次固結產生的沉降和不均勻沉降。
以上結論歸結起來,就是建設方一定要高度重視工程建設的專業性和嚴肅性,委托在理論和經驗上都技術實力足夠強的隊伍參與這類重大工程的建設,才能減少類似的失誤和損失。
[1]GB 50021—2001,巖土工程勘察規范(2009版)[S].
[2]劉加才,施建勇,趙維炳.真空堆載聯合預壓作用下路基固結分析[J].水運工程,2003,(6):1-4.
[3]湯宇皓.真空堆載聯合預壓法和水泥攪拌樁在軟土地基處理中的應用[J].中國外資,2008,6(下半月):216-218.
[4]楊先緒.丘陵地區場地平整土石方測量計算方法的研究[J].四川建筑,2012(5):174-176.
[5]傅裕壽,張正威.土力學與地基基礎[M].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12.
[6]工程地質手冊編寫委員會.工程地質手冊(第三版)[M].北京: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1992.
[7]GB 50007-2002,建筑地基基礎設計規范[S].
[8]DBJ 15-31—2003,建筑地基基礎設計規范[S].
[9]施建勇.地基基礎理論及應用[M].南京:河海大學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