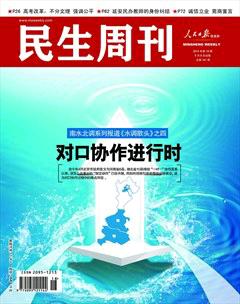探索破解名村“家族化”之路
嚴碧華 牛冠捷 劉曉宇

和傅山村一樣,上世紀80年代初,浙江東陽花園村、浙江奉化藤頭村等亦走上了發展的快車道。
30多年后,它們有了一個個響亮的稱號,成為遠近聞名的富村名村。
一方面,大部分有了良好經濟基礎的名村在改善村民民生方面成效顯著;另一方面,亦有一些村莊頭頂名村之名,而百姓的民生狀況卻十分堪憂。
“風口浪尖”的名村,下一步如何破解民生與名村不對稱的困惑?8月份,《民生周刊》記者根據實地調研情況,采訪多位業內權威專家,試圖理出脈絡。
制度紅利
去年十月,由浙江師范大學和發展中國論壇主辦的“紀念農村改革35周年暨近現代中國名村變遷與農民發展”學術研討會在京召開。
作為經濟強村,花園村負責人與會并介紹了其發展歷程和模式。
花園村是浙江東陽的一個村落,與傅山村類似,此前也是一個有名的窮山村。1978年,花園村年人均收入僅為87元。
30多年后的2013年,花園村實現工業總產值289.1億元,其中,花園村集團實現產值110億元,花園村個體工商戶達1539家,實現產值178億元。
這樣的數字分配在1700多戶5000多名村民身上,充分彰顯了村民的富足。
《民生周刊》記者站在花園集團的屋頂,村莊盡收眼底,農村與城市的區別蕩然無存。由于村里建立了多個市場,企業與商鋪眾多,村民可以合理利用自己房屋,坐地生財。
榮譽也隨之來而來,花園村先后被授予全國文明村和中國十大名村等稱號。
一百多公里之外的寧波奉化滕頭村,位于東海之濱。現有300多農戶,村民近千人,耕地近千畝,是一個充滿水鄉特色的江南小村。
優美的江南水鄉同樣曾極度貧困。“田不平,路不平,畝產只有兩百零,有女不嫁滕頭村。”滕頭村及周邊的村莊曾用這樣一首民謠來形象比喻村莊的貧窮。
20世紀末,滕頭村的歌謠變成了“田成方,樓成行,綠樹成蔭花果香,清清渠水繞村莊。”如今,新建村民別墅群,花樹綠坪環繞其間,假山盆景錯落有致。
2013年滕頭村實現社會總產值75.62億元,利稅8.328億元,村民人均純收入52000元。
富裕起來的滕頭村又有了兩句婦孺皆知的話,分別是:一家富了不算富,集體富了才算富; 滕頭沒有貧困戶,沒有暴發戶,家家都是小康戶、富裕戶。
類似名村還有不少。《民生周刊》記者調研發現,發展路徑大同小異,那就是早年就非常重視二、三產業,工商業發展起來后再反哺村莊。而農村工商業的發展顯然離不開農村改革的政策。
在前述關于名村變遷的研討會上。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原辦公室主任、中國扶貧基金會會長段應碧認為,35年來的農村改革主要是對農村三個方面的制度進行了深層次的改革:一是改革人民公社制度,實行了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給農村培育了市場經濟的微觀主體,把農戶變成了生產經營單位;二是改革計劃經濟制度,特別是計劃購銷制度,在農村形成了市場體系,讓農民進入工商領域,給農民發展開辟了新的機會;三是改革城鄉二元體制,逐步實施城鄉一體化發展。
“特別是第二條,讓農民進入工商領域,充分激發了農村經濟的活力。”8月28日,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宏觀室主任黨國英向《民生周刊》記者如此表示。
包括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趙學軍在內的多位專家在受訪時表示,各具特色的名村變遷與發展,集中彰顯農村改革和農民發展的巨大成就時,反過來也證明了農村改革的制度紅利給了名村做大做強的良機。
問題凸顯
政策利好之下,一批名村迅速脫穎而出,村內工商業發展迅速,村民生活也顯著改善。
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尤其是步入21世紀之后,亦顯現出一些問題。有一些村莊,盡管村集體經濟總量很大,村莊知名度也很高,但村民受益卻不多,且民主生活堪憂,兩極分化越來越嚴重。無論是村黨委、村委會還是村里的集團公司,“家族化”傾向越來越明顯。
類似案例近年來媒體報道層出不窮,有些村莊幾十年財務不公開,即便公開也很籠統,村民無從監督;有些村黨委書記或村支書長期任職,逐漸培養了自已的“圈子”,村民代表大會流于形式;村辦企業是粗放經濟的產物,其無序發展嚴重破環了村莊的優美環境。
趙學軍表示,按照《村民委員會自治法》規定,村應當建立村務監督委員會或者其他形式的村務監督機構,負責村民民主理財,監督村務公開等制度的落實,但在現實操作中,難度很大。
黨國英在調研中也發現,村民確實很難監督村兩委干部。“一些地方剝奪農民利益的情況確實存在,民主生活也多流于形式。”
農業部農村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宋洪遠在接受媒體訪談時也指出,從實踐層面上看,有兩個問題較為突出。一個是村黨支部委員會和村民委員會的關系很難處理好,另一個就是實行村民自治制度以后,賦予農民群眾的各項民主權利未能真正落實,農民利益受侵犯的情形仍比較普遍。
尤其是后者,在一些名村也普遍存在,一些村莊無論是村兩委還是村企,長期為某一家族把控。
最終導致的結果是,個別村集體經濟總量龐大,村莊知名度也很高,但跟普通老百姓卻關系不大,尤其在改善民生方面與村民期待相距甚遠。
參考路徑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對于能否從制度層面約束某一家族長期把控村兩委和村辦企業的問題,黨國英和趙學軍均表示并不樂觀。
“支部書記職務時間長,眼下可能也沒有更好的辦法,說任期搞個五年,十年,不現實。”黨國英表示,村委會主任是通過村民選舉,而村支書是通過村內黨員選舉或鄉鎮黨委任命。
而事實上,在農村特別是名村,黨支部書記比村委會主任擁有更加核心的權力,由于村支書或村黨委書記長期任職,其影響力遠遠高于村委會主任,往往是“支部書記定盤子,村主任領著干”,民主決策自然流于形式。
幾年前,北京通州推廣“村支書大考”, 考官為村民代表,他們對每名村支書逐一打分評議,并現場投票,12人曾因差評被罷免。
“農村能有這樣的做法很不容易。”黨國英當時受訪時坦言,他曾建議這一模式在農村鋪開。“村委會作為行政機構,可以進行基層民選,能體現群眾的意愿;而對于村支書的政績,群眾卻幾乎沒有話語權,難以評價。”
受訪專家普遍認為,名村是農村改革的產物,成效顯著,積極意義明顯,下一步,重點是完善和加強村民自治,破解名村民生之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