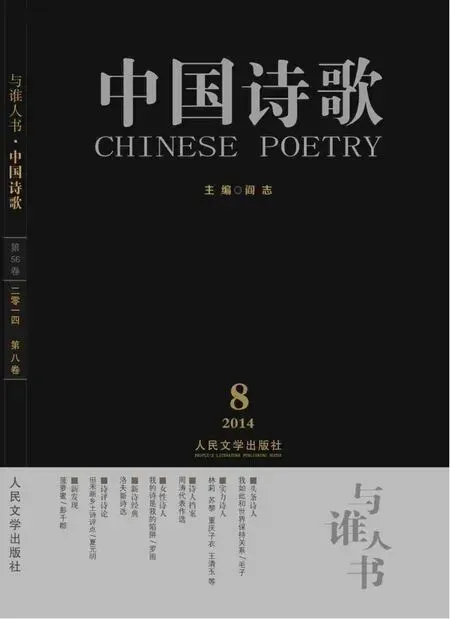一個人在村莊的廢墟上(組章)
2014-01-09 07:51:46□亞男
中國詩歌
2014年8期
關鍵詞:瓦片
□亞 男
序。這是哪兒——
幾間瓦房,一片水域。
山和田野都是干凈的,都是沉默的。
從黃昏推開。廣闊。綿柔。
田坎長了些花花草草。細嫩細嫩的。彎曲的是一條條交錯的路,如血管一樣盤繞。坡坡坎坎,伸手就可以撈到水中的魚。
幸福的魚,自由自在。
我不是魚——
夕陽在我后背上,落了幾片葉子。
手有一種黃的感覺,我觸摸到了河流的卵石。在祖先的余溫里,強顏歡笑。肩挑背磨的村莊。是的,老態龍鐘了。
我不是水——
河灘種植的笑聲早已遠去。

有老繭的村莊,祖先遺留下來的善良就是一口水井,源源不斷地養育我,或者一些雜物的堅硬。
我不是土——
坡坡坎坎上,牛和羊相依相伴。啃走了時光。古木與春天。
山野與曠古。
我生命的根源之地。
——我的村莊。
暗下來
天空。大地。
我看不見了,究竟籠罩著什么——
空氣在血液里流動,時光刻在滄桑里。
不自覺地去觸摸,大地一派空茫。這刻我走在一個叫村莊的地方,心生疑惑,這還是從前的村莊嗎——
枯枝和雜草哪去了。飛鳥和炊煙哪去了。雞鴨哪去了。殘存時光里的凌亂,荒蕪不見了,僅存的只有一聲嘆息。
流水和雨滴在我記憶里。
我不能失去的土地和村莊,陷入深夜的暗。
出現在我生命意識里的,不僅僅是一縷風,還有那些無孔不入的,從欲望里散發出來的毒。暗下來——
是最好的一處去處。
隱沒在靈魂里,我看見了靈魂流離失所。
裸露在廢墟上,我只能望眼欲穿。
不見了
靈魂的土壤,種植了月光和風雨——
我不想去回憶。
不想——
村莊被砍伐。時光被砍伐。……
登錄APP查看全文
猜你喜歡
遼河(2025年7期)2025-07-25 00:00:00
揚子江詩刊(2021年4期)2021-11-11 15:58:35
揚子江(2021年4期)2021-08-09 18:37:31
散文百家(2019年2期)2019-03-13 13:17:04
揚子江(2019年1期)2019-03-08 02:52:34
測繪科學與工程(2016年6期)2016-04-17 06:51:25
測繪科學與工程(2014年6期)2014-02-27 07:06:23
測繪科學與工程(2014年1期)2014-02-27 07:05: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