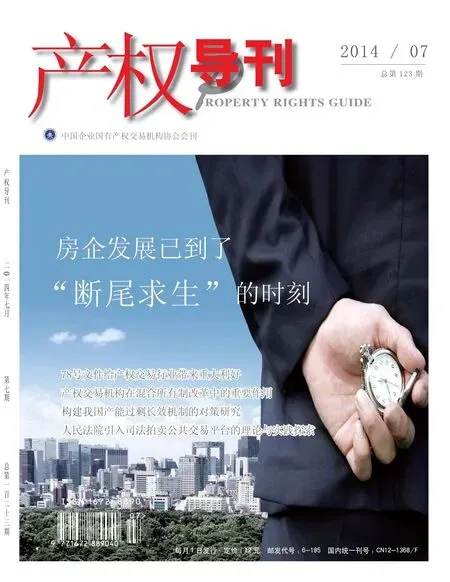新型城鎮化進程中農村土地流轉問題與治理
◎ 王智源(合肥市政協研究室,合肥 230071)
新型城鎮化進程中農村土地流轉問題與治理
◎ 王智源(合肥市政協研究室,合肥 230071)
經濟生產要素,只有進入流通領域才能發揮效益,而我國正處于新型城鎮化的關鍵時期,土地作為最稀缺的資源在不同的利益主體之間流轉也就成了必然。對于農村土地流轉的內涵主要可以從廣義、狹義與超狹義三方面著手:在廣義中對于農村土地流轉的定義是土地權利與功能(土地的利用關系)的雙流轉;狹義農村土地流轉概念則強調權利流轉,即農村所有權與使用權的全部流轉;而在我國,更多的學者則認可所謂的超狹義流轉,即僅僅包括了土地使用權的流轉,因為根據我國現行的憲法、土地管理法等相關規定,農村土地所有權歸國家所有與集體所有,農村土地所有權轉讓途徑僅限于國家對集體所有土地的一種不可逆的、單方面的征收,因此基本不存在所有權轉移的市場化運營問題。可以說,我國農村土地流轉的內涵多是側重于承包經營權的流轉,但是市場在農地資源流轉中起著決定性的作用。

1 新型城鎮化進程中農村土地流轉涉及的主要問題
1.1 土地產權關系不夠清晰
土地產權,即包括土地所有權、使用權、收益權、處置權與土地抵押權等各種權利的總和。只有明確的土地產權關系才能使得交易費用最小化,否則都會減小交易邊界,形成更高的交易成本。在我國,土地產權的關系是不明晰的,我國的土地所有權、使用權、收益權等相分離。如我國《土地管理法》規定,農民所有的,由村集體經濟組織或者村民委員會經營、管理。在這樣的產權中最為重要的所有權問題出現分離之后,這就產生了代理問題,對于農民的最大激勵作用消失,因為所有權的缺陷導致了所有權利的不穩定,這將影響到農民對所經營土地未來產出的判斷,農民將考慮自身投入的沉沒成本是否能在有限的租期內收回。而在土地正常流轉過程中,土地流轉所得將成為村集體所得,而自身職能得到微薄的補貼,這將嚴重損害正常土地流轉的進行。
1.2 行政干預時常侵犯農民土地流轉自主權
在基層政府與干部針對農村土地流轉工作時,由于主觀和客觀兩方面原因導致了干預和侵犯農民的土地流轉自主權。首先是主觀原因,即巨大的利益誘惑,在近幾年城市化過程中,土地作為稀有資源存在的巨大經濟利潤不言而喻,容易滋生腐敗。客觀原因主要是制度中的漏洞較多,一方面是基層官員權力過于集中,監督制約制度得不到真正落實。另一方面是土地流轉程序不規范,只有少部分通過鄉鎮村(居)集體產權交易和建設工程招投標管理中心交易的農村土地流轉業務才具備較為合法、合格、合理的交易程序。
1.3 農村土地處置權的不完整
處置權,即指依法對物在事實上或法律上最終處置的權利,包括使用權、轉讓權、抵押質押權等。但我國的農村土地是產權不明晰的,所有權缺陷導致了處置權不完整,土地產權界定模糊使得農民所擁有的土地處置權不完整,未能真正擁有土地的處置權和交易權, 也極大地妨礙了農村土地流轉。
1.4 農村土地流轉的頂層法律制度不配套
長期的城鄉二元體制,使得關于農村的法律法規嚴重滯后于現實的發展,無法滿足現實的需要。在我國的現行法律體系中,基本缺乏系統的宏觀、中觀的關于農村土地流轉的法律法規政策,僅僅《土地管理法》、《物權法》、《農村土地承包法》等少數幾部法律中具有相關的規定。操作性法律法規的缺失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農村土地流轉的不規范性與盲目性,這嚴重制約了農村土地流轉的開展。
2 治理新型城鎮化進程中農村土地流轉主要問題的幾點對策
根據上述對存在問題的簡要分析,在當前如火如荼的新型城鎮化進程中,對于農村土地流轉涉及這些問題的治理對策,可以從如下幾方面著力:
2.1 不斷完善農村土地流轉法律機制
2.1.1 通過立法明晰產權。產權不明晰是妨礙農村土地流轉最為主要的障礙,而在產權關系中,所有權對于農民做出決策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因此,通過立法明晰產權首要是明晰所有權關系。關于農村土地所有權的歸屬問題,我國眾多法律并未作出明確的規定,我國《憲法》第10條第二項規定,農村和城市郊區的土地,除由法律規定屬于國家所有的以外,屬于集體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屬于集體所有。之后在《民法通則》第74條、《土地管理法》第10條、《農村土地承包法》第12條、《物權法》第59條都將農村土地所有規定為集體所有,但集體所有是一個抽象的概念,并沒有一個明確的組織。因此,需要通過立法將所有權主體具體化。
2.1.2 充分保障農民權益權。在農村土地流轉中,利益受到損害最為嚴重的往往是農民,而收益權又是農民決定是否愿意土地流轉的重要因素,而保障農民在土地流轉過程中收益權的關鍵在于明確公共利益與征地補償機制。我國《憲法》第10條第三項規定,國家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規定對土地實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給予補償。而在我國現階段,幾乎所有的征地行為,無論是為企業征地還是為政府征地,都可以籠統地打著“公共利益”的旗號。因此,在立法過程中需要對“公共利益”進行明確的內容界定,設計嚴格公正的程序與征地規則;除了對公共利益進行界定之外,合理的征地補償機制的建立也是促進合理合法土地流轉的重要保障。我國《土地管理法》第47條規定,征收土地的,按照被征收土地的原用途給予補償。征收耕地的土地補償費,為該耕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產值的六至十倍。這與修訂前的《土地管理法》中規定的三至六倍已經有所提高,但基于我國土地價格一倒手便能上漲幾十倍、上百倍的現實而言,規定的補助倍數與上限限制顯然是不合理的。
2.1.3 允許有條件的土地經營權抵押。農村土地經營權是一項物權已經毋庸置疑,因此土地經營權所有人理所當然地擁有包括抵押權在內的處置權利。而且土地經營權的抵押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決農業生產資金不足問題,起到農業融資作用。當然,基于經營權這一對于未來收益是虛擬化的物權,應該適度有條件的放開,如學者王冠璽曾提出應該在完善現有的四荒地抵押基礎上擴大其范圍,有條件地將一般的土地承包經營權納入抵押貸款范圍之中。
2.2 建構和施行農村土地流轉監管的系統性長效機制
2.2.1 政府機關要建立相應的權力監督部門,我國目前正是由于缺乏強力的監督機制而導致土地流轉權力的配置與行使不規范,甚至有越權的現象,只有不斷加大約束,在政府建立監督部門才能有效控制權力濫用行為的發生。
2.2.2 除了在政府機關內部建立監督部門之外,社會輿論作為第三方監督機制發揮著重要的作用,但是在建立相關組織時需要公正、具有權威性、運行透明,突出對行政部門在農村土地流轉中的權力行使問題。
2.2.3 群眾監督,這主要是農民集體組織的監督功能。農民集體組織是在農村土地流轉過程中受損失最大的利益方。因此,只要對其進行相應的法律法規的宣傳與教育,農民集體組織會有自發的監督動力,可以促進合理的土地流轉機制的完善。
2.3 建立健全其他相關的配套治理措施與制度
2.3.1 健全村民自治機制。農村土地所有制為集體所有,作為農村土地流轉過程中重要的出讓方,必須是農民真正的代言人,站在農民的角度,為了農民的利益與轉讓方及政府等部門進行協商,使得農民的權益獲得真正的維護。
2.3.2 完善市場機制。這可以確保農村土地流轉在合法的情形下自由流通,發揮市場的決定性作用,保證資源合理利用,也有利于農民獲得更高的收益,充分享有所經營管理土地的收益權。
2.3.3 健全社會保障制度。在農民將自己所經營的農村土地流轉之后,緊接著面臨著就業問題,而在社會就業壓力日趨嚴重的情形下,必須將這部分農民的生活有所安排,使之有所保障,將社保體系對接和銜接好,防止農民在土地流轉后的毀約現象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