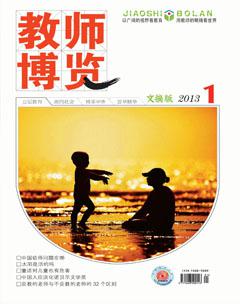饑來吃飯倦來眠
陳世旭
明代最著名的思想家、史上罕見的全能大儒王陽明有一首詩:“饑來吃飯倦來眠,唯此修行玄又玄。說與世人渾不信,偏向身外覓神仙。”比他大兩歲的風流才子唐伯虎也有一首詩:“不煉金丹不坐禪,饑來吃飯倦來眠。生涯畫筆兼詩筆,蹤跡花邊與柳邊。鏡里形骸春共老,燈前夫婦月同圓。萬場快樂千場醉,世上閑人地上仙。”
兩位古人處在同一時代,但人生境遇迥然不同:王陽明功成名就,唐伯虎則命運多舛。然而,他們從不同的人生角度,得到的是對人生的相同理解。
當代國學大師葉曼先生講解《道德經》時也說過:“什么是道?就是饑來吃飯困來睡。”
有一段禪門公案是這樣講的。兩位法師交談,甲問乙:“和尚修道,還用功嗎?”乙答:“當然用功啦。”甲問:“如何用功?”乙答:“饑來吃飯,困來即眠。”甲問:“人人都是如此,豈不是與大師一樣用功?”乙答:“不同。”甲問:“怎么不同呢?”乙答:“他們吃飯時百般挑揀,睡覺時千般計較,因此,他們與我的用功不同。”甲默然。
關于“饑來吃飯倦來眠”,許多人從許多角度做了許多引申和闡釋。以我有限的閱讀,做了一個不全面的梳理和歸納,主要有:
第一,“理出于易,道不在遠。極高寓于極平,至難出于至易;有意者反遠,無心者自近。”世間極高深的道理,往往產生于極平凡的事物中,有意者遠于理,而無心者近于真。比如寫詩的秘訣,就該是“眼前景致口頭語”,多運用隨處可見的景致和通俗明白的話語,因為極美的詩往往出于無心的真情流露。
第二,“出世在涉世,了心在盡心”。遠離凡塵俗世修行的道理,應在人世間磨煉,根本不必離群索居與世隔絕;要想完全明白智慧的功用,應在運用智慧的時刻去領悟,根本不必使心情猶如死灰一般寂然不動。
第三,“身放閑處,心在靜中”。只要使自己的身心處在安寧中,世間所有榮華富貴與成敗得失就都無法左右你;功名利祿與是是非非就都不能欺蒙你。
第四,“云中世界,靜里乾坤”。所謂“竹籬下,忽聞犬吠雞鳴,恍似云中世界;蕓窗中,雅聽蟬吟鴉噪,方知靜里乾坤”。當你正在竹籬下欣賞林泉之勝,忽然傳來雞鳴狗叫之聲,你會宛如置身在一個虛無縹緲的快樂世界里;當你靜坐于書房,忽然聽到蟬鳴鴉啼之聲,你會體會到寧靜中別有一番超凡脫俗的天地。
第五,“不希榮達,不畏權勢”。一個人如果不希圖榮華富貴,誰也無法用名利作餌來引誘你;一個人如果無意與人競爭高下,就不必恐懼官場、職場中潛伏的種種危機。
第六,“貧得者雖富亦貧,知足者雖貧亦富。貧得者分金恨不得玉,封公怨不受侯,權豪自甘乞丐;知足者藜羹旨于膏粱,布袍暖于狐貉,編民不讓王公。”一個貪得無厭的人,你給他金銀他還怨恨得不到珠寶,你封他爵位他還怨恨沒封王侯,這種人雖然身居富貴之位卻仍等于乞丐;一個自知滿足的人,即使吃粗茶淡飯、穿布衣棉袍身居平民地位,也會比吃山珍海味、穿狐襖貂裘的王公更為充實富有。
第七,“濃處味短,淡中趣長。悠長之趣,不得于酉農釅,而得于啜菽飲水;惆恨之懷,不生于枯寂,而生于品竹調絲。故知濃處味常短,淡中趣獨真也。”就是說,一種能維持久遠的趣味,并不是在美酒佳肴中得來,而是在清淡飲食中得到;一種悲傷失望的情懷,并非產生在窮愁潦倒中,而是產生于美妙聲色的狂歡中。美食和聲色的趣味常常顯得很短,單純淡泊的趣味才更雋永。
第八,“欲心生邪念,虛心生正念。欲其中者,波沸寒潭,山林不見其寂;虛其中者,涼生酷暑,朝市不見其喧。”一個內心充滿欲望的人,能使平靜得像深潭一樣的內心掀起洶涌波濤,即使處于深山老林也無法平息;一個內心毫無欲望的人,即使在酷暑中也會感到渾身涼爽,即使在鬧區之中也不會感到喧囂。
總之,我理解的“饑來吃飯倦來眠”,是一種淡然超脫的人生境界。古人因此講究“圣境之下,調心養神”,常“徜徉于山林泉石之間,而塵心漸息;夷猶于詩書圖畫之內,而俗氣潛消”。經常漫步在山林泉石,使滿腦子不切實際的念頭逐漸平息;經常流連于詩詞書畫,使身上的俗氣悄然消失。“借鏡調心”,最終使自己成為一個有才德修養的人。
(郝景田摘自2012年9月16日《今晚報》)
責編:袁海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