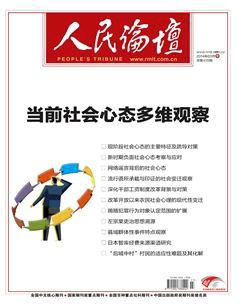權力個人化與腐敗的人性淵源
權力個人化與腐敗的人性淵源
蕭延中
金錢、美色和虛榮這三種欲望,并不因“人”有多少“良心”和“覺悟”就可以減少,因為在某種程度上,它們是“人”之所以為“人”的性質使其所以然
在當下的中國,英國貴族阿克頓勛爵的名言“Power tends to corrupt,and absolute power corrupts absolutely”幾乎無人不曉,人們一般將其譯為“權力使人腐敗,而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但已故著名科學史家許良英先生并不贊成,他認為在原文中,“權力”本身是主語,是“權力”本身“總是趨向”腐敗,并不是它“導致”或“使人”腐敗,“腐敗是指權力本身,是制度,不僅僅是掌權的人”。的確,一種良好的制度在政治中是極端重要的,然而再仔細琢磨,一來,良好制度又由誰人來建構和完成呢?二來,假若弱化了作為腐敗之受體的“人”,那么,權力所散發出的腐敗也就失去了對象,進而也就不會再有“腐敗”這回事了。由此可見,腐敗的主體究竟是“權力”還是“人”本身,就成了一個思考腐敗之出發點和立腳點。
防范權力個人化與腐敗的根基在于穿透“人性”
在抑制腐敗的鏈條中,良好的制度固然具有關鍵的不可或缺性,這是毋需贅言的。但要進一步說清這種“不可或缺性”,就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既是制定制度的主體,同時又是被制度約束的主體的“人”。而要說到這樣的一種“人”,就又要談及“人”為什么非要被制度所約束,進而再進入“人是什么”和“人又怎么了”的論域,自然,這些就是所謂對“人性”作出判斷的問題。
如何判斷“人性”幾乎是所有人文社會學科的基礎問題,對于政治學科來說更是最為基本的論述前提。因為對“人性”采取怎樣的透視進路,將在動機與意圖的層面上決定著建構怎樣的制度構架和設計怎樣的運作機制。一般而言,“人性”預設有幾種不同的角度:一是“善”與“惡”的定奪理論,二是“理性”與“非理性”的選擇說法,三是“靠得住”與“不可靠”的截然區分。雖然這三種預設都以二分法的形式出現,但其邏輯推演結果則可能不大相同,甚至大不相同。比較而言,前兩種透視進路相對來說較為模糊。例如,人們注意到“人”本身既有善的一面,又有惡的一面;“人”在一種境況下是理性的,而在另一種情景中又可能是非理性的,所以把它們作為“人性”判斷的基礎將難免偏頗。但要在“靠得住”與“不可靠”之間找出一個模糊的“中和”空間來,恐怕也并不容易。在筆者看來,或許正是這種非此即彼的斷然性,造就了此種“人性”透視進路的深刻維度,因為在這其中充滿了一種被稱之為“戒慎恐懼”的希望。
對于“人性”的透視,著名思想史家張灝先生的概括極具啟發性,按照他的概括,在西方文明的重要一支的“希伯來—基督教”傳統中,對“人性”中的罪(惡)性和墮(落)性(即所謂的sin,“原罪”)始終保持著一種極其敏感的警覺,張灝先生把這種警覺叫做“幽暗意識”。在其所撰的《幽暗意識與民主傳統》一文中,他指出,“幽暗意識是發自對人性中與宇宙中與始俱來的種種黑暗勢力的正視和省悟”,理由在于“這些黑暗勢力根深蒂固,這個世界才有缺陷,才不能圓滿,而人的生命才有種種的丑惡,種種的遺憾”。換言之,這種“人”之“丑惡”是自身所不情愿但又須臾不離的必然,所以是一種回避不了的窘境。例如,金錢、美色和虛榮這三種欲望,并不因“人”有多少“良心”和“覺悟”就可以減少,因為在某種程度上,它們是“人”之所以為“人”的性質使其所以然。一方面,沒有金錢則無法生存,失去美色人將絕種,丟棄了虛榮心似乎也就難有進取動力了;可另一方面,這三種欲望又絕對不是可以“多多益善”的,因為它們都深深地根植于某種“黑暗”的種子,隨時可能發作出來去傷害他人。因之,在“人性”之中,上述“三欲”(在負面意義上就是所謂“罪性”或“墮性”)時時處處呈現出強烈的“緊張”(tension)。質而言之,正是這種“人性”的幽暗一面,成為“人”可能腐敗的深刻根源。
在這樣的一種“人性”假定的路徑下,“人性既然不可靠,權力在人手中,便很容易‘泛濫成災’。因此,權力變成一種極危險的東西”。于是,抑制權力的必要就呼之欲出了。
把“最大的權力”關進籠子的“軟”“硬”路徑
既然“人”是靠不住的,而既充滿“三欲”,又具有支配力的權力又只能由“人”來行使,那么,緊跟著的問題就是如何限制這種權力。大致而言,歷史上解決權力問題的思路有兩條:一條路是希望執掌權力者自我約束,透過道德的培養,以一個完美的人格去凈化權力;另一條是“以惡治惡”,謀求制度上的抑制和防范。前者講求一種“內化”的“軟”的道德機制,以提升“人性”品質;而后者則相信只有在“人性”之“外面”尋找“硬”力量,“以權力制約權力”,從而達致一種最理想的狀態,即掌權者想腐敗而沒有機會。這后一種路徑就需建構合乎“人性”預設而審慎嚴密的制度。例如,現代會計制度就是出自于早期教會管理捐獻的一種方法。這一制度假定,每個人都有貪污或濫用捐款的可能,于是就設計出種種“記錄”和“簽署”程序,最終使企圖貪污或濫用捐款的私念落空。于是,一個并不排除其可能帶有私欲的“人”,當他曾經時時想貪污,可沒有機會,那么在他死后,就可以被冊封一個“善人”的桂冠。所以,嚴格的制度防范不會改變任何一位“罪人”預設的性質,但卻最終改變和成就了一位“善人”。
現代會計制度的設計初衷如此,明確的政治制度更是這樣。只不過政治制度的設計思路,更把“看盯”的重心放在“整體性絕對大權力”方面,用分割法和制衡法,使這種權力“化整為零”,再使小權力之間形成相互的“看盯”,從而在“大”、“小”各種權力間實現“去絕對性”。這樣,基于人性之不可靠的假設,在正視“人性”“自利”動機的前提下,通過“以惡治惡”的方式,達成一個“不曾預期”但卻最為接近的“善”與“公正”。
就此看來,關于“幽暗意識”的人性預設比樂觀主義的人性觀更為實在,也更為安全,因為后者最不牢靠的方面,與其說它并不反映“人性”更具普遍性質的一面,不如說這種“人性”透視需要在人間尋找出一種“超人”的角色,由其來頒賜準則、布施教化、實施懲戒。可在漫長的人類歷史中,我們從未見到過這種“超人”,反而從中國近代的歷史中嘗盡了信奉“超人”的苦頭。而最讓人感到悖謬的是,此種不曾正視自身“罪性”的“超人”,憑據拯救世界的雄心和自恃至高善性的道德,并以此作為正當性理據,就可以使用任何“不道德”的方式對違背其意志者實施懲戒。歷史就曾掉進了以“超人之大權力”去制約“凡俗之小權力”的“人治”怪圈,而“如何把最大的權力關進籠子中”的問題,只能懸空擱置,可這才是現實中抑制腐敗并保障長治久安的本質難題。
“消極思維”與“積極思維”
人們或許還要追問:為什么我們的文化中缺乏“幽暗意識”的反省自覺呢?這或許要從所謂“思想形式”(Mode of Thought)的分析方法說起。人的思維進路通常可分為“消極思維”和“積極思維”兩大類型。面對相同的世界,不同的“思想形式”往往會給出各異的解讀。讓我們比較一下這樣兩個思想命題:“為全人類絕大多數人謀取最大利益”和“為生活在絕對貧困線以下的人免除一丁點痛苦”,前者由于沒有限度,所以雖然志業深遠但難以實現;而后者由于具有明確限定,所以反倒容易操作。
在透視“人性”的深度上,“消極思維”幾乎成了“幽暗意識”的常態。猶太思想家帕斯卡爾(Pascal)認為“人”是一個處于“自主性”與“可墮失性”之間的吊詭,“萬物的裁決者,同時又是一個低能兒,一條泥土中的爬蟲”。此處,“低能兒”指人理性上的限制,而“爬蟲”則指道德上的敗壞。哈佛著名比較文化史家史華慈教授也曾說過:“人是所有的神中最壞的神。”學人把這解釋為“不要把人造成為神,不要視人為神”,如果有人自以為能扮演神的角色,他的破壞性會比最壞的人還要大得多:他是個最壞的神。
上述“幽暗意識”中包含的“消極思維”那“令人不快”和“并非高尚”的意識底蘊,以及由之而來的對“人”本性不信任的思維路徑,常被稱為“良性的懷疑主義”(Benign skepticism),雖并非樂觀進取的亢奮與高昂,但卻完全可與深度的理性思考相銜接,進而將沉思的力量直指“人類自身”與“永恒超越”之間的本質關系,也即對人性“奧秘”的不懈反省和終生拷問。而從孟子的“性善說”中,人們看到的則是“積極”道德意志的崇尚與高揚。我們是否可以進一步設問,面對權力腐敗的現實,這貌似被動的“消極思維”是否更具深刻洞察的慧眼呢?
(作者為華東師范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博導)
責編/袁靜 美編/李祥峰
權力個人化
概念:掌握權力者視手中權力為個人私有物,利用自身擁有的政府公共權力來謀取個人非正當額外利益的行為。權力的腐化墮落往往是從公權力的“個人化”開始的,部分領導干部以公肥私、中飽私囊的行為透支公共利益、損害百姓權益,更引發群眾與政府的尖銳對立和社會價值觀的惡變,破壞了和諧社會的建設。
表現:或將權力變特權,處處搞特殊化;或通過“一支筆”的權力,直接把公家的錢放進自己的腰包;或以變相分獎金的形式私分公款;或公車私用,將公共資源作為私人財產,揮霍浪費;或利令智昏大肆索賄受賄,謀求不正當利益;或官商勾結,合作共謀黑色利益鏈;或把官帽當做商品,賣官謀利,等等。
典型案例:劉鐵男貪腐案。劉鐵男,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原黨組成員、副主任,59歲,山西祁縣人,曾被曝出包養多個情婦,查出多個銀行賬號,存款高達千萬。2013年8月8日,因嚴重違紀違法被開除黨籍和公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