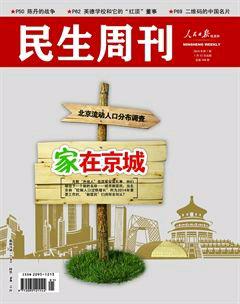扶貧體制要打破城鄉分割
嚴碧華
2013年末,審計署的一則公告在扶貧領域炸開了鍋,指向的正是近年來屢被垢病的部分地區挪用和截取扶貧資金問題。
公告公布了對部分地區2010至2012年財政扶貧資金分配管理和使用情況的審計結果,涉及廣西、云南、貴州、陜西、甘肅、寧夏6省區的19個國家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
審計結果顯示,這些縣普遍存在著虛報冒領、擠占挪用扶貧資金等問題,有的甚至將扶貧資金用于請客送禮及搞形象工程。
問題不止于此。
《民生周刊》記者采訪時,基層干部亦反應一些扶貧項目“水土不服”,無法準確識別貧困對象,扶貧力量“撒胡椒面”不解渴,條塊分割的資金難以整合,“戴帽子”的扶貧資金規定太死等。
比如在湖南省吉首市排綢鄉,近年來用扶貧資金建了幾百個沼氣池,但大部分卻成了擺設。因為山多田少,青壯年勞力大都外出務工,沼氣池所必需的人畜糞便極少。
2013年,該鄉又分了幾十個沼氣池的建設指標,但臨近年底,該鄉黨委書記李擁平還苦于難以落實。
同樣在排綢鄉,按照“兩項制度銜接”政策,每人每年400元的標準扶貧到戶,發展種植和養殖等產業。但按戶均4口人計算,每戶1600元,顯然很難發展產業。
“許多村民拿到錢,也就是逢年過節買幾斤肉、打幾壺酒的事。”李擁平如此坦言。
此外,排綢鄉每年大約能分到1500人指標的項目資金,共60萬元,但因大部分村民之間貧困差別不大,很難區別,容易產生矛盾。于是,有的村就曾采取向上報名單把錢領回來,最后給村民平分的方式來解決。
李擁平也意識到這樣操作,難以從根本上解決問題,于是想把上述資金整合,因地制宜幫助村民發展茶葉產業,但不符合資金使用規定。
“扶貧供需之間存在脫節。”吉首市委書記秦國文向《民生周刊》記者表示,現在地方要項目概括起來,也就三種情況——為項目而項目,為困難而項目,為發展而項目。“后者是地方最需要的,也是有利于從根本上解決貧困問題,但往往最難要到項目。”
《民生周刊》記者此前在多地調研發現,條塊分割的資金管理和投入模式,使得整合面臨許多不可逾越的障礙。一位基層干部反映,針對于國家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每年通過各種渠道有好幾億元的扶貧資金,但真要發展什么產業,整合幾千萬都很難。
這些現象指向的深層次問題是什么?如何擺脫扶貧—脫貧—返貧—再扶貧”的惡性循環,而做到真正有效扶貧?這些問題擺上了決策者的案頭,也引起了扶貧領域專家的高度關注。
李小云是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院長,同時也是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專家咨詢委員會專家。
對于扶貧領域發生的上述問題,他感同身受。2013年,他領導的研究小組在調研中發現,前幾年建的許多扶貧設施已經成為擺設。“這說明什么問題?要么項目不適應當地發展,或者相比在外打工來說不劃算。”
調研中,他們也發現,真正地方需要的資金,可能因為條條框框限制太多而無法實施,
“我們現在為了管理財政資金,非常嚴格,但扶貧是非常多元化的實踐活動,從資金管理的角度進行項目管理的形式本身沒錯,但忽視了各地方甚至到村和村之間的需求都不一樣,很難按照一個統一標準的項目要求進行。”
1月5日,在接受《民生周刊》記者專訪時,他表示開發式扶貧是在80年代針對巨大的貧困人口,同時國家又無力采用直接的收入轉移方式扶貧的條件下采用的一種折中的扶貧方式。
“持續了30多年的開發式扶貧依托市場的力量對緩解貧困起到了巨大作用,但在當前中國經濟社會新的格局下,已經難以繼續發揮有效的緩貧作用。”他進一步表示,過去30年,社會經濟結構發生很大變化,但農村扶貧戰略基本框架沒有發生變化。事實上,延續30多年的農村開發式扶貧已經不能適應農村迅速轉型的需要,應該考慮調整扶貧戰略。
“鄉村社會的快速轉型正在導致開發式扶貧承載主體的缺失,勞動力的機會成本導致扶貧開發所扶持的產業缺乏足夠的激勵機制,開發式扶貧到戶政策設計與新形勢下的致貧原因相脫節,扶貧資源管理的剛性要求制約了地方扶貧創新能力的發揮,鄉村治理轉型導致開發式到戶扶貧戰略到基層缺乏實質性的監督。”李小云說,開發式扶貧戰略面臨上述五個方面的挑戰。“而解決之道,首當其沖是應該調整開發式扶貧的戰略政策,打破扶貧政策的城鄉分割和扶貧措施的二元格局,推動形成大扶貧格局。”
民生周刊:審計署在19個國家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查出違規問題金額2.34億。問題的產生,可能有諸多原因,比如個人法制觀念淡薄,扶貧點多面廣監管難等。在你看來,最主要的的原因是什么?
李小云:我不了解審計結果的具體情況。根據我這么多年對扶貧工作的研究, 我認為真正意義上的財政扶貧資金的貪腐應該說比較少。主要是所謂的“制度性違規”,而制度性違規的發生主要是政策和規定脫離實際,加上地方和部門行政裁量的空間較大以及違規風險的個人損失不大等方面造成的。
我了解的大部分情況是財政扶貧資金使用管理的剛性與各個地方實際不同所要求的彈性之間存在矛盾。中央的管理相對省來說不適應,而省的規定相對縣來說也不適應,縣相對鄉和村也不適應。很多地方為了更好地使用資金,往往容易導致“違規“。
民生周刊:前不久,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六次會議舉行聯組會議,結合審議國務院關于農村扶貧開發工作情況的報告進行專題詢問。專題詢問中,如何打破“扶貧-脫貧-返貧-再扶貧”的惡性循環、走出“年年扶貧年年貧”的怪圈問題受到關注。你認為陷入惡性循環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李小云:之所以為會出現惡性循環,我認為根本原因在于開發式扶貧戰略已經不適應當前的經濟社會發展情況。首先,對于絕對貧困人口的扶持力度不夠,現在屬于保護式扶貧范疇的各種資源很多,但分散管理,標準不一,無法集中在真正的窮人身上,所以出現年年扶貧年年窮。其次,農村開發式扶貧主要針對所謂的低收入或者相對貧困的群體,而現行的開發式扶貧措施無法有效瞄準這個群體,他們在城鄉之間高度流動,高度脆弱,他們的生計更多地取決于宏觀經濟的變化,現行農村開發式扶貧無論從其設計還是力度上都無法有效地緩解。
此外,由于農村勞動力大量流失,留守在家的基本是老人、婦女和小孩,而開發的承載者需要有勞動能力和一定知識的勞動力。這樣必然會造成扶貧開發項目不接地氣,難以有好的效果。
民生周刊:農村開發扶貧戰略不適應當前經濟社會發展主要還表現在哪些方面?
李小云:第一, 勞動力的機會成本導致扶貧開發所扶持的產業缺乏應有的動力機制。在當前經濟背景下,農業和非農產業以及農業內部傳統種養業和其他農業之間的比較優勢差距日益增大,傳統種養業的收益越來越少,各地到戶的開發式扶貧仍然以發展農戶種養業為主,造成從事扶貧開發所支持的產業活動機會成本遠遠高于從事其他行業,扶貧開發的扶持難以對農戶形成有效的行動推動力。此外,在開發式扶貧資金總量約束下,貧困村和貧困人口獲得資金扶持通常都是年度性或者一次性,無法像其他扶持政策那樣能夠提供持續的扶持和支持,難以形成有效的脫貧動力。
第二, 開發式扶貧到戶政策設計與新形勢下的致貧原因相脫節。開發式扶貧到戶政策在設計上缺乏有效的創新,在扶貧方式上長期都是以支持農戶發展產業、農民培訓、移民搬遷以及危房改造等,雖然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部分農戶在生產生活中遇到了困難,但是這些方式和農戶致貧原因之間似乎并無顯著聯系,而這也是扶貧資源瞄準偏離的根本原因。
第三, 扶貧資源管理的剛性要求制約了地方扶貧創新能力的發揮。扶貧資金專項劃撥和嚴格按照審批使用和管理使得扶貧資金難以滿足不同地區千差萬別的資金需求。為了防止縣鄉兩級濫用、挪用扶貧資源,大部分扶貧資金都是通過專項轉移支付到縣,縣鄉兩級必須嚴格按照資金的投向來使用,雖然保證了扶貧資金使用的財務安全,但是卻極大限制了縣鄉兩級扶貧工作的創新能力和應對不同貧困特點和問題能力,全國不同區域在扶貧方式上呈現出一致性的趨勢和特點,這顯然不符合不同地域間的貧困問題差異的現實。
第四, 鄉村治理轉型導致開發式到戶扶貧戰略到基層缺乏實質性的監督。扶貧的直接利益主體的缺失,能夠真正參與到村級扶貧決策的基本上都是老人和婦女,這一方面導致了各種扶貧討論和監督會議缺乏直接的扶貧主體的參與,一方面也導致了村民代表和村委會之間權利的不平衡,村委會和留在村莊的精英群體力量過強,村民監督成為虛設,這為扶貧資源的鄉村精英捕獲和資源分配不合理埋下了伏筆。
民生周刊:既然農村開發式扶貧戰略已經存在很多問題,難以完成新形勢下的扶貧任務,那究竟該如何調整?
李小云:建議研究統籌城鄉和整合不同部門的整體性扶貧戰略,改革現行城鄉分割的扶貧管理體制,建立統籌城鄉扶貧一體化的大扶貧協調機制。
概括起來也是五個方面:研究全國統一的保護窮人的政策,制定適合不同地區,城鄉一體的,基于不同地區和城鄉生活水平的貧困線(不同地區和城鄉之間貧困線因為不同地區和城鄉人口擁有的生計資產可以不同);將不同類型的保護性扶貧措施集中供應處于貧困線以下的人口,解決目前對絕對貧困人口的扶持力度不夠的問題;將現行農村扶貧開發戰略調整為“落后地區經濟,社會和環境發展計劃”;將現行專項扶貧資金調整為以促進能力提升和提供公平競爭條件的普惠性計劃,避免捕獲,挪用和腐敗;推動針對農村扶貧的社會服務購買,發育活躍在貧困地區的民間組織的發展,從而彌補鄉村公共服務能力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