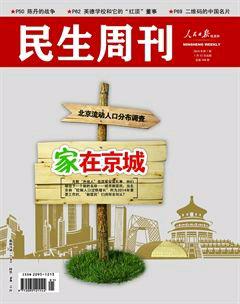留駐的“城市新居民”
崔靖芳 陳沙沙


侯佳偉發現,自己長期以來一直研究的北京市流動人口相關課題,最近發生了許多變化。
“7年前,我曾做過初步判斷,北京市超過1萬人的流動人口聚集地會大量增加。不過,最新的數字還是令人震驚,五環內幾乎所有街道流動人口數量都超過了1萬人。如果將這些街道在北京市地圖上一一標注出來,整張地圖會被密密麻麻的點所布滿。”
身為中央財經大學社會發展學院副教授,侯佳偉的新發現得到了北京市人口研究所副所長馬小紅的印證。
近日,北京市人口研究所發布了《北京人口發展研究報告(2013)》,報告中最新數據顯示,北京市常住人口已達到2069.3萬人,遠遠超出了北京市提出的1800萬人口“紅線”。馬小紅說:“流動人口膨脹是常住人口增長的主因。”
2000年以來,北京市流動人口總量加速膨脹,2012年增長到773.8萬,12年間增加了517.7萬。按照最新數據統計,北京市每3個人中就有1人來自外省市。
數以百萬計的外來人口不僅在京城的各個角落聚居,在我國,幾乎所有的大中型城市都出現了流動人口聚集地。隨著這種聚集地數量的增加,各種情況也愈發復雜。
“擴編”加速度
作為北京市哲學社會科學“十一五”規劃項目,“北京市外來人口聚集區問題研究”項目由國家衛計委專家委員會委員、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院長翟振武主持。當時,侯佳偉是翟振武研究團隊的一員,負責開展“2006年北京市1‰流動人口調查”的設計和協調工作,并在調查基礎上開展關于流動人口聚集地的研究。
2007年,侯佳偉開始對北京市流動人口聚集地進行跟進式調查,至今已有7年。7年間,無論研究者還是研究對象,都發生了許多改變。
侯佳偉在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讀完經濟學博士后,到中央財經大學社會發展學院擔任副教授。她的身份雖然從學生變成了老師,但研究方向卻沒有改變,對于流動人口聚集地的研究也更加深入。
隨著調研的不斷深入,侯佳偉發現,在北京,流動人口聚集地不僅越來越多,范圍也在不斷擴大。
1989年9月9日,《北京晚報》在第一版報道了“浙江村”,這是媒體對于北京流動人口聚集地的第一次公開報道。
隨后,“河南村”“安徽村”“福建村”和“破爛村”“畫家村”“眼鏡村”等陸續出現。這些流動人口聚集地或以人員的來源地命名,或以職業命名,它們既不是自然村落,更不具有行政編制,僅是進京務工經商的流動人口自發選擇集中居住的地區。
最初,這些“編外村”通常集中在城市近郊區,主要因為這里房租低廉、交通便捷、管理松散。
上世紀80年代初期已初具規模的“河南村”,原址位于北京市海淀區東升鄉二里莊。這里又被稱為“破爛村”,只因當時住在這里的流動人口多從事與廢品回收有關的職業。
與“河南村”一樣,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這些為數不多的“編外村”主要分布在北京市二環和三環沿線。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2000年。
作為北京市人口政策制定的參與者之一,幾年前,馬小紅也對流動人口進行過抽樣調查。馬小紅發現,2000年后,隨著改革開放程度的不斷提高,北京市的流動人口出現了一個加速膨脹期。2001年,北京市流動人口年增長量為6.7萬。
侯佳偉與馬小紅的研究結果得到了相互印證。
在研究過程中,侯佳偉也發現,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時,流動人口向郊區集中的趨勢凸顯出來。流動人口聚集地開始從原被稱作“城區”的東城區、西城區、崇文區、宣武區向原被稱作“郊區”的朝陽區、海淀區、豐臺區、石景山區拓展。
到2005年底,隨著北京市城鎮化進程加速,流動人口聚集地的外擴趨勢更加明顯,“城區”和“郊區”流動人口比重均有所下降。原被稱為“遠郊區”的通州區、順義區、大興區、昌平區、房山區和亦莊開發區,則成為流動人口聚居的新選擇。
而最新的數據,幾乎超出了侯佳偉多年的研究預期——五環內幾乎所有街道的流動人口數量都已過萬,換句話說,流動人口已遍布京城的每一個角落。那么,是否還存在所謂的緣聚型流動人口聚集地?
“老鄉”全城見
帶著這樣的疑問,侯佳偉開始梳理重點跟蹤的幾個“編外村”。在梳理過程中,她又發現了一個新現象。
“浙江村”曾是北京城內流動人口聚集地中名氣最大的,其最大特點就是“扎堆”,地緣鄉緣情結濃厚。
“直到上世紀90年代初期,‘浙江村’的聚居程度實際上愈發緊密了,但是到了1995年,情況就發生改了改變。”侯佳偉說。
自當地政府開啟徹底整治起,“浙江村”的聚居形態被打破,自此他們開始散居于北京南城一帶。
與“浙江村”類似,原緊密聚居在北京市東升鄉二里莊的“河南村”,因1992年整治而搬遷至八家村一帶。這次搬遷使得河南人的聚居程度有所減弱,分散居住到八家村的4個自然村中。
2003年,八家村內由河南人經營的廢品回收貨場,因嚴重困擾村民而被陸續拆除,自此,河南人開始向更偏遠的地區搬遷,散居于京城。
除“浙江村”“河南村”,其他“編外村”的聚居情況也被逐步打破,呈現出同樣的發展趨勢。
作為侯佳偉的老師,翟振武教授認為:“地域范圍越小,緣聚型的概率越大;地域范圍越大,混居型的可能性越大。”
侯佳偉通過7年間對流動人口聚集地的實地調查發現,近些年,緣聚型聚集地越來越少,普遍成為混居型聚集地。
“這種現象與北京市產業布局調整以及城市功能疏解等因素有關。”馬小紅說。
對于馬小紅的觀點,侯佳偉表示贊同:“近些年,北京大力發展城市新區,同時進行舊城改造,通過建設科技園區、新城區,把核心城區的產業和人口逐漸向城市新區轉移,再加上核心城區生活成本不斷走高,也使得人口隨之流入城市新區。正因如此,這種外推使得流動人口因地緣、鄉緣聚居的聚集地不斷減少。”
剔除緣聚因素,這些來自全國各地、混居在京城各個角落的流動人口,早已不知不覺成為北京這座城市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留下”而非“流動”
在循序漸進的調研中,研究者們腦海中逐漸形成了一個新的概念——城市新居民。他們生活在城市里的各個角落,早已楔入現代都市文明之中;他們大都屬于改革開放后社會流動加快背景下形成的移民階層。于是,馬小紅將研究視野擴展到流動人口群體中最難與城市融合的農民工。
侯佳偉的思路是在不斷的調研過程中,隨著調研客體的變化而形成的。“我們發現這種變化里出現了一個新情況,那就是流動人口升級換代了,這不得不提到整個農民工的發展歷程。” 人口遷移的歷史幾乎與人類歷史一樣久遠。人口遷移的最主要原因是為了生存,直到現在,最核心的問題依然是生存問題。
1958年,新中國通過戶籍制度將城鄉人為分割開,將人口固定在各自的地方,不再有遷移。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糧票、油票、布票慢慢放開,人口又開始了自由遷移。
“大規模的人口流動是在2000年以后,在此之前流動人口被稱作‘盲流’,就是盲目流動的意思。”侯佳偉解釋稱。
2000年后,流動人口規模迅速膨脹,引起政府和學術界的高度關注。有專家發現,他們的流動并不盲目,而是有規律的,是向著經濟發達的地區流動。農民變成了工人,所以叫“農民工”。
在侯佳偉對這一群體進行調研的同時,北京市委黨校、北京社科院也于同一年,在全北京選取了4000個樣本進行抽樣調查,發現了許多共同規律。其中之一,便是流動人口不再流動。
他們發現,流動人口不再流動,而是長期居住在北京。此時專家認為,“農民工”這個稱謂已經不再適合這個群體,于是提出了一個新概念——城市新居民。
這也正是侯佳偉研究這一群體的深層次邏輯——“與以前的‘農民工’相比,城市新居民有些出生在農村,卻一天農活也沒干過;有些甚至生在城市長在城市。”
在文化資本、經濟資本和社會資本方面,城市新居民較父輩具有明顯的優勢,這正是侯佳偉所謂的“升級換代”;另一方面,這些新居民卻無法擺脫流動人口的頭銜,面臨身份無法認同的尷尬。
侯佳偉認為,有兩個概念不得不提,即流動人口與遷移人口。兩個概念有相同之處,也有區別。相同的是,隨著空間和時間的改變,離開戶籍地半年以上,戶籍地和現居住地不一致;而區別則在于戶口,戶口隨人同時遷移就是遷移人口,否則就是流動人口。
“改變城市新居民的境遇,讓他們更好地融入城市,必須進行戶籍制度改革。”馬小紅說,當事實的發展已經超越了政策的預期,頂層設計就必須做出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