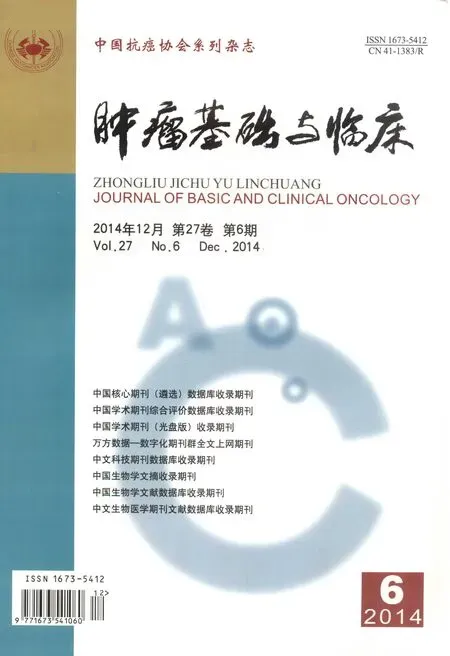食管癌生物治療的研究進展
金懷亮,岳文彬,翟鳳鈺
(1.新鄉醫學院,河南 新鄉453000;2.濮陽市油田總醫院腫瘤科,河南 濮陽457001)
食管癌是常見的人類消化道惡性腫瘤之一,其死亡率為90%,據估計,2008年全世界約有482 300例患者被確診為食管癌,死亡人數約為406 800 人,在腫瘤死亡譜中居第5 位[1]。食管癌是食管黏膜上皮或腺體發生的惡性腫瘤,其發生是由多因素導致的,其中與患者的不良飲食習慣、環境因素及遺傳因素密切相關;早期食管癌在臨床上一般沒有癥狀,很難發現,到中晚期出現進行性吞咽困難后,往往才會到醫院進行診治,因此許多患者錯過了最佳治療時機。目前,沒有遠處轉移的、能夠切除的食管癌仍以手術為主要治療手段。即便如此,食管癌患者的中位生存期也只有18 個月左右,而5 a 生存率為23%。不過隨著科學技術、生物免疫學及生物學技術的迅速發展,多學科的綜合治療越來越被重視[2-4],其中新興的生物治療主要是以腫瘤免疫治療為核心,向患者體內引入生物制劑和(或)活性細胞,以此調節患者機體的生物學反應,并使之有利于宿主直接殺傷或者抑制腫瘤細胞的生長,從而達到治療腫瘤的目的,本文現對食管癌在生物學治療方面的研究綜述如下。
1 生物治療的概念、作用及特點
生物治療是一種新的腫瘤治療模式,是利用生物工程的方法,通常指通過調動機體的防御機制或借助生物制劑的作用,以調節機體的生物學反應,從而抑制或阻止腫瘤生長的治療方法,主要治療手段包括抗體治療、細胞因子治療、過繼免疫治療、疫苗治療以及基因治療等。其具有十分完備的監視功能,并具有安全、有效、毒副反應低等特點,但腫瘤患者特別是晚期患者的免疫功能處于抑制狀態,不利于腫瘤的控制和清除。生物治療可以殺滅殘存的腫瘤細胞,并且可以提高患者的生活質量以及機體的免疫和造血功能,能夠增強放化療的耐受及治療疾病。
2 免疫治療
2.1 IFN 干擾素(interferon,IFN)是由某些病毒感染后的動物細胞分泌的具有抗病毒功能的宿主特異性糖蛋白。細胞在感染病毒后分泌的干擾素能夠與周圍沒有感染的細胞的某些相關性受體作用,促進這些細胞合成抗病毒蛋白,從而防止進一步的感染,因此起到抗病毒的作用,但其對已感染的細胞沒有幫助。IFN的作用不僅僅只局限在抗病毒領域,同時也是第1 個應用于腫瘤治療的細胞因子,其抗腫瘤作用是多方向性的,對多種腫瘤細胞均有抗腫瘤效應,如肝細胞癌、纖維瘤、食管癌、黑色素瘤等。IFN 也可以通過延長細胞周期,從而影響癌基因的表達和腫瘤細胞的分化,而且可活化宿主免疫系統中吞噬細胞、單核細胞、NK 細胞,使其細胞毒作用大大增強,還可以促進這些細胞分泌多種抗腫瘤的細胞因子,這些作用的發揮可影響腫瘤細胞的血供,還可降低細胞膜的通透性。目前,對實體瘤的治療效果而言,單獨應用IFN 的效果并不是很滿意,據統計,IFN 只對部分食管癌有效果[5]。近年來,越來越多的研究著眼于IFN-γ 抑制食管癌細胞的增殖作用機制,IFN-λ 屬于干擾素家族,是一種新發現的Ⅲ型干擾素,主要在抗原遞呈細胞中表達,主要包括3 個成員:IFN-λ1、IFN-λ2 及IFN-λ3,同時IFN-λ 具有種屬特異性,在人類中,IFN-λ 主要由3 個具高度同源性但又各具特異性的基因來編碼,但在小鼠中,IFN-λ1是由假基因編碼,僅僅只有IFN-λ2 和IFN-λ3 的表達[6]。IFN-λ 可以誘導MHC-I 類分子和抗病毒基因的表達,也可以抑制神經內分泌癌細胞或是結腸癌細胞增殖的生物學活性,還對食管癌細胞具有抑制增殖作用。
Li 等[7]研究發現IFN-λ1 對人食管癌細胞株(TE-1、TE-2、TE-10、TE-11、YES-2、YES-4、YES-5、YES-6、T.Tn)所表達的9 種IFN-λ 受體均有抑制作用,發現IFN-λl 可以抑制TE-11、YES-5 和T. Tn 的生長,其作用機制為直接導致細胞的凋亡或誘導處于G1期的細胞停滯。為了進一步研究IFN-λ 對抗食管癌的作用,將IFN-λ1 或者IFN-λ2 的基因與腺病毒的基因整合起來,形成Ad/IFN-λ,然后整合基因轉染對IFN-λ 敏感的人食管癌YES-2 細胞,結果發現被轉染的細胞上MHC-I類分子的表達量增多、caspase-3 和聚ADP 核糖聚合酶(poly ADP-ribose poly-merase,PARP)裂解、sub-G1期延長,這些均導致細胞生長受到抑制,由此腫瘤細胞的生長速度減慢。對照組用Ad/IFN-λ 轉染缺乏IFN-λ1 受體的纖維母細胞,導致被轉染的YES-2細胞死亡。同時,Li 等[8]把YES-2 細胞接種到裸鼠身上,而且同時注射了轉染的Ad/IFN-λ 纖維母細胞,結果出現了腫瘤細胞生長速度變慢,這再一次證明了IFN-λ1 和IFN-λ2 具有抗食管癌的作用。同時,也有研究[9]報道,IFN-λ 對食管癌細胞的增殖有抑制活性,其機制可能是通過抑制細胞周期及細胞凋亡。
2.2 NKG2D NKG2D 是NK 細胞表面主要的活化性受體之一,與腫瘤細胞表面的相應配體(MICA)結合后,可以使NK 細胞活化,從而使NK 細胞具有細胞毒活性,可以說NKG2D 的活化決定了生物體抗腫瘤細胞的免疫水平[10]。MICA 分子的表達可以作為治療腫瘤預后的一項指標。周智鋒等[11]通過對中晚期食管癌術后行化療聯合NK 細胞治療發現,化療同步NK細胞治療MICA 陽性的患者生活質量明顯提高,并且由化療帶來的一些毒副反應,如外周神經毒性及白細胞減少等明顯改善,而且最重要的是疾病的生存時間及疾病的進展時間明顯延長。
2.3 其他因子 另外,在食管癌的生物治療中還包括一些生物學應答調節劑,比如說,SART-1259 抗原和CEA 在許多食管癌細胞中均可表達,這些因子可以被特異性的抗體或免疫活性細胞所識別。目前,在臨床上運用食管癌患者中的云芝多糖,經研究發現其生存期顯著延長。
3 分子靶向治療
正常細胞與腫瘤細胞間存在分子生物學上的差異,分子靶向治療就是利用這些差異,運用抑制新生血管生成、封閉受體、阻斷信號傳導通路等方法作用于腫瘤細胞上特異性的位點,從而抑制腫瘤細胞的生長及促進腫瘤細胞的凋亡。分子靶向治療藥物的選擇性高、特異性強,不易于產生耐藥性,其安全性比一般化療藥物強,是現在腫瘤治療的新思路。近年來,隨著分子生物學的不斷發展,分子靶向治療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關注,并且已經在大腸癌、肺癌等疾病上得到了成功驗證,所以其也有望成為治療食管癌新的方法之一[12]。分子靶向治療配合放化療能夠使食管癌患者的生存率得到提高,在食管癌方面,分子靶向治療在多個靶點已進行了I、Ⅱ期的臨床試驗,比如表皮生長因子受體(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EGFR)、血管內皮細胞生長因子等。
3.1 EGFR 酪氨酸激酶抑制劑 厄洛替尼、吉非替尼為酪氨酸激酶抑制劑,在較早的一些Ⅱ期臨床試驗中表明,兩者在食管腺癌及食管與胃連接處的腺癌有一定的研究價值。近期研究者運用吉非替尼聯合放療治療80 例食管癌患者,在放化療前堅持4 周服用吉非替尼250 mg·d-1,行腫瘤切除術后再服用2 a,對照組93 例食管癌患者只進行了普通的放化療,未加用吉非替尼,研究結果表明2 組患者的生存率及遠處轉移率差異無統計學意義,并且未增加放化療的毒副反應,但其臨床應用價值仍需進一步驗證[13]。Li 等[14]研究發現,對于局部進展期食管癌,在采用放化療的同時加用厄洛替尼,能夠使局部控制率和2 a 生存率都得到改善,并且對患者來說其毒副反應是可以耐受的。厄洛替尼聯合改良的FOLFOX6 方案治療食管癌是有效的,且毒副反應是可以接受的[15]。厄洛替尼對食管鱗癌有一定的治療效果,而且在表達EGFR 較少的腫瘤中,EGFR 的表達情況并不代表治療效果的好壞。西妥昔單抗是一種IgG1單抗,主要針對EGFR,西妥昔單抗在競爭性結合特定位點后,能夠發揮抑制腫瘤細胞的生長作用,其在結腸癌中的療效已經得到了認可。Pinto 等[16]研究發現,在化療聯合西妥昔單抗治療胃食管交接處的腺癌及胃癌時,認為西妥昔單抗與順鉑及泰素帝一起用的時候,能夠改善胃食管交接處的腺癌及胃癌的治療效果,并且沒有增加順鉑和泰素帝的毒副反應,但是對該種疾病的進展和總的生存時間并沒有改善。最新的一項前瞻性多中心研究結果顯示,西妥昔單抗能夠使68%可切除的局部進展期的食管癌患者達到近似完全緩解或完全緩解,且在術前應用西妥昔單抗聯合放化療并不增加患者的術后死亡率。因為該研究顯示:西妥昔單抗對組織的緩解率和對R0的切除率比較高,現在該藥正在進行Ⅲ期臨床研究實驗。
3.2 血管內皮生長因子 血管內皮生長因子不管在生理情況還是在病理情況下,都是一個很關鍵的調節因子,在乳腺癌、肺癌及大腸癌等許多實體瘤中存在過表達。現在對于血管內皮生長因子的應用也只限于I、Ⅱ期的臨床試驗。抗血管內皮生長因子單抗貝伐單抗與化療聯合治療胃食管腺癌患者的2 a 生存率為37%,對于胃食管腺癌的治療,貝伐單抗與順鉑、泰素帝等聯用,不僅毒副反應可以耐受,而且效果顯著[17]。
4 基因治療
基因治療是從分子水平來認識疾病的,并且找到特異的靶點進行治療,與很多疾病一樣,食管癌的發生也被認為與遺傳、基因有關。任力強等[18]研究發現,在體外用維甲酸處理食管癌細胞,然后經分離后可得到RA538 基因,最后將RA538 基因的cDNA 轉移到食管癌細胞內,發現被轉移的食管癌細胞增殖受到抑制,而且出現細胞的脫落及死亡,這表明RA538 在治療食管癌中有應用價值。另P16 是一類抑癌基因,在腫瘤細胞中這種基因往往是缺失的或突變的。彭瓊等[19]研究發現,食管癌細胞被轉染了P16 基因的cDNA 后,腫瘤細胞的生長速度變慢,增殖數量及體積均變小,這就說明在食管癌治療中可把P16 基因作為治療的靶點。另外,還有種藥叫抗腫瘤基因藥,其以腺病毒為載體,把P53 基因導入食管癌細胞內,從而提高瘤體細胞對放療的敏感性。在鼻咽癌的治療中,該種藥的應用已取得了比較好的效果,因為鼻咽癌大多為鱗癌,而食管癌大多也是以鱗癌為主,那么把這種藥用于食管癌帶來了啟示,路平等[20]的研究表明,將重組人P53 腺病毒注入瘤體內,對于需放療的患者來說可顯著增加患者對放療的敏感性。
5 前景與展望
20 世紀80年代,美國學者Oldham 提出了生物反應調節理論,以后生物治療成為繼手術、放療、化療之后的第4 大腫瘤治療模式,并因其安全、有效、毒副反應低等特點,被認為是本世紀腫瘤綜合治療模式中最活躍、最有前途的手段。生物治療相比較于其他治療手段,具有其獨特的優勢。腫瘤的傳統治療側重于腫瘤本身的生物學特性,如采用手術、放療局部控制腫瘤,通過化療控制復發和遠處轉移。但手術不能解決腫瘤細胞的擴散、轉移問題;而放化療是一把雙刃劍,在殺傷腫瘤細胞的同時,對正常細胞以及機體的免疫、造血功能也有損害。然而對于食管癌的生物治療來說,其仍尚處于實驗研究和臨床試驗階段,尤其是基因治療還處于起始階段,因此,生物治療還只是抗食管癌的一種輔助方法,但是隨著病因生物學和基因工程技術的提高,比如隨著腫瘤疫苗的研究、單克隆抗體導向治療的研究、基因治療載體的研究等問題的突破,食管癌的生物治療將成為未來研究的一個主要方向,并將使食管癌內科治療目的從姑息發展轉變成根治。
[1]Jemal A,Bray F,Center MM,et al.Global cancer statistics[J].CA Cancer J Clin,2011,61(2):69-90.
[2]邵令方,王其彰.新編食管外科學[M]. 石家莊:河北科學技術出版社,2002:681-686.
[3]魏礦榮,練秋紅,劉靜,等.食管癌流行概況[J].中華內科雜志,2012,5l(2):156-158.
[4]赫捷.規范化診治是推動我國食管癌臨床和研究發展的必由之路[J].中華腫瘤雜志,2012,34(4):241-244.
[5]曹蕾.癌癥新療法—細胞因子療法[M].北京:北京科學技術出版社1993:13.
[6]Donnelly RP,Kotenko SV. Interferon-lambda:a new addition to an old family[J].J Interferon Cytokine Res.2010,30(8):555-564.
[7]Li Q,Kawamura K,Ma G,et al.Interferon-lambda induces G1 phase arrest or apoptosis in oesophageal carcinoma cells and produces anti-tumour effects in combination with anti-cancer agents[J]. Eur J Cancer,2010,46(1):180-190.
[8]Li Q,Kawamura K,Okamoto S,et al.Adenoviruses-mediated transduction of human oesophageal carcinoma cells with the interferon-λ genes produced anti-tumour effects[J]. Br J Cancer,2011,105(9):1302-1312.
[9]趙鑫,齊義新,魏林,等. IFN-λ 對人食管癌細胞增殖的抑制作用及機制[J].山東醫藥,2011,51(39):6-8.
[10]Raulet DH,Gasser S,Gowen BG,et al.Regulation of ligands for the NKG2D activating receptor[J].Annu Rev Immunol,2013,31:413-441.
[11]周智鋒,柳碩巖,鄭慶豐,等.NKG2D 配體在中晚期食管癌患者術后NK 細胞免疫治療中的作用[J],中國腫瘤臨床,2013,40(22):1373-1377.
[12]Jiang Y,Kimchi E,Ajani JA.Localized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of the esophagus:bimodality or trimodality approach?[J]. Future Oncol,2009,5(2):157-161.
[13]Rodriguez CP,Adelstein DJ,Rice TW,et al. A phase Ⅱstudy of perioperative concurrent chemotherapy,gefitinib,and hyperfractionated radiation followed by maintenance gefitinib in locoregionally advanced esophagus and gastroesophageal junction cancer[J]. J Thorac Oncol,2010,5(2):229-235.
[14]Li G,Hu W,Wang J,et al.Phase Ⅱstudy of concurrent chemoradiation in combination with erlotinib for locally advanced esophageal carcinoma[J].Int J Radiat Oncol Biol Phys,2010,78(5):1407-1412.
[15]Wainberg ZA,Lin LS,DiCarlo B,et al. Phase Ⅱtrial of modified FOLFOX6 and erlotinib in patients with metastatic or advanced adenocarcinoma of the oesophagus and gastro-oesophageal junction[J].Br J Cancer,2011,105(6):760-765.
[16]Pinto C,Di Fabio F,Barone C,et al. Phase Ⅱstudy of cetuximab in combination with cisplatin and docetaxel in patients with untreated advanced gastric or gastro-oesophageal junction adenocarcinoma(DOCETUX study)[J]. Br J Cancer,2009,101 (8):1261-1268.
[17]Shah MA,Jhawer M,Ilson DH,et al. Phase Ⅱstudy of modified docetaxel,cisplatin,and fluorouracil with bevacizumab in patients with metastatic gastroesophageal adenocarcinoma[J].J Clin Oncol,2011,29(7):868-874.
[18]任力強,楊曉光,王秀琴,等.RA538 基因功能片段的克隆和對HL-60 細胞的作用[J]. 中華血液學雜志,1995,16(5):229-231.
[19]彭瓊,金順錢,陸士新,等. p16 基因抑制食管癌細胞生長的研究[J].中華腫瘤雜志,1999,21(3):175-177.
[20]路平,苗戰會,陸志紅,等.內鏡下瘤體內注射p53 基因聯合放射治療治療食管癌15 例[J]. 鄭州大學學報:醫學版,2008,43(6):1101-1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