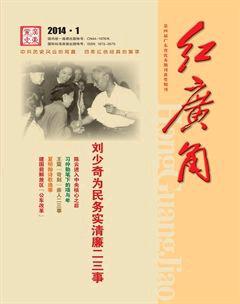“文革”前京劇《紅燈記》對(duì)香港的影響
詹延欽
作為中國(guó)二十世紀(jì)的紅色經(jīng)典劇目,革命現(xiàn)代京劇《紅燈記》無論就其思想性還是藝術(shù)性來說都堪稱革命文藝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大凡四十開外的人一定不會(huì)忘記當(dāng)年革命現(xiàn)代京劇《紅燈記》演出時(shí)萬人空巷的盛況。《紅燈記》不但在大陸產(chǎn)生那么大的影響,而且對(duì)香港也造成了巨大的影響。
《紅燈記》講述的是在抗日戰(zhàn)爭(zhēng)時(shí)期的東北敵占區(qū),我地下黨工作者李玉和接受向柏山游擊隊(duì)轉(zhuǎn)送密碼的任務(wù)。由于叛徒的出賣,李玉和遭日寇殺害,李玉和的女兒鐵梅繼承父志,將密碼送上山,游擊隊(duì)殲滅了追趕鐵梅的日寇的故事。京劇《紅燈記》在60年代初改編后不久立即脫穎而出。1964年11月6日晚,毛澤東主席在劉少奇、鄧小平等人陪同下在人大小禮堂再次觀看了《紅燈記》,對(duì)這個(gè)戲十分贊賞。不久江青又來到中國(guó)京劇院說:“《紅燈記》主席通過了,你們到南方去一下吧,擴(kuò)大影響。”1965年2月,中國(guó)京劇院副院長(zhǎng)張東川和阿甲一起帶劇組南下公演。所到之處,觀眾對(duì)這出戲反應(yīng)之強(qiáng)烈大大出乎劇組的預(yù)料。在廣州東風(fēng)劇場(chǎng)和擁有5000個(gè)座位的中山紀(jì)念堂演出時(shí),不僅場(chǎng)內(nèi)觀眾爆滿,場(chǎng)外也是人頭攢動(dòng)。在深圳演出時(shí),許多香港居民也紛紛跑過羅浮橋來先睹為快。“我家的表叔數(shù)不盡,沒有大事不登門……”,“臨行喝媽一碗酒,渾身是膽雄糾糾……”,劇中的唱詞唱腔一時(shí)響遍大街小巷,為南國(guó)早春注入了一股股革命豪情。同年3月初,劇組揮師北上,在能容納三四千人座位的上海人民大舞臺(tái)連演42場(chǎng),觀眾達(dá)11萬5千人次,打破了該劇場(chǎng)建立以來單個(gè)劇目上演最高紀(jì)錄。《紅燈記》以感人肺腑的愛國(guó)精神和演員精湛的表演在觀眾中留下了深刻印象。不僅觀眾熱看《紅燈記》,各類媒體也爭(zhēng)相報(bào)道關(guān)于《紅燈記》的演出情況。文藝評(píng)論界也掀起了一股《紅燈記》熱。據(jù)當(dāng)時(shí)統(tǒng)計(jì)資料顯示:從1964年初到1965年6月,文藝評(píng)論界發(fā)表評(píng)論文章達(dá)200余篇,稱京劇《紅燈記》是“政治與藝術(shù)完美結(jié)合的好戲” 。
《紅燈記》能夠這么快就來到邊陲小鎮(zhèn)深圳演出并對(duì)香港形成一股強(qiáng)大的沖擊波是完全出乎人們意料的。從1960年3月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fā)前夕的整整7年間,為了消除國(guó)民黨敵特活動(dòng)和港英當(dāng)局對(duì)立行為所造成的海外惡劣影響,中共中央和廣東省委作出決定,通過深圳對(duì)外演出活動(dòng)吸引港澳同胞來深觀戲,增強(qiáng)他們對(duì)新中國(guó)的信心和凝聚力,使他們更好地團(tuán)結(jié)在新中國(guó)的周圍。這段時(shí)間內(nèi)幾乎全國(guó)所有省份的文藝團(tuán)體紛至沓來,使深圳的文化生活達(dá)到了空前的繁榮。劇種既有表現(xiàn)我國(guó)優(yōu)秀藝術(shù)傳統(tǒng)的,又有反映建國(guó)后藝術(shù)上的進(jìn)步和成就,以及黨的“推陳出新”、“百花齊放”文藝方針的。他們的劇目突出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相結(jié)合,內(nèi)容豐富多彩,受到熱烈歡迎。上演過的劇種有芭蕾舞、話劇、歌劇、京劇、越劇、評(píng)劇、豫劇、漢劇、錫劇、潮劇、黃梅戲等。特別是上述的1965年2月春節(jié)期間在深圳演出的《紅燈記》,大大轟動(dòng)了港澳,是繼1964年冬中央芭蕾舞劇團(tuán)的《紅色娘子軍》在深演出后的又一個(gè)熱烈高潮。隨后每一次的演出,也非常熱烈。港澳觀眾不單場(chǎng)場(chǎng)滿額滿座,而且還要求增加演出場(chǎng)次。根據(jù)香港中國(guó)旅行社在代售《紅燈記》等的戲票時(shí)統(tǒng)計(jì),許多香港觀眾買不到票。當(dāng)他們獲得一張戲票時(shí),便感到非常幸福和光榮,很多學(xué)生把到深圳看演出的票稱為“幸福票”,不少工人買不到票時(shí),便跑到深圳來,苦苦要求買票,得到一張“站票”進(jìn)場(chǎng),也感到十分滿足。
在演出中,劇場(chǎng)的熱烈氣氛是少見的,每場(chǎng)或精彩的片段都報(bào)以雷鳴般的掌聲。觀眾由于劇情的感染而熱淚盈眶是普遍的。《大公報(bào)》攝影記者陳跡看了《紅燈記》第一場(chǎng)演出時(shí),沒有拍到幾張照片,事后他說,原因是忙于“抹鏡頭”(拭眼淚)。每次演出結(jié)束,演員謝幕少的三、四次,多的七、八次,有些觀眾,激動(dòng)地跑到臺(tái)前高呼“毛主席萬歲”、“共產(chǎn)黨萬歲”。《紅燈記》的演出,大大地震動(dòng)了香港同胞。當(dāng)《紅燈記》演出時(shí),香港的中間、進(jìn)步報(bào)紙大力評(píng)述推薦,許多著名人士如費(fèi)彝民、李子誦、金堯如等還親自執(zhí)筆,專題評(píng)贊;也有一般的社會(huì)人士撰寫了贊頌的文章,熱烈異常。
香港較有地位的文化界、藝術(shù)界、電影界、戲劇界人士大部分都來看了《紅燈記》,看后都一致稱贊演出的成功。香港老牌電影演員吳楚帆連看數(shù)場(chǎng),完全被緊湊動(dòng)人的劇情和精湛的演技所吸引,看得如癡如醉,連聲叫妙。他說:“這個(gè)戲已經(jīng)創(chuàng)造了一套新的藝術(shù)體系,有些人尚懷疑現(xiàn)代京劇是否看得順眼,他們應(yīng)該來看看了……”香港須生名票友陳中和,過去認(rèn)為絕對(duì)不能把京劇的基本東西運(yùn)用到現(xiàn)代生活中去,認(rèn)為京劇是不能改的,可是,他看了《紅燈記》之后說:“我看了這個(gè)戲,才知道京劇現(xiàn)代戲是高度的藝術(shù)結(jié)晶。京劇傳下來的東西太多了,演現(xiàn)代戲是適合不過的。”香港電影導(dǎo)演盧敦也說:“中國(guó)人創(chuàng)造了現(xiàn)代京劇的藝術(shù),我們值得驕傲。”導(dǎo)演費(fèi)魯伊看了后,認(rèn)為這戲體現(xiàn)了現(xiàn)代京劇的新內(nèi)容、新表現(xiàn),有傳統(tǒng)、有革新,并且說:“豈止是服了,簡(jiǎn)直是五體投地。”這些都表明了京劇現(xiàn)代戲《紅燈記》在觀眾的思想境界里產(chǎn)生了巨大的革命感染力。
革命現(xiàn)代戲的演出,給廣大的香港群眾以現(xiàn)實(shí)的革命教育和精神鼓舞,也推動(dòng)了香港文藝工作的前進(jìn),增強(qiáng)文藝活動(dòng)的革命內(nèi)容和戰(zhàn)斗力。由于受到深圳大演革命現(xiàn)代戲的影響,革命現(xiàn)代戲已為廣大香港觀眾所喜愛,推動(dòng)了香港文藝、戲劇界加速走向演革命現(xiàn)代戲的道路。香港話劇團(tuán)(香港電影界組織的)在1965年曾把《紅燈記》改編為話劇,在香港、澳門演出,而且一再重演,博得很多港澳觀眾的贊揚(yáng);香港南國(guó)粵劇團(tuán)亦曾把《紅燈記》局部改編為粵劇,向工人演出,亦獲得好評(píng)。香港的一些團(tuán)體和學(xué)校,1965年就組織七、八十位青年來深圳向陜西歌舞團(tuán)和四川歌舞團(tuán)學(xué)習(xí)革命歌舞,大大豐富了他們的文娛活動(dòng)。1965年國(guó)慶節(jié)紀(jì)念活動(dòng)中,很多團(tuán)體、學(xué)校的表演節(jié)目,都是從陜西、四川歌舞團(tuán)學(xué)來的,有好幾位香港的音樂家和歌唱家,看過陜西歌舞團(tuán)、上海音樂學(xué)院演出組和四川歌舞團(tuán)演出之后,要求給他們一些革命的樂譜和歌曲,準(zhǔn)備在香港公開表演。每次演出期間,香港長(zhǎng)城、鳳凰電影公司、香港話劇團(tuán)、南國(guó)粵劇團(tuán)的導(dǎo)演、演員、藝術(shù)工作者和舞臺(tái)工作者,都熱烈要求與演出劇團(tuán)的領(lǐng)導(dǎo)和演員舉行座談,要求他們介紹演革命現(xiàn)代戲的經(jīng)驗(yàn)、心得、體會(huì),希望從中獲得一些演現(xiàn)代劇的新知識(shí)。
可見,《紅燈記》對(duì)香港的沖擊和影響主要是通過深圳這個(gè)文化的橋頭堡輻射的,深圳日益成為溝通香港和大陸之間的一座重要文化橋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