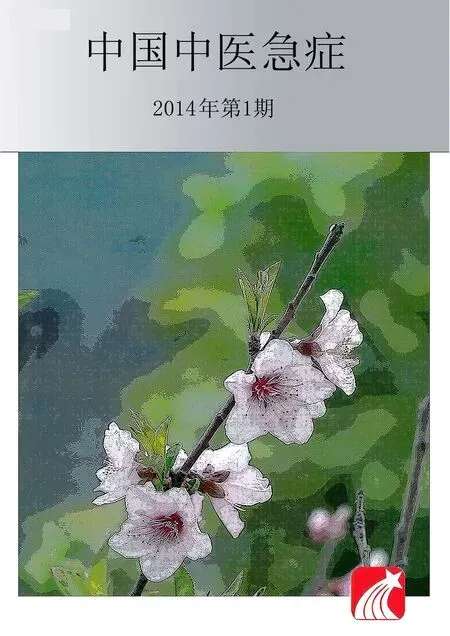楊志旭教授中醫治療重癥肺部感染患者發熱經驗總結
彭 健 王婭楠 指導 楊志旭△
(1.北京中醫藥大學,北京 100029;2.中國中醫科學院西苑醫院,北京 100091)
楊志旭教授中醫治療重癥肺部感染患者發熱經驗總結
彭 健1王婭楠2指導 楊志旭2△
(1.北京中醫藥大學,北京 100029;2.中國中醫科學院西苑醫院,北京 100091)
重癥肺部感染發熱中醫治療攻補兼施
發熱作為內科臨床最為常見的癥狀之一,為諸多疾病的臨床表現。在重癥患者中,發熱的原因通常為感染、組織損傷、腫瘤以及免疫性疾病。通常來講,重癥患者的發熱癥狀多由感染引起。而且嚴重感染是引起多臟器功能衰竭(MODS)最常見也最重要的始動因素[1]。諸多感染之中,肺部感染又是其中最常見的一種。中醫將發熱分為外感發熱和內傷發熱兩大方面。楊志旭教授作為中國中醫科學院西苑醫院重癥監護病房的主任,臨證選用中藥治療重癥患者諸多疑難雜癥均有著自己獨到的見解。筆者有幸跟隨師學習,在中藥治療重癥患者疑難雜癥方面收獲頗多,現將楊教授中醫治療重癥肺部感染患者發熱的經驗總結如下。
1 重癥肺部感染發熱病因病機探析
楊教授認為,重癥感染患者的發熱,大多以內傷為病因,臟腑功能失調,氣血陰陽失衡為基本病機,以發熱為主癥。雖然發熱原因眾多,但是楊師根據臨床重癥患者的實際情況,認為主要有以下幾個主要原因。
1.1 年老體衰入住ICU患者大多數年齡超過70周歲,早在《內經·上古天真論》中便提到女子“七七,任脈虛,太沖脈衰少,天癸竭,地道不通,故形壞而無子也”。男子“八八,天癸竭,精少,腎臟衰,形體皆極則齒發去”。《壽親養老新書》中亦闡述“其高年之人,真氣耗竭,五臟衰弱,全仰飲食以資氣血,若生冷無節,饑飽失宜,調停無度,動成疾患”。因此,由于天癸衰竭,臟腑功能下降,經絡受阻,氣血失衡,或中氣不足,陰火內生;或血虛陰傷,不能斂陽;或陽氣衰竭,虛陽外浮等等。
1.2 飲食勞倦《素問·調經論》說“有所勞形,形氣衰少,谷氣不盈,上焦不通,下脘不暢,胃氣熱,熱氣熏胸中,故內熱”,即勞倦傷脾氣致上焦與下脘不得相通,中焦氣郁而為熱。而脾虛不能化生氣血也能導致氣虛發熱或者血虛發熱,亦或者脾虛生痰,痰濁阻滯,郁而化熱;或進食不化,食積于內,積而成熱。重癥患者大多胃不能入而以鼻飼飲食代之,鼻飼之食又多為流食或營養液為主,與常人正常飲食相差甚遠。再者,由于本身脾胃虧虛,患者大多體倦乏力,肢不能動,導致脈絡更為不通,加重化熱之勢。
1.3 邪毒犯肺重癥患者由于呼吸衰竭、心力衰竭、呼吸窘迫等各種原因,大多接受呼吸機輔助通氣,同時眾多患者為氣管切開或經口氣管插管,致使口鼻不能如正常人般保護肺臟,邪毒能長驅直入,侵襲肺臟,本身僅有之正氣,與邪毒奮力做最后抗爭,正邪相爭,勢必導致發熱,而因正氣虛弱,大多正不勝邪,難以將邪毒清之除之,使得發熱之癥遷延難愈。
1.4 藥物原因由于重癥患者病情復雜,藥物使用種類以及總量相對較大,同時感染作為諸多疾病產生和加重的一個重要因素,為了控制感染,抗生素的使用也較為頻繁。正是因為藥物之性繁雜,其中不乏苦寒清泄之品,使得中焦之陽日漸衰弱,同時,諸多苦寒藥品也易耗損陽氣以及陰液,虛陽外浮,導致發熱。
2 攻補兼施治療難治性發熱分析
楊教授治療重癥患者難治性發熱的原則,主要在于攻補兼施。外邪侵犯,肺衛首當其沖,又因外邪入侵易從陽化熱,故發熱的治療,應審證求因,因勢利導,順勢透邪,務求邪氣外達為要,同時又需清泄里熱,衛氣同治[2]。因此,針對邪毒犯肺,楊師主要依靠3個方法清除邪毒,其一便是宣透,宣,指宣散、宣發、宣通、宣暢;透,指透泄、透發。宣透的治法屬于祛邪的范疇,其特點在于為邪氣尋找出路以引邪外出,是溫病理論中常用的一種方法,楊師認為宣透之法則是通過機體的腠理將熱邪透托出體外。其二便是清泄,清泄法是指通過清熱、瀉火、涼血、瀉下等方法,祛除里熱的治療大法,是先師仲景治療疾病的常用治法[3]。清泄之法則將體內之熱清而泄之,通過代謝產物諸如大便或者小便等物泄出體外。其三,在清泄與宣透之余,楊教授尤其側重“引經”,正如尤在徑云“兵無向導,則不達賊境,藥無引使,是不通病所”。楊師認為患者的發熱為多種因素共同導致,而且熱邪的存在也遍布全身氣血,所以治療相當棘手。重癥患者的發熱一般病程較久,患者入住時邪熱已過衛分以及氣分進入營血分,因此,常常出現舌質紅絳甚至出現出血的癥狀,因此在“清泄”、“宣透”的同時需加用清血分的藥物更利于邪熱的清除。與此同時,楊師跟筆者分析病情時經常強調,重癥患者本身由于年老體弱,脾胃本就虧虛,同時由于清泄藥物大多為苦寒之品,大多攻伐脾胃;再者,溫邪侵襲更易耗損脾胃之氣;又由于飲食、勞倦等諸多因素影響,楊師注重顧護患者的脾胃,正所謂“存得一分胃氣,便得一分生機”。同時,健脾益氣則“補土生金”使脾胃功能恢復,肺氣充盛,肺氣亦能充盛,更有助于邪毒的清除[4]。楊師用方用藥通常會在前面“清泄”、“宣透”、“引經”的基礎上酌加補益脾胃藥物,而又多以建中湯或四君子湯做加減,效果頗佳。
3 藥物使用配伍
針對上述方法,楊師對藥物的配伍和相互作用也頗為講究。首先是“宣透”,楊師認為宣透是本方之中重中之重,楊師認為邪熱熾盛必定耗傷陰液,陰虛容易加重虛熱,因此他常用地骨皮、青蒿、白芷、白薇等清透虛熱的藥物相互配伍,以達宣透之功。其次便是清泄之藥,楊師喜用忍冬藤一藥。楊師認為忍冬藤既有清除熱毒之功,亦有疏通經絡之用,用于重癥患者即可清泄熱毒,又可疏通經絡利邪外出,用之甚佳。楊師也用貫眾一味,認為貫眾有貫通之用,在清除邪熱的同時,可貫通經絡,與忍冬藤相配伍既可疏通,也可清泄,兩者相輔相成,相得益彰。再說“引經”,楊師則將黃芩、牡丹皮作為引經之藥。《本草蒙筌》提到“治寒,肝氣,吳茱萸。血,當歸。治熱,肝氣,柴胡。血,黃芩”。楊師認為,黃芩清熱燥濕、涼血解毒,善于清血中之熱,同時可清除機體中其他濕熱邪毒,亦有將其他邪熱引入血中一起清除體外的功用,同時,牡丹皮可入手厥陰以及足少陰兩經,亦有清除血熱之功用,與黃芩相配可共奏引經之功。對于補益脾胃而言,楊師仿四君子湯及黃芪建中湯之意,常用黃芪、山藥、黨參、茯苓、炙甘草等補脾益氣的藥物,一則實脾,再則健胃,使得患者中焦得立,脾胃得運,正氣得生,從而加快清除邪熱的過程,使患者預后得到大大的改善。
4 驗案舉例
顧某,女性,89歲,主因“咳嗽、咯痰1月,加重伴發熱2周”由本院綜合內科高干病房轉入我科。患者在綜合內科病房按“肺部感染”已經治療1月,先后以頭孢哌酮、亞胺培南、萬古霉素、氟康唑等抗生素控制感染,均未獲效,后患者出現發熱,腋溫常在38℃以上,久而不退,故轉入我科。轉入時癥見咳嗽、咯痰,喉中痰鳴聲明顯,咯出痰為黃色黏痰,痰量中等,發熱無惡寒,無明顯汗出,無胸悶,偶有喘息,鼻飼飲食,夜寐欠安,大便秘結,需使用開塞露灌腸后才能解出,小便量少,色黃。患者既往冠心病、腔隙性腦梗死、老年性癡呆病史,2005年因心動過緩植入心臟起搏器,曾因左側股骨頭骨折、右側股骨頭壞死行股骨頭置換術。入院查體可見患者嗜睡,呼之可應,形體極瘦,查體欠合作,不能對答,癡呆貌。全身皮膚干燥,脫屑,周身皮膚無出血點,胸廓對稱無畸形,雙肺聽診呼吸音粗,雙肺可聞及少量干濕啰音,心界向左下擴大,心率為起搏心率,60次/min,二尖瓣區可聞及收縮期4/6級吹風樣雜音。腹膨隆,按之不硬,無任何壓痛,無其他陽性體征。入院后予鹽酸氨溴索化痰、雷貝拉唑保護胃黏膜、拉氧頭孢控制感染等治療方法,同時予翻身拍背、定時吸痰、氣道濕化等方法幫助痰液從氣道流出。治療兩周后無明顯改善,楊志旭教授查房后中醫辨證為:氣陰兩虛,以自擬方投之,方藥為忍冬藤20g,貫眾12g,黃芩15g,白薇15g,生地黃15g,白茅根15g,牡丹皮12g,白術15g,黨參15g,生黃芪25g,神曲12g,厚樸12g,方用6劑,水煎后鼻飼喂入。服藥后,患者熱勢下降,每日最高體溫降至38℃以下。楊師再次查房,將上述白芷易為地骨皮,同時忍冬藤貫眾易為金銀花、敗醬草,再服6劑之后,患者體溫每日最高為37.1~37.3℃。楊師查房后,守方續服,患者體溫恢復正常。
按:一診中,楊師用黃芩、丹皮相互配伍一則清除血熱,二則將體內其余邪熱一同引入血中清之,同時用忍冬藤、貫眾兩者配伍清泄熱毒,再加以白芷、白薇透出虛熱,最后用黨參、白術、神曲、厚樸清除積熱,建立中焦以達到攻補兼施之用。二診中,楊師用銀花、敗醬草偏清外在之熱,同時用地骨皮以及白芷更清里之虛熱,患者內外之熱漸消。
5 總結
重癥監護病房之中,由于患者基礎疾病眾多,患者發熱癥狀時常發生,盡管抗生素以及復蘇治療近年來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但是重癥感染仍然是導致患者死亡的重要原因,病死率高達30%~70%,早期診斷和治療重癥感染能夠明確降低患者的病死率作為使動因素的肺部感染常常使得發熱更難得到控制[4]。西醫往往通過積極的氣道護理、痰液的引流和抗生素的使用進行治療,但是效果欠佳。楊志旭教授根據自己臨床多年經驗,將“清泄”、“宣透”之攻法聯合補益脾氣及引經之三法并用治療重癥肺部感染患者發熱,臨床效果卓越,筆者將此經驗做簡單總結,與廣大臨床同仁分享,歡迎批評指正。
[1]陳灝珠.多系統臟器官衰竭[M].10版.實用內科學.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98:1750.
[2]劉夕寧,奚肇慶,胡云龍.透表清氣法在病毒性上呼吸道感染發熱的應用[J].中國中醫急癥,2010,19(5):788,850.
[3]侯洪濤,劉立平.仲景清泄法探析[J].江西中醫學院學報,2004,8(16):16-17.
[4]梁晉普,寇蘭俊,王亞紅,等.補中益氣法治療老年性肺部感染臨床體會[J].中國中醫急癥,3013,22(7):1248-1249.
R249.8
A
1004-745X(2014)01-0073-03
10.3969/j.issn.1004-745X.2014.01.034
△通信作者
2013-09-11)
·臨床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