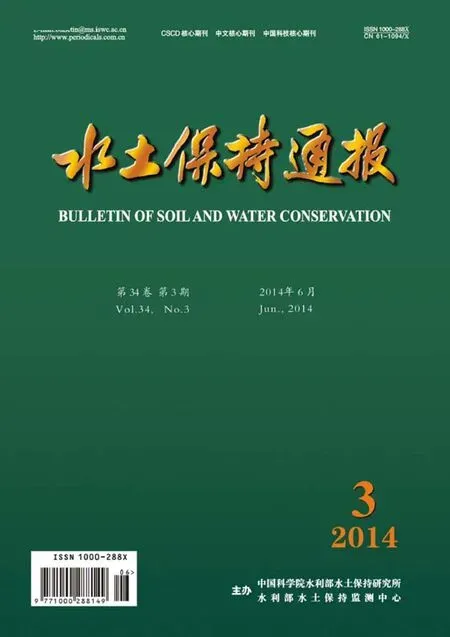淮南大通礦區復墾土壤微生物量碳氮的分布特征
張杰瓊,方鳳滿,2,余 健,江培龍,鄧正偉,林躍勝
(1.安徽師范大學 國土資源與旅游學院,安徽 蕪湖241003;2.安徽自然災害過程與防控研究省級實驗室,安徽 蕪湖241003)
土壤是人類賴以生存發展的重要物質基礎。隨著煤炭資源的開采,特別是井工開采造成大面積的地面塌陷,嚴重破壞了礦區土壤資源,使可耕地面積減少,影響了礦區農業生產,同時會導致民事糾紛增多,誘發嚴重的社會問題[1-2]。因此,采煤塌陷地土壤的生態恢復成為礦區復墾的研究熱點之一。
土壤微生物是土壤生態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有機質分解,養分循環和植物養分利用過程中發揮著關鍵作用,同時對外部環境變化敏感,因此,土壤微生物量可以作為綜合評價土壤質量和肥力狀況的指標之一[3]。與自然土壤相比,復墾區土壤表土擾動劇烈,土壤理化性質和性狀受到較大破壞,使得土壤微生物的生存環境發生變化,因而礦區土壤的微生物種群數量的多少可以作為礦區復墾土壤性質演變的指標之一。現有采煤塌陷地復墾土壤研究多集中在復墾后土壤可耕性及污染狀況時空變化及評價等方面[4-5],而有關煤礦復墾區內部土壤微生物量碳氮的空間分布特征研究較少。本文以淮南市大通區九龍崗煤礦復墾區為研究對象,通過比較不同農業用地方式下土壤微生物量碳、氮的分布特征并分析其影響因素,探討煤礦復墾區土壤微生物量和農業用地方式之間的相關性,以期為煤礦復墾區土壤肥力的維持和培育提供一定的參考和借鑒。
1 材料與方法
1.1 研究區概況
安徽省淮南市大通老礦區,隨著煤炭資源的枯竭,礦井報廢,形成了大面積耕地沉陷,為典型的穩定塌陷區,于2004年完成復墾,其生態修復工程已成為礦區塌陷地復墾的成功典范。該區復墾方式是利用礦區廢物煤矸石、污泥等充填后,表層覆正常農田土壤造田種植,覆土厚度為40cm(油菜地、蔬菜大棚覆土多為表層土,小麥地、林地覆土表層土相對較少)。該區屬于亞熱帶季風氣候,氣候溫和,雨熱同期,日照充足,積溫較高降水集中于春夏季節,年日照時數為2 279~2 323h,年平均氣溫15℃左右,年平均降水量900mm。土壤類型主要為黃棕壤。
1.2 樣品采集與處理
2012年4月底,通過實地考察和資料收集,采用網格布點法,結合土地利用現狀,根據農業用地方式的不同(油菜地、林地(灌木桃林)、蔬菜大棚、小麥地)分別設置3~8個采樣點,采樣前去除地表植被及雜物,每個樣點分別采集3個土樣均勻混合成一個樣品,現場取一部分裝鋁盒,用烘干法測定土壤水分。采樣深度為0—10cm。并采集塌陷地未復墾土壤作為對照樣,共采集土樣18個,所得土樣儲存于4℃以下的便攜式冷藏箱中。同時記錄采樣點周邊環境特征并調查肥料施用狀況。
樣品帶回實驗室后,除去土壤動植物殘體和碎石,碾碎過2mm篩,混合均勻,分為兩份。一份鮮樣測定土壤微生物量碳氮;另一份土樣經風干磨細,過60目篩,測定土壤理化性質。
1.3 分析方法
微生物量碳、氮的測定采用氯仿熏蒸—K2SO4提取法,分別用重鉻酸鉀氧化法和開氏定氮法測定浸提液中的碳、氮[6]。土壤理化性質采用實驗室常規分析方法[7]。
本文采用SPSS和Excel軟件進行統計數據分析,處理間的差異顯著性采用單因素方差分析檢驗,變量間的相關關系采用Pearson相關統計方法。
2 結果與討論
2.1 土壤理化性質
由表1可知,復墾區土壤理化性狀差異顯著,pH值約為7.41±0.32,呈中性。土壤有機碳的變化由高到低依次為:油菜地>蔬菜大棚>小麥地>林地,且達到顯著性水平(小麥地與林地除外)(p<0.05)。同為旱作糧田,油菜地土壤有機碳含量顯著高于小麥地、林地和蔬菜大棚。主要是由于油菜地上覆表土為當地基本農田表層土,而其他農業利用方式土壤上覆表土土壤主要來自深層土壤,故油菜地土壤有機碳含量顯著高于其他農業用地方式。蔬菜大棚有機碳含量顯著高于林地和小麥地,可能是由于大棚內施用有機肥和化肥的頻率較高,強度較大所致。土壤全氮和全磷的變化趨勢與有機碳分布具有很好的相關關系。受施肥頻率及施肥種類的的影響,土壤中全氮、全磷的變化趨勢與堿解氮和有效磷的變化并不一致,土壤堿解氮和有效磷的高低變化順序則表現為蔬菜大棚、油菜地、小麥地、林地。林地堿解氮含量顯著低于其他農業用地方式(p<0.05)。蔬菜大棚有效磷含量顯著高于其他農業用地方式。可見,施用有機肥和進行秸稈還田可提高復墾區土壤有機碳含量,大量施用化肥會造成土壤氮、磷含量較高,pH值下降。
總體上,耕地(蔬菜大棚、小麥地、油菜地)的有機碳、氮、磷含量均高于林地;pH值則是林地高于耕地。對照全國第二次土壤普查土壤養分分級標準[8],發現研究區土壤養分普遍缺乏,屬于低肥力土壤生態系統,需通過各種方式改善土壤肥力。
2.2 土壤微生物量碳和微生物量氮
土壤微生物量的高低反映了土壤礦化和同化能力的大小,是土壤生態系統肥力的重要生物學指標[9]。不同農業管理措施對土壤微生物生物量具有明顯的影響[10]。由圖1可知,復墾區土壤微生物量碳含量變幅在116.89~432.58mg/kg,平均值為254.45±81.54mg/kg;與對照樣相比,土壤微生物量碳含量有明顯提高。

表1 淮南煤礦復墾區土壤理化性質分布特征

圖1 復墾區土壤微生物量碳分布特征
土壤微生物量碳由高到低依次為蔬菜大棚(421.19±16.09mg/kg)>油菜地(254.69±32.53mg/kg)>小麥地(232.58±2.89mg/kg)>林地(224.60±63.88mg/kg),蔬菜大棚土壤微生物量碳顯著高于其他農業用地方式(p<0.05)。這與劉文娜等[11]的研究結果(糧田>菜地>林地)并不一致。一方面可能是由于該區蔬菜大棚施用有機肥和化肥的頻率和強度明顯高于林地和糧田(小麥地、油菜地),使得土壤外來有機碳源增加,土壤理化性狀得到改善,植物根系生物量及根系分泌物增加,進而提高了土壤微生物量碳含量。另一方面是由于大棚覆蓋使得土壤能夠保持相對穩定的溫度和濕度,同時減少了太陽光照射對土壤微生物的損害,從而提高土壤微生物的活性。與劉文娜等[11]的研究結果相比,研究區林地土壤微生物量碳和糧田(小麥地、油菜地)差異性并不顯著,可能是由于采樣期間正值農作物生長季節,作物生長迅速與土壤微生物競爭養分,最終導致糧田土壤微生物量較低。另一方面是由于復墾年限尚短,不同農業用地方式和農業管理對土壤微生物量碳的影響尚未充分顯現。
由圖2可知,土壤微生物量氮含量變幅在10.81~26.56mg/kg,平均值為19.0±4.87mg/kg。在不同農業用地方式下依次為:蔬菜大棚(25.7±1.253mg/kg)>小麥地(21.92±0.095mg/kg)>油菜地(21.63±0.908mg/kg)>林地(15.65±4.177mg/kg)。
差異性分析表明,林地土壤微生物量氮顯著低于其他農業用地方式(p<0.05)。但趙先麗等[12]研究表明林地土壤微生物量氮含量顯著高于耕地,這可能是因為本研究區林地是典型的速生灌木林地,與一般天然林地相比,生長年限較短,且常年不施肥,土壤有效氮匱乏,微生物對土壤氮素的固定量降低。而小麥地、油菜地和蔬菜大棚由于長期施用有機肥和化肥有效地補充了土壤有效氮源,故微生物量氮含量要顯著高于速生林地。

圖2 復墾區土壤微生物量氮分布特征
2.3 土壤微生物熵
土壤微生物碳/土壤有機碳稱為微生物熵,對有機質含量不同的土壤進行比較時,比土壤微生物碳更具優勢[13]。由圖3可知,復墾區土壤微生物熵在0.65%~2.81%,平均值為1.71±0.68%。與未復墾對照樣(0.56%)相比,不同農業用地方式下土壤微生物熵均有較大提高,說明復墾后土壤環境更有利于土壤微生物的生長。
由圖3可知,4種農業用地方式下,林地土壤微生物熵最高為2.01±0.65%,油菜地最低為0.71±10.1%,小麥地(1.71±0.23%)與蔬菜大棚(1.85±0.35%)相差不大。說明林地在有機質積累過程中更有利于土壤微生物量的提高,這可能是由于林地表層土壤受人類擾動少,土壤結構適宜,更有利于土壤微生物的生長。同為旱作糧田,油菜地土壤微生物熵顯著低于小麥地,可能是由于復墾土壤由于人為擾動較大,使得土壤微生物生存環境發生變化,從而影響了油菜地土壤微生物商的大小。

圖3 復墾區土壤微生物商分布特征
2.4 土壤微生物量碳氮與土壤理化性質相關性分析
土壤微生物量碳與有效磷之間呈極顯著正相關(R=0.755,p<0.05);土壤微生物量氮與土壤有機碳、堿解氮、全磷、有效磷呈顯著正相關(R=0.485,0.485,0.621,0.644,p<0.05)。土壤微生物量碳、氮之間極顯著正相關(R=0.623,p<0.05,表2)。與前人研究結果相比[11,14],土壤微生物量碳和有機碳、全氮的相關性并未達到顯著性水平,而土壤微生物量碳與有效磷呈顯著相關。這可能是由于磷肥的施入可以刺激植物根系發育,地下生物量增加促進了根系分泌物的釋放,增加根系殘茬的還田量。另一方面可能是磷素的加入使得土壤pH值改變或鹽濃度改變,創造了有利于土壤微生物生存的環境。

表2 土壤微生物量碳氮與土壤理化性質相關性分析
3 結論
淮南煤礦復墾區土壤理化性質與土壤微生物量碳、氮差異顯著。油菜地和蔬菜大棚的土壤有機碳、全氮、全磷含量顯著大于小麥地和林地,受施肥措施的影響,林地土壤pH值較大,堿解氮和有效磷顯著小于其他農業用地方式。土壤微生物量碳、氮及微生物熵與對未復墾對照樣相比均有較大提高,復墾區土壤微生物量碳、氮,均表現為蔬菜大棚最高,油菜地和小麥地相差不大,林地最低。微生物熵分析表明,林地具有較高的微生物維持能力;土壤微生物量碳、氮之間顯著相關,表明土壤微生物量碳、氮可以作為表征土壤肥力的敏感因子。
[1] 劉飛,陸林.采煤塌陷區的生態恢復研究進展[J].自然資源學報,2009,24(4):612-620.
[2] 李新舉,胡振琪,李晶,等.采煤塌陷地復墾土壤質量研究進展[J].農業工程學報,2007,23(6):276-280.
[3] 李新愛,肖和艾,吳金水,等.喀斯特地區不同土地利用方式對土壤有機碳、全氮以及微生物生物量碳和氮的影響[J].應用生態學報,2006,17(10):1827-1831.
[4] 梁利寶,洪堅平,謝英荷,等.不同培肥處理對采煤塌陷地復墾不同年限土壤熟化的影響[J].水土保持學報,2010,24(3):140-145.
[5] 李玲,高暢,董洋洋,等.典型煤礦工業園區土壤重金屬污染評價[J].土壤通報,2013(1):227-231.
[6] 彭佩欽,吳金水,黃道友,等.洞庭湖區不同利用方式對土壤微生物生物量碳氮磷的影響[J].生態學報,2006,26(7):2261-2267.
[7] 魯如坤.土壤農業化學分析方法[M].北京:中國農業科技出版社,2000.
[8] 王小利,蘇以榮,黃道友,等.土地利用對亞熱帶紅壤低山區土壤有機碳和微生物碳的影響[J].中國農業科學,2006,39(4):750-757.
[9] 董莉麗,鄭粉莉.土地利用類型對土壤微生物量和有機質的影響[J].水土保持通報,2009,29(6):10-16.
[10] 張平究,李戀卿,潘根興,等.長期不同施肥下太湖地區黃泥土表土微生物碳氮量及基因多樣性變化[J].生態學報,2004,24(12):2818-2824.
[11] 劉文娜,吳文良,王秀斌,等.不同土壤類型和農業用地方式對土壤微生物量碳的影響[J].植物營養與肥料學報,2006,12(3):406-411.
[12] 趙先麗,呂國紅,于文穎,等.遼寧省不同土地利用對土壤微生物量碳氮的影響[J].農業環境科學學報2010,29(10):1966-1970.
[13] 任天志,Grego S.持續農業中的土壤生物指標研究[J].中國農業科學,2000,33(1):68-75.
[14] 王曉龍,胡鋒,李輝信,等.紅壤小流域不同土地利用方式對土壤微生物量碳氮的影響[J].農業環境科學學報,2006,25(1):143-1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