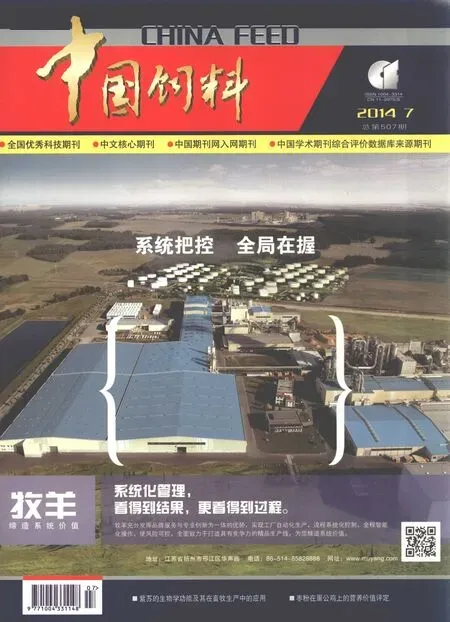微生物原生質體融合育種技術及其應用研究進展
劉敏躍,李 鵬,龍 淼*
(1.遼寧省農牧業機械研究所有限公司,遼寧沈陽 110036;2.沈陽農業大學畜牧獸醫學院,遼寧沈陽 110161)
原生質體融合是20世紀70年代發展起來的基因重組技術,具有許多常規雜交方法無法比擬的獨到優點:(1)克服種屬間雜交的“不育性”,可以進行遠緣雜交。(2)基因重組頻率高,重組類型多。(3)可將由其他育種方法獲得的優良性狀,經原生質體融合而組合到一個菌株中。(4)存在著兩個以上親株同時參與的融合,可形成多種性狀的融合子。同基因工程方法相比,這一技術不需對試驗菌株進行詳細的遺傳學研究,避免了分離提純、剪切、拼接等基因操作,也不需高精尖的儀器設備和昂貴的材料費用等(羅雯和陳志勤,2003)。隨著生物學研究手段的不斷創新,原生質體融合技術的基本實驗方法逐步完善。經過多年的實際應用證明,微生物原生質體融合是一項十分有用的育種技術(Kim 等,2000)。
1 原生質體融合方法
1.1 化學法——PEG結合高Ca2+法 親本原生質體制備好后,即可進行融合,但在自然條件下雖然也可融合,但融合率極低。自從1974年Kao和Michayluk用聚乙二醇(PEG)誘導大麥、大豆等植物原生質體融合后,PEG很快用于微生物細胞的原生質體融合。其融合效率高,適用范圍廣,在各類微生物細胞原生質體的融合中廣泛使用。
1.2 電融合 原生質體電融合是始于20世紀80年代的細胞改良技術。這一技術將電學與生物化學相結合,產生了緩和而高頻率的原生質體融合效果。實踐證明,該技術不但廣泛用于動物和植物的細胞融合,而且在各類微生物細胞的改良中也十分有效。如原核微生物克氏固氮菌與枯草芽孢桿菌的原生質體融合;真核微生物中的酵母菌、霉菌中的黑曲霉以及食用真菌中的蘑菇等均有原生質體電融合的報道。
1.3 激光誘導融合 1987年利用激光誘導融合的技術迅速發展起來,并很快被應用在動物細胞及植物原生質體融合中,后來又被用于微生物原生質體融合中。激光融合的優點是毒性小、損傷小,但由于其所需設備昂貴復雜,操作技術難度大,很難推廣應用。在微生物原生質體融合中應用激光微束技術,融合效率低,且喪失了高度選擇性的優點,有賴于后續步驟檢出融合子。因此,激光誘導融合技術仍處于發展初期,還有待于進一步完善。
2 原生質體融合子篩選方法
融合體中除重組體外,還有異核體或部分結合子、雜合二倍體或雜合系,這些都會在平板上形成菌落,檢出融合體的方法有多種,在育種工作中可根據實驗目的和微生物不同加以選擇。
2.1 利用營養缺陷型標記篩選融合子 這是常見而有效的傳統選擇標記方法,其檢出設計原則是將親本菌株誘變處理后產生對某些營養物質合成途徑受阻的突變株,在分離的培養基上只有融合子生長而不能讓突變的雙親本原生質體形成菌落。融合的雙親帶有不同營養缺陷型標記,原生質體融合處理后的混合物直接分離到基本培養基上就可以檢出融合子。
2.2 利用抗藥性標記篩選融合子 微生物抗藥性是菌種的重要特性,是由遺傳物質決定的,不同種的微生物對某一種藥物的抗性存在差異,利用這種差異即可對融合子進行選擇。Bradshaw Perdy首先用這種方法檢出了融合子。他們以Apergillusrugulosus(營養缺陷型,吖啶黃抗性)和Apergillusrugulosus(原養型,吖啶黃敏感)為雙親本,經原生質體融合處理后在含有25 μg/mL或50 μg/mL吖啶黃的基本培養基上檢出融合子。但應用此法須注意藥物濃度,過高會使融合頻率降低,過低則會使親本生長,影響融合子的檢出。
2.3 利用熒光染色法篩選融合子 熒光染色法是事先將雙親染色而攜帶不同熒光色素(DAPI,FTTC)標記,然后在顯微操作器和熒光顯微鏡下,挑取同時帶有雙親原生質體熒光標記的融合子,直接分離到再生培養基上再生,最后得到融合子。本法簡便易行,保持了親本的優良遺傳特性,是融合子選擇法的發展趨勢,但對儀器設備要求高,且費用高,有條件的實驗室采用此法能提高融合效率。
2.4 利用滅活原生質體標記篩選融合子 利用滅活原生質體標記篩選融合子的原理是在原生質體融合之前,對單親或雙親原生質體進行滅活,使其喪失再生的能力,當與另一親株融合后,代謝上得到互補,能夠存活。滅活的方法很多,主要有熱滅活法和紫外滅活法,某些化學藥劑(如碘乙酸)滅活法等。將融合親本之一原生質體滅活,即可根據另一親本的特性設計選擇條件篩選融合子。由于滅活原生質體融合減少了尋找穩定遺傳標記的繁瑣工作及由此可能帶來的親株優良性狀的丟失,因此是獲得遺傳重組的一條有利途徑;而且在不利用選擇培養基的情況下即可減少親株的生長,從而提高了篩選效率,因而在融合子篩選上的應用也較為廣泛(王燕,2007;高玉榮等,2006),但滅活法的不足之處是融合頻率下降。
2.5 雙親對碳源利用不同而檢出融合子 利用親株對各種碳源利用差異,結合其他特性分離篩選出融合子。如釀酒酵母89-1為呼吸完整,不能利用木糖,對放線菌酮敏感的一株酵母菌。另一株親株是經誘變劑處理后的呼吸缺陷型菌株,但能夠抗20 μg/mL放線菌酮。當這兩親本融合后,融合子能在含有木糖和20 μg/mL放線菌酮的選擇培養基上生長。通過此方法可將融合子篩選出來,但此法適應的菌種范圍相對較小。
2.6 融合子的其他篩選方法 以上幾種方法可以較準確地選出融合子,還有一些輔助性方法可用于融合子的檢測。雖然用這些方法單獨定論是否為融合子證據不充分,但他們各自都從不同方面證實融合發生,因而常被用作非人工標記鑒別融合子的輔助性方法,主要用于:(1)對昆蟲的毒力測定進行融合子的選擇;(2)利用形態差異選擇融合子,這一方法首先要求所采用的菌株具有可供肉眼直接觀察的形態學差異,目前只有在青霉的育種過程中采用這種方法;(3)生化測定指標選擇融合子,通常測定的生化項目有DNA含量、氨基酸含量、酸性磷酸酶、同工酶和電泳等。一般來說,融合子的DNA含量高于任何一個親本的DNA含量,但卻少于雙親DNA含量之和。融合子與雙親氨基酸含量百分比不同,融合子和親本的酸性磷酸酶同工酶和酯酶同工酶酶譜電泳結果也不同。
以上是一些常見的融合子篩選方法,實際應用中往往是將上述這些方法進行結合使用。如將營養缺陷型與抗藥性、抗藥性與原生質體滅活等相結合選擇融合子。
3 原生質體的鑒定方法
原生質體融合過程中,先是細胞質融合然后才是細胞核融合,所以融合產物可能有兩種:合核體(細胞質和細胞核產物)和異核體(細胞質融合產物),前者遺傳穩定,為真正的融合子,后者不穩定,容易發生性狀分離。因此,要得到真正的融合子,必須進行數代的自然分離和選擇鑒定(陳代杰和朱寶泉,1994)。融合子的鑒定一般從形態學、生理生化特性、生長速度、生物量、遺傳學(基因型、核型、DNA含量、GC比等)和同工酶等分析實現。近年來,也有人通過DNA限制內切酶酶切片段圖譜比較、核苷酸序列分析、分子雜交、RAPD技術等分子生物學方法來鑒定融合子(孫劍秋和周東坡,2002)。
菌落形態觀察:采用巨大菌落法。融合產物在平板上長出的菌落形態一般有兩種:兩親本類型和非親本類型,后者很可能就是融合子。
菌體形態觀察:融合子在傳代初期,細胞形態差異很大,隨著傳代次數的增加,細胞形態趨于穩定。
菌體細胞大小:一般用顯微測微尺分別測量親株和融合子的長軸、短軸,按公式:V=4/3·π·a/2·(b/2)2計算。研究表明,融合子細胞體積并非為兩親株細胞體積之和,而是略大于或介于兩親株之間。有研究發現,融合子的細胞體積在傳代過程中有逐漸縮小的趨勢,一般恢復到與親本大小相近的程度,但軸比及體積仍與同親本有一定差別。
DNA含量:有的融合子DNA含量接近兩親株DNA含量之和,有的介于兩親株之間。這種現象一般認為是由于融合子在傳代穩定過程中部分親本染色體丟失引起的。
生理生化特性:優良的融合子應兼具雙親的優良特性。對融合子生理生化特性的分析一般針對兩親株生理特性的差異進行,包括生長溫度、耐酒精濃度、碳源/氮源底物分解利用情況、營養需求等。
核染色:融合過程中,兩親株原生質體在促融因子作用下先發生凝集、接觸,再進行細胞質融合,進而可能發生核融合。所以在選擇培養基上長出的融合產物有兩種:真正的融合子(細胞質和細胞核都發生了融合)和異核體(只有細胞質發生了融合)。Gimsa染色、Feulgen染色、蘇木精染色或 4,6-二氨基-2-苯基吲哚(DAPI)熒光染色都能清楚地看到核相,從而使異核體得到排除(焦瑞身,1989)。
同工酶電泳:一般通過乙醇脫氫酶同工酶、酯酶同工酶電泳對融合產物加以鑒定。若融合物具有兩親株的譜帶,則可證明是真正的融合子。
4 原生質體融合育種技術的應用
4.1 在抗生素生產上的應用 原生質體融合技術不僅可用于提高抗生素的產量,同時還可用于融合子產生新的抗生素的研究。柳君科(1989)將產生慶大霉素的棘孢小單孢菌(Micromonospora ech inospora)與鏈霉素產生菌灰色鏈霉菌素(Streptomyces griceus)進行原生質體融合,其融合子產生慶大霉素的產量比親本菌明顯提高。賀敏霞等(1989)通過將諾卡氏菌原生質體融合重組得到了一株簡體轉化活力明顯高于親本的融合子。林榮團和楊毓芬(1990)以天然無抗菌活性的變青鏈霉菌1326與鏈霉菌1254營養缺陷型突變株進行種間原生質體融合,從755株融合體中篩選到5株抗菌活性較穩定的菌株。徐京寧等(1992)將金色鏈霉菌(Streptomuces.au reofaciens)和林可鏈霉菌(Streptomycesl incolnensis)的原生質體融合,其融合株能在孢內積累一種新的具抗菌活性的物質,其性質不同于兩親株所產生的抗生素金霉素和林可霉素。曾洪梅和張震霖(1995)通過原生質體融合的方法提高了農抗武夷菌素的效價。朱昌雄和李永慧(1996)通過對中生菌素高產菌株采用原生質體融合等4種育種方法,結果表明所用方法都能有效地提高中生菌素產生菌的效價。陳五嶺(1997)對金霉素鏈霉菌和龜裂鏈霉菌原生質體融合,融合子產抗生素能力及遺傳穩定性均優于金霉素鏈霉菌。王金盛和李春波(1998)用電場誘導棘孢小單胞菌原生質體融合,得到產小諾霉素(MCR)量高于親株的融合子。
4.2 在防治動物疾病上的應用 王興龍等(1994)進行了多殺性巴氏桿菌×73株與P1059株原生質體融合株的構建,融合株兼具有兩親本株的抗原性和雙抗藥性,從而為研究新型的禽多殺性巴氏菌雙價菌苗奠定了基礎。張元和等(1995)進行了痢疾桿菌P15和E弧菌8822原生質體融合的初步研究,獲得兼有兩親株遺傳性狀的融合子。任濤等 (1998)進行了大腸桿菌O2(Norr,Chls)、O78(Chlr,Nors)原生質體制備和再生。蔣文泓和黃青云(1999)以耐藥標記的禽多殺性巴氏桿菌5A弱毒菌株與禽大腸桿菌02弱毒菌株作親本進行原生質體融合后再生,成功地獲得3株具有雙親本耐藥性和雙菌體血清型的融合菌株,獲得具有多種疾病免疫力的疫苗生產菌株。吳孔興等(2002)進行了禽巴氏桿菌、大腸桿菌融合二聯弱毒菌株的培育。鐘蕾等(2002)進行了腸型點狀氣單胞菌和魚害黏球菌融合子的構建,獲得了制備這種融合疫苗的遺傳性穩定的融合菌株。這些都為動物疫病防治探索出了一條新的途徑。
4.3 在改良菌種及優化菌種特性上的應用 許多微生物能在較高的溫度下生存,有的能在45~65℃甚至更高溫度下生長。有的耐熱菌可在98℃的溫泉中生長繁殖。這種耐熱特性在工業上具有很重要的應用價值,比如在酒精釀造中,釀酒酵母在40℃時產酒率明顯下降,要降低發酵液的溫度,必須消耗大量能源,因為在纖維素類物質同步糖化發酵(SSF)過程中制約反應效率的一個重要因素是纖維素酶的最適溫度同酵母發酵的最適溫度的不一致性,纖維素酶的最適溫度為45~50℃,而酵母發酵的控制溫度一般在30℃左右,選用耐高溫酵母菌株是解決纖維素同步發酵中這兩個溫度不協調的有效方法。Seki等(1983)、方靄祺和李紹蘭(1990)通過原生質體融合分別獲得了42℃條件下發酵產酒精體積分數為6.0%和40℃發酵產酒精體積分數為5.9%的耐高溫酵母。文鐵橋和趙學慧(1999)通過耐高溫的克魯維酵母和產酒率高的釀酒酵母進行屬間原生質體融合,獲得了在45℃下發酵產酒精體積分數為7.14%的融合子。孫君社等(2002)通過原生質體融合獲得了在固態發酵45℃時產酒能力達到體積分數為7.28%的融合子。
由于自身生長條件的限制,許多菌種如雙歧桿菌是嚴格的厭氧菌,生長相對緩慢,需經F6PPK的特殊途徑發酵葡萄糖,對氧極為敏感,暴露在空氣中易死亡,給雙歧桿菌微生態制劑的生產、開發帶來困難,其制劑中的活菌數也難以長時間維持,極大地限制了其在食品工業中的應用。張莉滟和張德純(2003)將兼性厭氧菌保加利亞乳桿菌熱滅活的原生質體作為遺傳物質供體,采用電融合方法,誘導其原生質體與雙歧桿菌融合,將其耐氧基因隨機整合到長雙歧桿菌中,提高了其耐氧能力。黎永學等(2002)將雙歧桿菌和釀酒酵母原生質體融合,初篩出具有雙歧桿菌和釀酒酵母生物學特性、較穩定的融合細胞株BSF1和BSF2,克服了雙歧桿菌因厭氧而不易開發利用的難題,為益生菌種的改良提供了新思路。
嗜酸乳桿菌(L.acidophilus)是人和動物腸道中重要的微生物,口服乳酸菌需要菌體能夠通過低pH胃液存活下來,還要耐受腸道內的膽鹽濃度,但不是所有的嗜酸乳桿菌都能耐受低pH和高濃度膽鹽環境,王玉華等(2006)利用原生質體融合技術獲得一株能耐酸耐膽鹽能力強的菌株La-F1,并且其生長特性符合乳酸發酵食品的要求,也可用在發酵肉制品、醫藥和飼料工業中。
5 原生質體融合育種存在的問題
原生質體融合技術雖取得了較大的發展,但也存在著許多問題和困難。雖然細胞融合階段不存在異種間的任何不親和性,但在核融合染色體交換、雜交,以及融合雜種細胞隨后的發育過程中,遠源物種之間仍存在著嚴重的不親和性和排斥性,有時并未發生真正的核融合,兩親本的染色體是相互保守甚至是排斥的,它們所帶的基因無法在一個細胞中同時表達出來,最終產生了分離。原生質體融合技術的另一困難是雜種鑒定問題。雜種鑒定往往需要從遺傳、生化等方面獲得有利的證據。所以首選兩親本也應有某些生化或遺傳標記,但在自然界帶有這類標記的細菌很少,雖可通過人工誘導產生突變體,而獲得一個真正的突變體不經過幾年的時間是無法獲得的,而單親滅活原生質體可顯著縮短融合工序和時間,提高篩選效率,但融合的頻率明顯降低。
6 小結
綜上所述,原生質體融合技術為遺傳操縱、分子生物學和基礎理論研究提供了一種重要工具,也為遺傳育種改良提供了一種有效手段,現已廣泛應用于各個領域,尤其為微生物育種提供了一種簡潔而高效的方法。
目前,原生質體融合技術發展迅速、應用廣泛,已經成為遺傳育種的重要手段,尋找具有更高融合效率的方法有著重要意義。如基于微流控芯片的原生質體融合技術、高通量原生質體融合芯片、空間原生質體融合技術、離子束原生質體融合技術和滅活原生質體融合技術相繼被提出并被應用于遺傳育種中。而且高通量原生質體融合芯片可以與化學誘導融合、電融合等方法相互結合,這些技術將在未來原生質體融合育種方面的研究中發揮重要作用,相信隨著融合技術的不斷完善,原生質體融合技術在遺傳育種中的地位將會越來越重要(王登宇等,2008)。
[1]陳代杰,朱寶泉.工業微生物菌種選育與發酵控制技術[M].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1994.
[2]陳五嶺.酯酶同工酶技術在選育BT新菌株中的應用[J].西北大學學報,1997,(4):355 ~ 358.
[3]方靄祺,李紹蘭.耐熱酵母與釀酒酵母原生質體融合的研究[J].生物工程學報,1990,6(3):224 ~ 229.
[4]高玉榮,李大鵬,高年發.利用單滅活原生質體融合技術選育降酸能力強的葡萄酒酵母[J].中國食品學報,2006,6(3):106 ~ 110.
[5]賀敏霞,史濟平,褚志文.諾卡氏菌原生質體融合重組研究[J].生物工程學報,1989,5(4):303 ~ 308.
[6]蔣文泓,黃青云.禽多殺性巴氏桿菌與大腸桿菌原生質體融合的研究[J].畜牧獸醫學報,1999,30(3):267 ~ 272.
[7]焦瑞身.細胞工程[M]北京:化學工業出版社,1989.
[8]黎永學.雙歧桿菌和釀酒酵母原生質體融合的研究[D].重慶:重慶醫科大學,2002.
[9]林榮團,楊毓芬.天然無抗菌活性鏈霉菌種間原生質體融合與活性重組體的分離[J].生物工程學報,1990,6(2):134 ~ 139.
[10]柳君科.棘孢小單孢菌和灰色鏈霉菌原生質體融合的研究[J].遺傳學報,1989,16(1):49 ~ 55.
[11]羅雯,陳志勤.微生物原生質體融合技術及其在育種中的應用[J].西安聯合大學學報,2003,6(4):5 ~ 9.
[12]任濤,黃青云,歐守杼.大腸桿菌 O2(Norr,Chls)、O78(Chlr,Nors)原生質體制備和再生的研究[J].華南農業大學學報1998,19(1):49~53.
[13]孫劍秋,周東坡.微生物原生質體技術[J].生物學通報,2002,37(7):9~11.
[14]孫君社,李雪,李軍席.原生質體融合構建耐高溫酵母菌株[J].食品與發酵工業,2002,28(5):1 ~ 5.
[15]王登宇,臧威,孫劍秋.細菌原生質體融合育種技術及其應用進展[J].中國釀造,2008,7:1 ~ 6.
[16]王金盛,李春波.電場誘導棘孢小單胞菌原生質體融合[J].生物技術,1998,8(6):6 ~ 8.
[17]王興龍,劉玉斌,馮來坤.多殺性巴氏桿菌X73株與P1059株原生質體融合株的構建[J].中國獸醫學報,1994,14(2):177 ~ 180.
[18]王燕.雙親滅活米曲霉原生質體融合中原生質體制備的研究[J].中國釀造,2007,5:19 ~ 22.
[19]王玉華,張桂榮,劉景圣.原生質體融合提高嗜酸乳桿菌耐酸及耐膽鹽能力[J].食品科學,2006,27(3):96 ~ 99.
[20]文鐵橋,趙學慧.酵母菌屬間原生質體融合構建耐高溫酵母菌株[J].微生物學報,1999,2:141 ~ 147.
[21]吳孔興,黃青云,丘家軍.禽巴氏桿菌大腸桿菌融合二聯弱毒菌株F4的培育[J].華南農業大學學報,2002,28:139 ~ 142.
[22]徐京寧,米貫東,唐孝宣.應用原生質體融合技術定向改造林可霉素產生菌的探索[J].生物工程學報,1992,8(3):237 ~ 242.
[23]曾洪梅,張震霖.原生質體融合提高農抗武夷菌素的效價[J].微生物學報,1995,35(5):375 ~ 380.
[24]張莉滟,張德純.雙歧桿菌與乳桿菌原生質體的融合及篩選[J].生物技術,2003,13(4):14 ~ 15.
[25]張元和,康素蘭,姚敏.痢疾桿菌D15和EiTor弧菌88-2原生質體融合的初步研究[J].中國微生態學雜志,1995,7(4):62 ~ 63.
[26]鐘蕾,肖克宇,周夢嬌.腸型點狀產氣單胞菌和魚害粘球菌原生質體融合的耐藥性遺傳標記的選擇[J].湖南農業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2002,28(2):150 ~ 153.
[27]朱昌雄,李永慧.中生菌素高產菌株的選育[J].中國生物防治,1996,12(1):15 ~ 19.
[28]Kim B K,Kang J H,Jin M,et al.Mycelial protoplast isolation and regeneration of Lentinus lepideus[J].Life Sci.,2000,66(14):1359 ~ 1367.
[29]Seki T S,Myoga S,Limtong S,et al.Genetic construction of yeast strains for high ethanol production[J].Bioteehno1.Let.,1983,5(5):351 ~ 356.